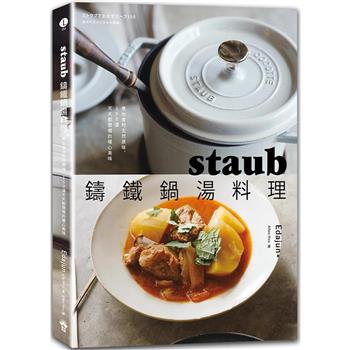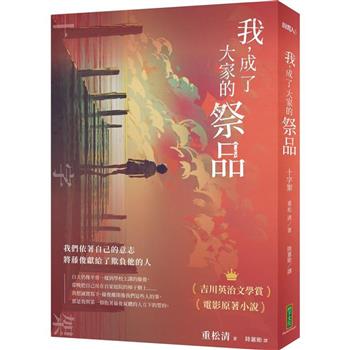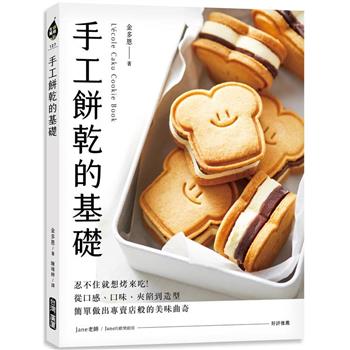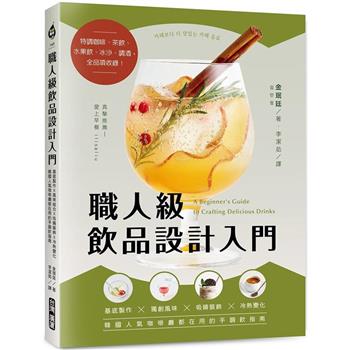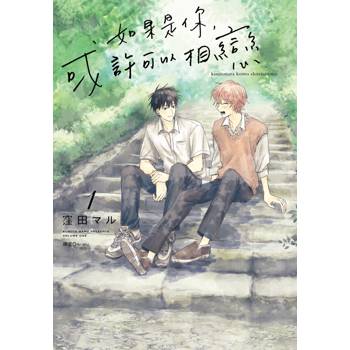【第一章】 轉舊為新──《群書治要》的編纂與意義
一、前言
回顧歷史,在朝代交替的時間區段中,對於文化的發展多具有關鍵性意義。戰火的洗禮,打破了學術文化穩定發展的走向,雖然典籍的焚棄與人才短缺等問題,常使新朝代在初始時顯得貧乏、失色,但伴隨而來的審視,汰除臃腫、無味、失根的學術內容,重新以不同的關懷與視野,形塑一代學術之新貌,卻是具有拓展文化的可貴價值。因此,在這看似失落的時刻裡,實質上蘊藏著劃定一代學術發展之要素而有待挖掘。
學術界有所謂「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的說法,作為一個朝代,唐代是如何發展成一個具有特殊性的「唐型文化」?如果,學術像是一個生命體,那麼初始的奠基,或將形塑其根本的性格。換言之,在初唐時期,關於學術文化的思考,是值得令人深入探究的。例如羅宗強在《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中即肯定唐太宗和他們的重臣們為唐代文學的發展,奠定了很好的思想基礎。不過,整體而言,對於初唐時期學術文化的詮釋與掌握,仍欠缺一個精彩的關注視角。
根據《唐會要》的說法,《群書治要》一書是在貞觀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由魏徵等人編撰而成,並詳述云:
太宗欲覽前王得失。爰自六經,訖于諸子,上始五帝,下盡晉年。徵與虞世南、褚亮、蕭德言等始成凡五十卷。上之。諸王各賜一本。
藉此,可以形成以下四點推想:其一,《群書治要》的編纂是在唐太宗「欲覽前王得失」的情形下所發起,則上之所好,下必從之,對於學術文化的投注,勢將形成風尚。其二,就編纂的時間來看,屬於新時代的開端,其中正蘊含著新舊並存的思維內涵。新的視野,或尚疏淺,然而以其蘊含帶來巨變之契機,彌足珍貴。其三,視野所及,包含了經、史與諸子,層面之廣,可以視為是融攝文化傳統的一個嘗試。其四,就編纂者而言,魏徵、虞世南、褚亮與蕭德言四人,不僅學識淵博、學術涵養深厚,並且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舉如唐太宗所云:「貞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玄齡之功無所與讓;貞觀之後,盡心於我,獻納忠讜,安國利人,成我今日功業,為天下所稱者,惟魏徵而已。」作為輔成要角,魏徵等人所編撰之《群書治要》,理當蘊含契合走向盛世的思維內涵。由此而言,《群書治要》深具價值與意義。
然而,從《群書治要》的傳播與影響來看,不免令人產生疑惑。一方面,成書後的《群書治要》並未獲得廣泛的流行與儒者的討論,南宋時即見散佚之說,元代後當已不傳,今日所見乃清嘉慶年間由日本回傳到中土的版本,藉此可見《群書治要》長期被漠視的現象。另一方面,以關注《群書治要》的視角來說,最為突出的面向,就是文獻學的掌握方式,而流傳於日本的特殊性,讓中日文化的交流得到新的內涵,也有採用特殊視角來探討《群書治要》蘊含意義的空間。不過,就目前關於《群書治要》的四類研究:其一,以《群書治要》為對象,進行較為全面的展示,舉如周少文《《群書治要》研究》與金光一《《群書治要》研究》。 其次,擷取某個面向進行《群書治要》的分析與詮釋,舉如呂效祖〈《群書治要》及中日文化交流〉、吳剛《從《群書治要》看貞觀君臣的治國理念》、洪觀智《《群書治要》史部研究─從貞觀史學的致用精神談起》、潘銘基〈「昭德塞違,勸善懲惡」─論《群書治要》所引先秦諸子與治國之道〉等。其三,以文獻學的角度,著重於文獻保存的價值。除周少文與金光一亦有著墨外,舉如張蓓蓓〈略論中古子籍的整理──從嚴可均的工作談起〉、吳金華〈略談日本古寫本《群書治要》的文獻學價值〉、林溢欣〈從《群書治要》看唐初《孫子》版本系統──兼論《孫子》流傳、篇目次序等問題〉、王維佳《《群書治要》的回傳與嚴可均的輯佚成就》等。其四,著重於實踐的推廣。舉如劉余莉、谷文國〈《群書治要》的得人之道〉、劉余莉、劉紅利〈《群書治要》論奢靡之害〉等。 諸多研究成果,仍舊無法彰顯位處於「初唐時期」之《群書治要》所蘊含的獨特價值與意義。
為彰顯《群書治要》蘊含著思維脈絡與時代特色,本文擬透過《群書治要》的梳理,審視其編纂型態與編纂宗旨,期盼能明晰《群書治要》所存在的思維架構與特殊取向。
二、《群書治要》的編纂型態
《群書治要》所呈現的樣貌究竟有何特色而值得探究呢?有關於此,可以從幾個方面來進行掌握:(一)典籍的性質。(二)取材的範圍。(三)選編的內容。(四)撰寫的方式。以下分別詳細說明。
(一)典籍的性質
根據〈群書治要序〉一文中所述:
但《皇覽》、《遍略》,隨方類聚,名目互顯,首尾淆亂,文義斷絶,尋究爲難。今之所撰,異乎先作,總立新名,各全舊體,欲令見本知末,原始要終,并弃彼春華,采茲秋實。一書之内,牙角無遺;一事之中,羽毛咸盡。
從與《皇覽》、《遍略》的類比而言,《群書治要》的性質,當與之類似。然而,若因此等同視之,卻是魏徵等人所無法認同的。原因在於:《皇覽》是中國類書的始祖,與《遍略》一樣,是以「直書其事」、「隨方類聚」的方式來呈現,大體而言,屬於一種方便查驗資料的工具書,唐初即大量編輯這種類書,應與當時詩文創作大量徵集詞藻典故的需要,有著密切的關聯。顯然,在編輯意識上魏徵等人清楚地想要有所區隔,企圖展現出不同的意義,所謂「異乎先作」即是。
何謂「異乎先作」?焦點即在於內容之「文義」的呈現上。不同於僅止於追求可觀之詞藻,致使置「文義斷絕」於不顧,《群書治要》的編纂即反過來重視「文義」的完整性,秉持要能知本末、見始終的原則,將原有的「體」保存下來,最終在選錄的內容上展現出「一書之内,牙角無遺;一事之中,羽毛咸盡。」的全面性與完整性。
有關《群書治要》的特殊性,聞一多在討論類書時已有所關注,其云:
章句家是書簏,類書家也是書簏,章句家是「釋事而忘意」,類書家便是「采事而忘意」了。我這種說法並不苛刻。只消舉出《群書治要》來和《北堂書鈔》或《藝文類聚》比一比,你便明白。同是鈔書,同是一個時代的產物,但拿來和《治要》的「主意」的質素一比,《書鈔》或《類聚》「主事」的質素便顯著格外分明了。
《北堂書鈔》,雖也是由虞世南所撰作,但根據劉禹錫的說法,乃是「集群書中事可為文用者」,正如聞一多的判斷,著重於「采事」而忘了所存之「意」。至於《藝文類聚》,乃歐陽詢所撰,雖「比類相從,事居於前,文列於後」,合《皇覽》與《文選》之兩長,但性質依舊與《北堂書鈔》近似,聞一多就認為扣除了詩賦文部分,《藝文類聚》便等於是《北堂書鈔》了,其間的差異更可視為是類書的進化史。 迥異於《北堂書鈔》與《藝文類聚》的「主事」,《群書治要》展現出「主意」的質素,聞一多確實凸顯出《群書治要》在編撰時,就存有一「文義」關注的核心思維。
綜上所述,《群書治要》雖被劃歸為類書,但是在以「文義」為主軸的呈現下,讓人無法迴避其保存舊「體」的特殊性,並順此而思考到其中是否蘊含魏徵等人編撰之「意」呢?若是,則《群書治要》是否即具有「以編代作」之特殊性的意涵呢?
(二)取材的範圍
《群書治要》在編撰成書時共有五十卷,依據〈群書治要序〉一文中的敘述,文曰:
爰自六經,訖乎諸子,上始五帝,下盡晉年。凡爲五帙,合五十卷。(〈群書治要序〉,頁2)
所以五十卷的《群書治要》,選錄典籍的時間區段,是從「五帝」開始,直至「晉」為止。至於選錄的內容,從「六經」到「諸子」,詳細來說,包括了「經」、「史」與「子」,橫跨三部的典籍。具體選錄的典籍,整理如下表:
次序 書名 次序 書名 次序 書名 次序 書名
1 周易 2 尚書 3 毛詩 4 左傳
5 禮記 6 周禮 7 周書 8 國語
9 韓詩外傳 10 孝經 11 論語 12 孔子家語
13 史記 14 吳越春秋 15 漢書 16 後漢書
17 魏志 18 蜀志 19 吳志 20 晉書
21 六韜 22 陰謀 23 鬻子 24 管子
25 晏子 26 司馬法 27 孫子兵法 28 老子
29 鶡冠子 30 列子 31 墨子 32 文子
33 曾子 34 吳子 35 商君書 36 尸子
37 申子 38 孟子 39 慎子 40 尹文子
41 莊子 42 尉繚子 43 孫卿子 44 呂氏春秋
45 韓子 46 三略 47 新語 48 賈子
49 淮南子 50 鹽鐵論 51 新序 52 說苑
53 桓子新論 54 潛夫論 55 崔寔政論 56 仲長子昌言
57 申鑒 58 中論 59 典論 60 劉廙政論
61 蔣子萬機論 62 政要論 63 體論 64 時務論
65 典語 66 傅子 67 袁子正書 68 抱朴子
根據上表所示,《群書治要》選錄的典籍來源,合計共有六十八部著作。其中,卷一至卷十所收為屬於「經」的十二部著作,即次序1~12,卷十一至卷三十所收為屬於「史」的八部著作,即次序13~20,而卷三十一至卷五十所收為屬於「子」的四十八部著作,即次序21~68。目前可見版本僅有四十七卷,卷四之《春秋左氏傳》(上)、卷十三之《漢書》(一)與卷二十之《漢書》(八)三卷已亡佚,雖有缺憾,但並無礙於對選錄標的的掌握。 至於「子」的四十八部著作,依據《隋書・經籍志》的流派來看,屬於儒家者,有十七部,數量上最多;屬於道家者,有六部;屬於墨家者,有一部;屬於法家者,有八部;屬於名家者,有一部;屬於雜家者,有九部,份量上僅次於儒家;屬於兵家者,有六部,與道家等量齊觀。大體而言,儒家依舊具有主流地位而佔有較大的份量,不過道家、法家、雜家、兵家的份量,透露出《群書治要》在內涵上存在著多元而複雜的質素。
若依據《隋書・經籍志》的說法:「今考見存,分為四部,合條為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魏徵等人當時面對的典籍數量大致與此貼近,即使「經」、「史」兩部受限於傳統文化所形成的認知框架,致使擇取空間相對較小,但以最終僅擇取六十八部著作來說,經過了精挑細選,其間必然存在著相通、相同的質素,始能共同建構起《群書治要》的思維殿堂。
因此,根據選錄著作的質量來看,《群書治要》存在著值得深入挖掘的意藴。
(三)選編的內容
進一步觀察《群書治要》針對所收錄之六十八部著作的處理情形,可以看到去取間呈現出各自不同的跡象,以下分別由「經」、「史」、「子」三大部分來進行呈現:
1.「經」部方面
乾、坤、屯、蒙、師、比、履、泰、否、同人、大有、謙、豫、隨、觀、噬嗑、賁、大畜、頤、習坎、離、咸、恒、遯、大壯、晉、明夷、家人、睽、蹇、解、損、益、升、革、鼎、震、艮、豐、兌、渙、節、中孚、小過、既濟
繫辭(上)、繫辭(下)
說卦傳
六十四卦方面,擇取了其中的四十五卦,除乾、坤兩卦最後分別附有〈文言〉外,每卦後多兼有〈象〉、〈彖〉,且先〈象〉而後〈彖〉,少部分單取〈象〉而無〈彖〉,至於單獨附〈彖〉的情形,並未見到。關於未收錄的十九卦,分別為:需、訟、小畜、蠱、臨、剝、復、无妄、大過、夬、姤、萃、困、井、漸、歸妹、旅、巽、未濟。僅就卦的數量來說,選錄的比例約佔七成,且選錄內容並未見穿插、錯亂之現象,依去取之跡象已可見編撰之用心。
其次,以《尚書》而言,《群書治要》引錄的資料依序為:
虞書 堯典、舜典、大禹謨、皋陶謨、益稷〔謨〕
夏書 五子之歌
商書 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說命上、說命中、說命下
周書 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牧誓、武成、旅獒、康誥、酒誥、無逸、蔡仲之命、多方、立政、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呂刑
以上資料,乃是依據《群書治要》所選錄內容,核對《尚書》原本篇章所得,共關涉三十四個篇章。至於,未觸及內容的篇章有:
夏書 禹貢、甘誓、胤征
商書 湯誓、盤庚上、盤庚中、盤庚下、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
周書 洪範、金縢、大誥、微子之命、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君奭、顧命、康王之誥、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合計共有二十四個篇章的內容並未被《群書治要》所節錄。依據篇章的比例來說,被選錄的篇章,約佔總篇章的有五成八,與《易》相較,取捨更加鮮明,編纂之意值得玩味。
又次,以《毛詩》而言,《群書治要》所引錄的資料,詳細情形如下:
周南 關雎、卷耳
邵南 甘棠、何彼襛矣
鄁風 柏舟、谷風
鄘風 相鼠、干旄
衛風 淇澳、芄蘭
王風 葛藟、采葛
鄭風 風雨、子衿
齊風 雞鳴、甫田
魏風 伐檀、碩鼠
唐風 杕杜
秦風 晨風、渭陽、權輿
曹風 蜉蝣、候人
小雅 鹿鳴、皇皇者華、常棣、伐木、天保、南山有臺、蓼蕭、淇露、六月、車攻、鴻雁、白駒、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小旻、小宛、小弁、巧言、巷伯、谷風、蓼莪、北山、青蠅、賓之初筵、采菽、角弓、菀柳、隰桑、白華、何草不黃
大雅 文王、大明、思齊、靈臺、行葦、假樂、民勞、板、蕩、抑、桑柔、雲漢、崧高、烝民、瞻仰
周頌 清廟、振鷺、雍、有客、敬之
魯頌 閟宮
商頌 長發、殷武
《群書治要》在《毛詩》的編寫內容上,標明各國國風,如「周南」、「邵南」等,並引錄了詩大序與小序的內容。依據上表所示,《群書治要》共選錄了七十八首作品,其中於「風」之十五國風選取了十二國風,排除了〈陳〉、〈檜〉與〈豳〉,共有二十四首作品;於「雅」之〈大雅〉、〈小雅〉中擇取了四十六首作品;於「頌」之〈周頌〉、〈魯頌〉、〈商頌〉中擷取了八首作品。整體來說,《群書治要》在選錄《毛詩》上,幾乎兼顧其本身的完整性,符合序文所謂「各全舊體」的想法。至於作品選錄的比例,依據《詩經》三百零五篇來說,僅佔約兩成五,嚴選的跡象傳達出魏徵等人特殊的編選關懷。
又次,以《春秋左氏傳》而言,《群書治要》所引錄的情形如下:
春秋左氏傳(上) 佚
春秋左氏傳(中) 宣公 二年、三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五年、十六年
成公 二年、六年、八年、十六年
襄公 三年、四年、九年、十一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二十五年、二十六年、二十七年、二十九年、三十年、三十一年
春秋左氏傳(下) 昭公 元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二年、十三年、十五年、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五年、二十六年、二十七年、二十八年
定公 四年、五年、九年
哀公 元年、六年、十一年、十四年、二十四年
《春秋左氏傳》(上)為《群書治要》卷四,已佚,無法掌握其選錄狀態。至於其他部分,核對於《春秋左氏傳》,宣公原記載了十八年,《群書治要》選錄了其中的六年;成公原亦記載了十八年,《群書治要》選錄了其中的四年;襄公原記載了三十一年,《群書治要》選錄了其中的十五年;昭公原記載了三十二年,《群書治要》選錄了其中的十八年;定公原記載了十五年,《群書治要》選錄了其中的三年;哀公原記載了二十七年,《群書治要》選錄了其中的五年。依據以上所得資料,以「年」之時間單位為計算基礎,《群書治要》選錄《春秋左氏傳》的比例,約佔有三成六。雖然擇取有偏重於襄公與昭公的現象,但即使僅就兩公記載而言,擇取比例亦分別僅有約四成八與五成六而已,與《書》的情形貼近。值得提出的是:《春秋左氏傳》被截錄的內容,不僅多以對話的生動形式呈現,並且展現出顯著的「表意」作用。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群書治要》與貞觀精神的圖書 |
 |
《群書治要》與貞觀精神 作者:張瑞麟 出版社: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3-09-25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群書治要》與貞觀精神
在保存古代珍貴文獻的價值之外,實際上《群書治要》具有屬於自身更加精彩的思想內容與映照的時代精神。魏徵等人採用「以編代作」的方式,一方面承繼了文化傳統,一方面又賦予了時代新意。
本書五個篇章,憑藉《貞觀政要》,以「文脈」結合「語境」的解讀方式,剖析《群書治要》的思想內涵,不僅得以契會魏徵的治政理念,亦能深入掌握貞觀的時代精神。此外,以〈看見《群書治要》〉一文代序,綜述《群書治要》的研究方法與開展方向。
商品特色
透過《貞觀政要》,
契會魏徵的治政理念,
掌握貞觀的時代精神,
看見屬於《群書治要》自身的精彩。
作者簡介:
張瑞麟
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
私立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
經歷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逢甲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香港浸會大學孫少文伉儷人文中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現職博識投資有限公司董事
研究領域
宋代學術、韓愈學術、《群書治要》
著作
《理解宋學:從韓愈看起》
合編《第一屆《群書治要》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合編《續纂群書治要》
章節試閱
【第一章】 轉舊為新──《群書治要》的編纂與意義
一、前言
回顧歷史,在朝代交替的時間區段中,對於文化的發展多具有關鍵性意義。戰火的洗禮,打破了學術文化穩定發展的走向,雖然典籍的焚棄與人才短缺等問題,常使新朝代在初始時顯得貧乏、失色,但伴隨而來的審視,汰除臃腫、無味、失根的學術內容,重新以不同的關懷與視野,形塑一代學術之新貌,卻是具有拓展文化的可貴價值。因此,在這看似失落的時刻裡,實質上蘊藏著劃定一代學術發展之要素而有待挖掘。
學術界有所謂「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的說法,作為一個朝代,唐代是如...
一、前言
回顧歷史,在朝代交替的時間區段中,對於文化的發展多具有關鍵性意義。戰火的洗禮,打破了學術文化穩定發展的走向,雖然典籍的焚棄與人才短缺等問題,常使新朝代在初始時顯得貧乏、失色,但伴隨而來的審視,汰除臃腫、無味、失根的學術內容,重新以不同的關懷與視野,形塑一代學術之新貌,卻是具有拓展文化的可貴價值。因此,在這看似失落的時刻裡,實質上蘊藏著劃定一代學術發展之要素而有待挖掘。
學術界有所謂「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的說法,作為一個朝代,唐代是如...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代序:看見《群書治要》】
為什麼要關注《群書治要》呢?因為:「唐型文化形塑於貞觀時期,《群書治要》潛存著貞觀精神。」過往,《群書治要》被視為類書,因而看不見它的「時代性」,也就無法理解其中蘊含的特殊意義。因此,需要重新審視以看見《群書治要》的精彩。
「您認識《群書治要》嗎?」還記得剛開始要和大家分享《群書治要》的研究心得時,得到的回應卻是:「您指的是哪幾本書呢?」顯然,多數人對於《群書治要》是感到陌生的。我之所以熟悉,也是因為淨空上人的關注,藉著與業師林朝成教授一起承接極樂寺委託研究案的機...
為什麼要關注《群書治要》呢?因為:「唐型文化形塑於貞觀時期,《群書治要》潛存著貞觀精神。」過往,《群書治要》被視為類書,因而看不見它的「時代性」,也就無法理解其中蘊含的特殊意義。因此,需要重新審視以看見《群書治要》的精彩。
「您認識《群書治要》嗎?」還記得剛開始要和大家分享《群書治要》的研究心得時,得到的回應卻是:「您指的是哪幾本書呢?」顯然,多數人對於《群書治要》是感到陌生的。我之所以熟悉,也是因為淨空上人的關注,藉著與業師林朝成教授一起承接極樂寺委託研究案的機...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代序:看見《群書治要》
一、傾聽作者的聲音:不容忽視的〈序〉
二、看見作品的精彩
三、貞觀精神與唐型文化
四、連結生活以譜寫新章
第一章 轉舊為新──《群書治要》的編纂與意義
一、前言
二、《群書治要》的編纂型態
三、《群書治要》編纂主題與宗旨
四、《群書治要》編纂的視野與意義
五、結語
第二章 立名存思──關於《群書治要》的編纂、傳播與接受
一、前言
二、關於《群書治要》的編纂
三、《群書治要》的傳播
四、《群書治要》的接受
五、結論
第三章 《群書治要》選編《墨子》的意蘊──從初期墨學...
一、傾聽作者的聲音:不容忽視的〈序〉
二、看見作品的精彩
三、貞觀精神與唐型文化
四、連結生活以譜寫新章
第一章 轉舊為新──《群書治要》的編纂與意義
一、前言
二、《群書治要》的編纂型態
三、《群書治要》編纂主題與宗旨
四、《群書治要》編纂的視野與意義
五、結語
第二章 立名存思──關於《群書治要》的編纂、傳播與接受
一、前言
二、關於《群書治要》的編纂
三、《群書治要》的傳播
四、《群書治要》的接受
五、結論
第三章 《群書治要》選編《墨子》的意蘊──從初期墨學...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