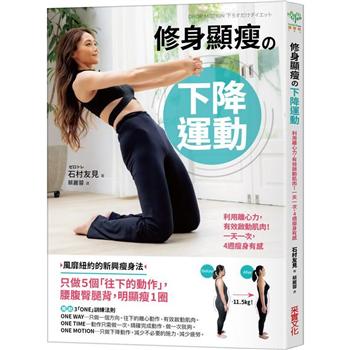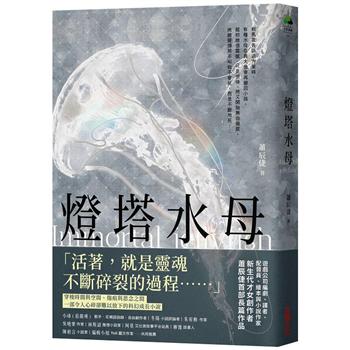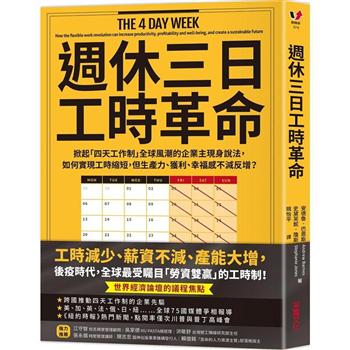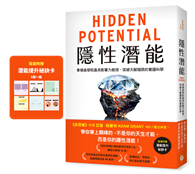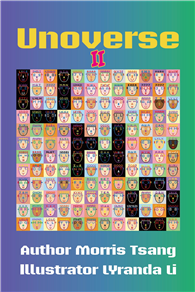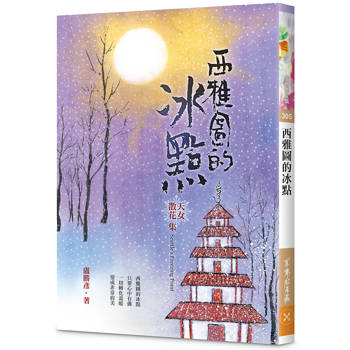任何國家對決於戰場,影響勝負的因素絕非軍隊有多強大,抑或國家領導人、指揮官有多麼睿智而已。本書關心的主題在於宣傳與戰爭究竟有何關係、宣傳在戰爭中占著什麼樣的位置,以及宣傳在戰爭中究竟有哪些值得我們注意的演進與變化。
本書採歷史與文獻分析法、敘事分析法,分別探討宣傳戰與公關化戰爭的演進,以此歷史分析的發現為基礎,進一步檢視美、英兩國(以美國為主)在兩次波斯灣戰爭中遂行公關化戰爭的媒體管理、媒體運用、訊息規劃等策略與作為,以及對伊拉克「推倒海珊銅像」進行假事件分析。
本書特色
縱使宣傳是「必要之惡」,卻有一善,「一個好的宣傳戰略可能會節省一年的戰爭。這意味著會節省上千萬英鎊,無疑還有上百萬人的生命。」(《泰晤士報》,1918.10.31.)
人類的戰爭若少了宣傳,那所需付出的後果與代價,豈不更難想像!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宣傳與戰爭:從「宣傳戰」到「公關化戰爭」的圖書 |
 |
宣傳與戰爭:從「宣傳戰」到「公關化戰爭」 作者:方鵬程 出版社: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5-03-20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462頁 / 17 x 23 x 1.9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89 |
軍事戰略 |
$ 558 |
戰略/戰役 |
$ 558 |
中文書 |
$ 558 |
政治 |
$ 558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宣傳與戰爭:從「宣傳戰」到「公關化戰爭」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方鵬程
學歷
臺灣師範大學法學博士
經歷
曾任記者、採訪編輯、中央文工會編審、臺灣省政府參議兼編譯室主任、《臺灣新生報》副社長、台電公司董事、臺北市報業同業公會理事、國防大學新聞系副教授兼系主任、雲林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臺灣藝術大學兼任助理教授等職。
著作
《戰爭傳播:一個「傳播者」取向的研究》(2007)、《蔣經國祕書報告》(2018)、《從威權邁向開放民主:臺灣民主化關鍵歷程1988-1993》(2019)、《公門好修行:臺灣史上唯一民選省長宋楚瑜工作實錄》(2023)等書。曾主編《軍事傳播媒介實務:企劃知識與實作要領》(2013)、《軍隊危機傳播15講》(2015)、《軍隊公共事務15講》(2016)、《始終如一:新聞人朱宗軻憶往文集》(2025)等書。
方鵬程
學歷
臺灣師範大學法學博士
經歷
曾任記者、採訪編輯、中央文工會編審、臺灣省政府參議兼編譯室主任、《臺灣新生報》副社長、台電公司董事、臺北市報業同業公會理事、國防大學新聞系副教授兼系主任、雲林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臺灣藝術大學兼任助理教授等職。
著作
《戰爭傳播:一個「傳播者」取向的研究》(2007)、《蔣經國祕書報告》(2018)、《從威權邁向開放民主:臺灣民主化關鍵歷程1988-1993》(2019)、《公門好修行:臺灣史上唯一民選省長宋楚瑜工作實錄》(2023)等書。曾主編《軍事傳播媒介實務:企劃知識與實作要領》(2013)、《軍隊危機傳播15講》(2015)、《軍隊公共事務15講》(2016)、《始終如一:新聞人朱宗軻憶往文集》(2025)等書。
目錄
自 序
第壹篇 導論篇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從「宣傳」說起
第二節 「宣傳戰」與「公關化戰爭」的定義
第三節 戰爭型態的演進與本書歷史階段劃分
第四節 研究旨趣、研究問題與研究方法
第五節 本書章節架構
第二章 宣傳與戰爭研究的理論基礎
第一節 宣傳與戰爭的研究取向
第二節 政治作戰與軍事說服理論
第三節 公共關係與軍隊公共事務
第四節 群眾心理學與民意研究
第五節 新媒介發展與公關化戰爭研究的結合
第六節 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
第七節 中文文獻檢視與結論
第貳篇 歷史回溯篇
第三章 宣傳戰的歷史演進
第一節 前言
第二節 相關文獻檢視
第三節 帝國主義時期
第四節 革命戰爭與殖民戰爭時期
第五節 總體戰爭時期
第六節 冷戰時期
第七節 結論
第四章 公關化戰爭的發展歷程
第一節 前言
第二節 相關文獻檢視
第三節 孕育公關化戰爭的越戰
第四節 冷戰時期的公關化戰爭
第五節 後冷戰時期的公關化戰爭
第六節 結論
第參篇 公關化戰爭篇
第五章 公關化戰爭的媒體管理策略分析:以兩次波斯灣戰爭的美軍作為為例
第一節 前言
第二節 相關文獻檢視
第三節 1991年波斯灣戰爭的媒體管理策略分析
第四節 2003年波斯灣戰爭的媒體管理策略分析
第五節 結論
第六章 公關化戰爭的媒體運用策略分析:以兩次波斯灣戰爭的美軍作為為例
第一節 前言
第二節 相關文獻檢視
第三節 1991年波斯灣戰爭的媒體運用策略分析
第四節 2003年波斯灣戰爭的媒體運用策略分析
第五節 結論
第七章 公關化戰爭的訊息規劃策略分析:以兩次波斯灣戰爭的美軍作為為例
第一節 前言
第二節 相關文獻檢視
第三節 戰爭正當化的訊息規劃策略分析
第四節 敵我二元對立的訊息規劃策略分析
第五節 新聞淨化及消除記憶的訊息規劃策略分析
第六節 大後方「支持軍隊」的訊息規劃策略分析
第七節 結論
第八章 2003年巴格達市「推倒海珊銅像」的假事件分析
第一節 前言
第二節 相關文獻檢視
第三節 推倒海珊銅像事件的敘事分析
第四節 對宣傳與戰爭中假事件的檢討
第五節 結論
第肆篇 結語篇
第九章 公關化戰爭的過去與未來
第一節 本書研究總結
第二節 對公關化戰爭發展的觀察與思考
第三節 公關化戰爭的適用性、借鏡與未來研究建議
參考書目
第壹篇 導論篇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從「宣傳」說起
第二節 「宣傳戰」與「公關化戰爭」的定義
第三節 戰爭型態的演進與本書歷史階段劃分
第四節 研究旨趣、研究問題與研究方法
第五節 本書章節架構
第二章 宣傳與戰爭研究的理論基礎
第一節 宣傳與戰爭的研究取向
第二節 政治作戰與軍事說服理論
第三節 公共關係與軍隊公共事務
第四節 群眾心理學與民意研究
第五節 新媒介發展與公關化戰爭研究的結合
第六節 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
第七節 中文文獻檢視與結論
第貳篇 歷史回溯篇
第三章 宣傳戰的歷史演進
第一節 前言
第二節 相關文獻檢視
第三節 帝國主義時期
第四節 革命戰爭與殖民戰爭時期
第五節 總體戰爭時期
第六節 冷戰時期
第七節 結論
第四章 公關化戰爭的發展歷程
第一節 前言
第二節 相關文獻檢視
第三節 孕育公關化戰爭的越戰
第四節 冷戰時期的公關化戰爭
第五節 後冷戰時期的公關化戰爭
第六節 結論
第參篇 公關化戰爭篇
第五章 公關化戰爭的媒體管理策略分析:以兩次波斯灣戰爭的美軍作為為例
第一節 前言
第二節 相關文獻檢視
第三節 1991年波斯灣戰爭的媒體管理策略分析
第四節 2003年波斯灣戰爭的媒體管理策略分析
第五節 結論
第六章 公關化戰爭的媒體運用策略分析:以兩次波斯灣戰爭的美軍作為為例
第一節 前言
第二節 相關文獻檢視
第三節 1991年波斯灣戰爭的媒體運用策略分析
第四節 2003年波斯灣戰爭的媒體運用策略分析
第五節 結論
第七章 公關化戰爭的訊息規劃策略分析:以兩次波斯灣戰爭的美軍作為為例
第一節 前言
第二節 相關文獻檢視
第三節 戰爭正當化的訊息規劃策略分析
第四節 敵我二元對立的訊息規劃策略分析
第五節 新聞淨化及消除記憶的訊息規劃策略分析
第六節 大後方「支持軍隊」的訊息規劃策略分析
第七節 結論
第八章 2003年巴格達市「推倒海珊銅像」的假事件分析
第一節 前言
第二節 相關文獻檢視
第三節 推倒海珊銅像事件的敘事分析
第四節 對宣傳與戰爭中假事件的檢討
第五節 結論
第肆篇 結語篇
第九章 公關化戰爭的過去與未來
第一節 本書研究總結
第二節 對公關化戰爭發展的觀察與思考
第三節 公關化戰爭的適用性、借鏡與未來研究建議
參考書目
序
自序
美國有一位評論家曾言:「戰爭是殘酷的,無論如何都無法將它掩飾。」雖是如此,戰爭始終存在,戰爭的故事總是有人傳頌,戰爭的小說或電影仍是擁有無數熱情的讀者與觀眾。
人類為何有戰爭,這不是本書探討的主題,本書關心的是宣傳與戰爭究竟有何關係、宣傳在戰爭中占著什麼樣的位置,以及宣傳在戰爭中究竟有哪些值得我們注意的演進與變化。而在本書中,可以看到各個不同的歷史階段中,宣傳者以最新的傳播技術與方法,將軍隊凝聚成可戰之師,將平民團結成支援前線的後盾長城,甚至演進到越戰以後,美化戰爭與醜化敵人已是師出有名與克敵致勝不可或缺的策略與作為。
古往今來,任何國家對決於戰場,影響勝負的因素不止一端,箇中關鍵絕非僅是軍隊有多麼強大或國家領導人、指揮官有多麼睿智而已,若少了平民的支持與認同,軍隊士氣無以維繫提振,再強大的軍隊終將得不到勝利。然而,軍隊的兵員來自於平民,軍隊的武器物資由平民來供應,那平民的支持與認同又從何而來?拉斯威爾(H. D. Lasswell)如是說:「要將平民團結起來,不能靠人身控制,也不能靠重複的社會運動,只能藉著共同的信念與想法;平民的信念與想法是透過媒體報導,而非軍事訓練,才被統一起來的。」
儘管迄今人類社會中的宣傳無所不在,無時無刻不在進行,卻由於歷史經驗的因素,「宣傳」一直是令人不喜歡的字眼,宣傳者更是以不同說法、不同運用的方式,來模糊其與宣傳之間的關聯。本書嘗試整理相關的學術名詞,藉以梳理人類戰爭宣傳由宣傳戰邁向公關化戰爭的發展歷程。縱使宣傳是「必要之惡」,卻有一善,誠如《泰晤士報》在簽定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協定前11天的 1918年10月31日曾刊載的一個總結:「一個好的宣傳戰略可能會節省一年的戰爭。這意味著會節省上千萬英鎊,無疑還有上百萬人的生命。」試想,人類的戰爭若少了宣傳,那所需付出的後果與代價,豈不更難以想像!
大眾傳播研究的理論取向主要有「行政性」與「批判性」兩種。前者是以共識為前提,從機構組織的角度為出發點,著重於如何提升行政效能與有效運作;後者則以政經結構、意識形態、權力宰制等為重點,為前者的替代性典範。在宣傳研究上,除人文主義者反宣傳立場外,又可大致區分經驗學派一貫客觀中立的研究態度、專業主義的宣傳觀、新自由主義對政府和企業的宣傳策略與媒體的壟斷集中進行批判。基本上,作者任教於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新聞系,基於平日的教學與多年工作經驗,採取行政性研究的理論取向,並將宣傳視為專業主義的作為,亦期許研究成果能對教學或軍隊實務工作有所裨益,並非刻意忽略批判性研究的觀點與啟發。
本書是作者從事軍事新聞傳播教育與研究工作一些綜合成果的呈現,其中第三章宣傳戰歷史演進的部分內容(第二、第五及第六節)及第六章公關化戰爭的媒體運用策略分析的部分內容(第二、第四節),曾發表於《復興崗學報》第98期、97期。第四章公關化戰爭發展歷程及第五章公關化戰爭的媒體管理策略分析的精簡內容則曾發表於《復興崗學報》第92期、94期。另,第七章兩次波斯灣戰爭的訊息規劃策略分析的主要內容曾發表於「第四屆軍事新聞學術研討會」(2010年9月8日,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與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共同舉辦);第八章2003年巴格達市「推倒海珊銅像」的假事件分析曾發表於「2009傳播科技與軍事傳播研討會」(2009年5月21日,國防大學與世新大學共同舉辦),並刊載於《2009傳播科技與軍事傳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年7月,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出版)。
本書共分為四篇、九章節。第壹篇(第一至二章),是本書的研究旨趣、研究問題、研究方法、本書章節架構及本書的理論基礎的陳述。第貳篇(第三及四章)為歷史回溯篇,探討宣傳戰與公關化戰爭的歷史演進。宣傳戰從西方歷史上的主要戰爭中,依序回溯帝國主義時期、革命戰爭與殖民戰爭時期、總體戰爭時期、冷戰時期四個階段的發展情形。公關化戰爭從孕育到成熟,係以越戰為起始點,探論冷戰時期及後冷戰時期兩個階段的發展情形。第參篇(第五至八章)為公關化戰爭篇,是以上一篇歷史分析的研究發現為基礎,進一步檢視美英兩國(以美國為主)在兩次波斯灣戰爭中遂行公關化戰爭的媒體管理、媒體運用、訊息規劃及媒體假事件等重要策略與作為。第肆篇(第九章)為結語篇,係對本書各章的探討與論述做出總結陳述,並提出一些對宣傳與戰爭的研究心得與看法,以及本書的研究限制與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本書寫作過程中,多承作者任教系所劉建鷗主任、徐蕙萍主任、樓榕嬌主任、張梅雨主任、謝奇任主任、陳竹梅老師惠賜寶貴意見,時任世新大學胡光夏教授兼主任熱心指教與協助,以及前國防部軍事發言人暨銘傳大學新聞系副教授吳奇為將軍、軍聞社社長田文輝上校、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吳冠輝副教授、玄奘大學新聞系主任延英陸、文化大學廣告系陶聖屏副教授、前東森電視總經理暨副董事長朱宗軻先生、臺灣中小企業聯合輔導基金會董事長馬傑明先生、前台灣新聞報兼台灣新生報社長趙立年先生、前中央社社長汪萬里先生、前中廣公司花蓮台台長吳晶晶女士等多位師長、同仁、友好的勉勵與督促;又有勞劉建鷗教授、謝奇任主任及銘傳大學劉久清主任百忙中抽空閱讀,並給予寶貴建言與指正,均銘感於心。
本書撰寫時間,特別感謝內人廖麗雪提供無後顧之憂的關心與照顧,小女珮璇、沛樺及芊畬幫忙借還書與校對等工作;本書得以出版,承蒙警察大學陳添壽教授推介,以及元華文創主編李欣芳小姐多所協助,併此誌謝,尚祈各方先進對任何疏漏不吝賜教。
美國有一位評論家曾言:「戰爭是殘酷的,無論如何都無法將它掩飾。」雖是如此,戰爭始終存在,戰爭的故事總是有人傳頌,戰爭的小說或電影仍是擁有無數熱情的讀者與觀眾。
人類為何有戰爭,這不是本書探討的主題,本書關心的是宣傳與戰爭究竟有何關係、宣傳在戰爭中占著什麼樣的位置,以及宣傳在戰爭中究竟有哪些值得我們注意的演進與變化。而在本書中,可以看到各個不同的歷史階段中,宣傳者以最新的傳播技術與方法,將軍隊凝聚成可戰之師,將平民團結成支援前線的後盾長城,甚至演進到越戰以後,美化戰爭與醜化敵人已是師出有名與克敵致勝不可或缺的策略與作為。
古往今來,任何國家對決於戰場,影響勝負的因素不止一端,箇中關鍵絕非僅是軍隊有多麼強大或國家領導人、指揮官有多麼睿智而已,若少了平民的支持與認同,軍隊士氣無以維繫提振,再強大的軍隊終將得不到勝利。然而,軍隊的兵員來自於平民,軍隊的武器物資由平民來供應,那平民的支持與認同又從何而來?拉斯威爾(H. D. Lasswell)如是說:「要將平民團結起來,不能靠人身控制,也不能靠重複的社會運動,只能藉著共同的信念與想法;平民的信念與想法是透過媒體報導,而非軍事訓練,才被統一起來的。」
儘管迄今人類社會中的宣傳無所不在,無時無刻不在進行,卻由於歷史經驗的因素,「宣傳」一直是令人不喜歡的字眼,宣傳者更是以不同說法、不同運用的方式,來模糊其與宣傳之間的關聯。本書嘗試整理相關的學術名詞,藉以梳理人類戰爭宣傳由宣傳戰邁向公關化戰爭的發展歷程。縱使宣傳是「必要之惡」,卻有一善,誠如《泰晤士報》在簽定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協定前11天的 1918年10月31日曾刊載的一個總結:「一個好的宣傳戰略可能會節省一年的戰爭。這意味著會節省上千萬英鎊,無疑還有上百萬人的生命。」試想,人類的戰爭若少了宣傳,那所需付出的後果與代價,豈不更難以想像!
大眾傳播研究的理論取向主要有「行政性」與「批判性」兩種。前者是以共識為前提,從機構組織的角度為出發點,著重於如何提升行政效能與有效運作;後者則以政經結構、意識形態、權力宰制等為重點,為前者的替代性典範。在宣傳研究上,除人文主義者反宣傳立場外,又可大致區分經驗學派一貫客觀中立的研究態度、專業主義的宣傳觀、新自由主義對政府和企業的宣傳策略與媒體的壟斷集中進行批判。基本上,作者任教於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新聞系,基於平日的教學與多年工作經驗,採取行政性研究的理論取向,並將宣傳視為專業主義的作為,亦期許研究成果能對教學或軍隊實務工作有所裨益,並非刻意忽略批判性研究的觀點與啟發。
本書是作者從事軍事新聞傳播教育與研究工作一些綜合成果的呈現,其中第三章宣傳戰歷史演進的部分內容(第二、第五及第六節)及第六章公關化戰爭的媒體運用策略分析的部分內容(第二、第四節),曾發表於《復興崗學報》第98期、97期。第四章公關化戰爭發展歷程及第五章公關化戰爭的媒體管理策略分析的精簡內容則曾發表於《復興崗學報》第92期、94期。另,第七章兩次波斯灣戰爭的訊息規劃策略分析的主要內容曾發表於「第四屆軍事新聞學術研討會」(2010年9月8日,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與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共同舉辦);第八章2003年巴格達市「推倒海珊銅像」的假事件分析曾發表於「2009傳播科技與軍事傳播研討會」(2009年5月21日,國防大學與世新大學共同舉辦),並刊載於《2009傳播科技與軍事傳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年7月,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出版)。
本書共分為四篇、九章節。第壹篇(第一至二章),是本書的研究旨趣、研究問題、研究方法、本書章節架構及本書的理論基礎的陳述。第貳篇(第三及四章)為歷史回溯篇,探討宣傳戰與公關化戰爭的歷史演進。宣傳戰從西方歷史上的主要戰爭中,依序回溯帝國主義時期、革命戰爭與殖民戰爭時期、總體戰爭時期、冷戰時期四個階段的發展情形。公關化戰爭從孕育到成熟,係以越戰為起始點,探論冷戰時期及後冷戰時期兩個階段的發展情形。第參篇(第五至八章)為公關化戰爭篇,是以上一篇歷史分析的研究發現為基礎,進一步檢視美英兩國(以美國為主)在兩次波斯灣戰爭中遂行公關化戰爭的媒體管理、媒體運用、訊息規劃及媒體假事件等重要策略與作為。第肆篇(第九章)為結語篇,係對本書各章的探討與論述做出總結陳述,並提出一些對宣傳與戰爭的研究心得與看法,以及本書的研究限制與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本書寫作過程中,多承作者任教系所劉建鷗主任、徐蕙萍主任、樓榕嬌主任、張梅雨主任、謝奇任主任、陳竹梅老師惠賜寶貴意見,時任世新大學胡光夏教授兼主任熱心指教與協助,以及前國防部軍事發言人暨銘傳大學新聞系副教授吳奇為將軍、軍聞社社長田文輝上校、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吳冠輝副教授、玄奘大學新聞系主任延英陸、文化大學廣告系陶聖屏副教授、前東森電視總經理暨副董事長朱宗軻先生、臺灣中小企業聯合輔導基金會董事長馬傑明先生、前台灣新聞報兼台灣新生報社長趙立年先生、前中央社社長汪萬里先生、前中廣公司花蓮台台長吳晶晶女士等多位師長、同仁、友好的勉勵與督促;又有勞劉建鷗教授、謝奇任主任及銘傳大學劉久清主任百忙中抽空閱讀,並給予寶貴建言與指正,均銘感於心。
本書撰寫時間,特別感謝內人廖麗雪提供無後顧之憂的關心與照顧,小女珮璇、沛樺及芊畬幫忙借還書與校對等工作;本書得以出版,承蒙警察大學陳添壽教授推介,以及元華文創主編李欣芳小姐多所協助,併此誌謝,尚祈各方先進對任何疏漏不吝賜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