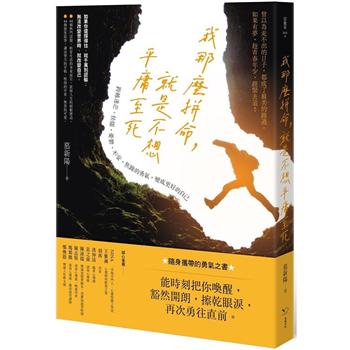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動機與目的
一、從人物到微物與幽情
幽微靈秀地,無可奈何天。(5回)
《紅樓夢》是一個世界,每個人物都確實存在且具有意義。作者碩士論文《另類索隱:《紅樓夢》小人物探微》,將人物按書中出現的文字篇幅多寡區分,大小是對舉言之,無褒貶意思,探索回目中匆匆一過的人物,逐一說人物的文辭諧隱、文學功能等意義,凸顯各人物皆是《紅樓夢》作者匠心塑造。
本書從人物到微物,延續碩士論文中對「物」的闡釋,著重於微小細微之物及其闡發隱微的幽情,畢竟「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微物,寶玉與蔣玉菡交換汗巾前曾言「微物不堪,略表今日之誼。(28回)」顯示了一種以微物寄情的態度。「幽微」有隱微、微弱引申至鬼神的意思, 「靈秀」則有清新脫俗的氣質之意,「幽微靈秀地」或可指隱微脫俗之地之意。在《紅樓夢》太虛幻境這一隱微脫俗之地,卻蘊含著「無可奈何天」的慨歎,因此《紅樓夢》或有隱情未表,也是本書欲探討「真事隱」、「假語存」的語言奧秘之處。有學者說:「在傳統小說中,《紅樓夢》大概是典故用得最多而且最妙的一部。」氏著從第二回雨村遇智通寺「龍鍾老僧煮粥」為起點,梳理六朝筆記、唐傳奇中〈枕中記〉、〈南柯太守傳〉、〈櫻桃青衣〉等以人生如夢為同一主題,將「煮粥」與「蒸黍」作為隱射,視為洩漏天機的安排,讓讀者循此線索,窺探整個段落的奧秘。倘或第2回的龍鍾老僧,並未煮粥,其用典或脂批所謂「是翻過來的」將難以成立,是《紅樓夢》藉物、用典、訴幽情一例。
第二回嬌杏「夜嫁」雨村。婚禮原作昏禮:「父親醮子而迎之前,故曲禮云『齋戒以告鬼神』,是昏禮有齊也。」昏禮,下達,納採用雁「昏禮目錄云,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其陽往陰來之義日,入後二刻半爲昏」,婚禮採黃昏之時為期,取陰陽來往之時,往後大抵底定「昏禮」模式。《醒世恆言》卷三〈賣油郎獨占花魁〉,美娘遭輕薄後欲改從良,四娘道「就是今夜嫁人,叫不得個黃花女兒。」文中見嫁女是為「夜嫁」,另在頗有鬼魅幽冥之說的《拍案驚奇》卷五〈感神媒張德容遇虎〉回目中,李氏同樣「夜嫁」盧生,李母巧遇神媒,直斷盧生非如意郎君,而盧生當日見李氏面目醜陋嚇得逃走,鄭生見李氏則貌美如花,後李氏改嫁鄭生,此回目說明「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一語。而較知名的「夜嫁」故事還有「鍾馗夜嫁妹」等。第二回嬌杏「夜嫁」雨村「乘夜只用一頂小轎,便把嬌杏送進去了。(1回,頁39)」對應批語「知己相逢,得遂半生,一大快事(1回,頁39)」,頗似《拍案驚奇》中以「夜嫁」探索語錄,將批語「知己難逢」、「僥倖(嬌杏)」等語引得全書大綱之一的用典方法,正因「渉于神鬼幽冥」的用典更顯《紅樓夢》用典之精奧。同時,黃一農引周汝昌說法指出「元妃歸省自戌時初刻起身,丑正三刻即刻返回宮中,前後不足四個時辰,此與長期在王府就養一事頗不同」若照史實不相符,那麼戌時起身,丑時三刻回鑾的元妃省親,其時刻頗有可能是作者刻意寫之,夜半回來天未明離去,這見不得光的皇族省親大寫「離合悲歡」的情節,其幽情亦與本例相似。
透過敘述視角不同,既有「夜嫁」便有「夜娶」,寶玉遭陷娶寶釵。寶玉原來因為元妃過身有九個月的功服,鳳姐為沖喜索性連婚也不合,說道「即挑了好日子,按著偺家分兒過了禮。趕著挑個娶親日子,一概鼓樂不用,倒按宮裡的樣子,用十二對提燈,一乘八人轎子抬了來…(96回,頁2259)」,儼如嬌杏夜嫁雨村,又如秦氏出殯黑壓壓一片,紅事悄然如白事,九十七回夜,當寶玉發現所娶的不是林妹妹時,那「本來原有昏憒的病,加以今夜神出鬼沒,更叫他不得主意。(97回,頁2288)」其「神出鬼沒」此註解指變化神奇,難以捉摸,這「夜娶」直指了寶玉不能自主的婚姻,無可奈何天的未來。值得一提,元妃省親點戲,脂批所言四大過節、大關鍵之一《一捧雪.豪宴》「伏賈家之敗」, 同樣在《一捧雪.誅奸》中,湯勤「夜娶」雪娘,雪娘刺殺湯勤後自刎, 因此獃寶玉夜娶寶釵,是否意味著賈府之敗,需要誅奸懲惡才能扭轉劣勢,伏「賈家之勢」也未可知。
幽情,其「幽」情與「陰」互為呼應,按《說文》「(見原書) ,隱也。从山中 , 亦聲。」,《異體》釋義從「隱微」、「幽遠」引申至「鬼神。《北史.卷二五.列傳.尉元》:『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 唐.韓愈〈岳陽樓別竇司直〉詩『炎風日搜攪,幽怪多冗長。』」及「佛教用以指稱地獄及餓鬼道。或稱為『冥土』。《初刻拍案驚奇》卷三○:『那陰報事也儘多,卻是在幽冥地府之中,雖是分毫不爽,無人看見。』」,王熙鳳弄權鐵檻寺,曾這樣對老尼說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從來不信什麼是陰司地獄報應的。(15回,頁386)」「陰司」,《重編》釋:「人死後靈魂所進入的地方」。鳳姐向來不信「陰司」報應,然此時提出,表示有人相信「陰司地獄報應」,作者或讀者的相信或不相信,在此拋下苗頭,待後來鳳姐過身回目反省過去不信果報對照,頗有陰騭勸說之意。
鳳姐說不信陰司此話之前,鳳姐實已與陰間有所聯繫,即13回開頭,秦氏魂託鳳姐。那日賈璉送黛玉回揚州,與平兒說笑後「胡亂睡了。這日夜間,正和平兒燈下擁爐倦繡,早命濃薰繡被,二人睡下,屈指算行程該到何處,不知不覺已交三鼓。平兒已睡熟了。鳳姐方覺星眼微朦,恍惚只見秦氏從外走來……(13回,頁330)」。鳳姐「星眼微朦」,「恍惚」之際,是在半夢半醒間,從秦氏開口「嬸子好睡!」可知鳳姐已經入眠,甚至已經入夢。她二人是因賈璉外出,鳳姐平兒不同往常正經睡,而是「胡亂睡了」,此已為異常的「非常」狀態。「擁爐倦繡」、「濃薰繡被」,當時房內有溫暖的火爐,二人倦繡,後在濃香薰被中入眠,從火爐感受到溫暖的閣房,繡線疲倦的生理狀態,《紅樓夢》作者敘述的入夢方式日常且生活,隨意而自然,和魏晉南北朝的志怪筆記中,仙道,冥見等入夢前意識矇矓的情節相似,插曲般的巧手筆,營造出處於入夢的絕佳狀態,讓王熙鳳體見到已經死去成為幽影的秦氏的魂託。擁爐倦繡中的火爐與繡被,濃濃熏香,此些空間中的微物營造的氛圍,再而引出幽遠的情思,以入陰間的死者可卿的幽情,三重互為表裡,是為微物、幽情與陰性之應合。
晚明玩物品鑑大量出現,香是為其一,知名者莫崇禎年間周嘉冑(1582-1658?)《香乘》。《紅樓夢》裡香味無處不在,寶玉案上有一只香爐,為的不只熏香,更為祭祀所用。董說《非煙香法》更是焚香技術中的極致,書中明載焚香「古者焚蕭以達神明」為達天聽的歷史,更特製了一種不必以火焚燒,以水蒸香的製香法。係因香在明清之際,從文人表現生活情調的物品轉變為故國的象徵,焚(熏)香源自暴力和犧牲,蒸以水代火,認為「百草木之有香氣者,皆可以入蒸香之鬲」,採用昇華(sublimation),形上的香,是董說透過召喚物質的靈魂來滿足嗅覺,也是他憂鬱症的自我療程,也是董說科舉落第後一個斷裂的標誌。周策縱認為《紅樓夢》可能受到董說《西遊補》影響,董說屢次燒掉自己的詩文書稿,彷彿被自己給完全抹除,甲申國變更經歷暴力與死亡的直接體驗,使他有難以抹滅的創傷、恐懼,有時「凡數百卷,悉焚之」與寄人籬下、心病重重的黛玉焚稿斷癡情的情境極為相似,冷香丸、玉生香等,與董說《非煙香法》間有所延續。 寶玉案上那只香爐,雖以火焚之,拜祀的是眾其情不情之人、物,亦達形上。董說是為明遺民,《非煙香法》與《紅樓夢》之間的聯繫,莫不使人聯想至索隱派廖咸浩亡國補天之恨感的徑路。
綜合上述幽、隱、微之意,從小人物到微物與幽情,前者是遊走於《紅樓夢》世界的人物,是較為顯著的。後兩者將與陰性屬性連結,則較為隱性,需透過物件或事情探索更深層的意蘊,故以微物與幽情命之。
二、重讀陰性書寫
本書以「重讀(Rereading)」為題,重讀(Rereading)啟迪於余國藩《重讀石頭記:《紅樓夢》裡的情欲與虛構Rereading the stone : desire and the making of fictio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余氏認為青埂峰上這顆頑石係《紅樓夢》全書象徵結構的總綱,「情」為何的是小說中大問題,余氏旁徵博引情欲糾葛和其中隱含的後設問題由此開展。從文化整體對這個問題有多面性的探討,對「欲望論述」觸處可見,並對後設小說的多重指涉,特就紅樓原書「假語存」的虛構論加以闡釋。作者將透過文本細讀(close reading),追索《紅樓夢》中的微物體系、隱微幽情,將《紅樓夢》置於重新構築的「陰性書寫」中,檢視書中的「物」、「情」、「女性」與「陰間」的關聯性,給予閱讀《紅樓夢》的不同方法。
陰性書寫(Écriture féminine)是一源自法國的女性主義文學理論。法國女性主義思想家海倫.西蘇(Hélène Cixous)(1937-)1976年提出陰性書寫,認為由父權論述收編的人類語言不啻為對女性的身體、個人與社會身分的扭曲。女性為重申自身形象,應持續創造出超越二元對立、動搖理性與邏輯、得以將語言連結至自身身體及慾望、並具有語言結構浮動性及語意無止盡性的個人書寫……,西蘇倡導:
迄今為止,寫作一直遠比人們以為和承認的更為廣泛而專制地被某種性慾和文化(因而也是政治的、典型男性的)經濟所控制。我認為這就是對婦女的壓制延續不絕之所在。
因此
她必須寫她自己,因為這是開創一種新的反叛的寫作……1.通過寫她自己,婦女將返回自己的身體…2.這行為同時也以婦女奪取講話機會為標誌。寫作。這就為她自己鍛製出反理念的武器。為了她自身的權利,在一切象徵體系和政治歷程中,依照自己的意志做一個獲取者和開創者。……只有通過寫作,通過出自婦女並且面向婦女的寫作,通過接受一切由男性崇拜統治的言論的挑戰,婦女才能確立自己的地位。
西蘇的看法:
女性作家在與分娩陣痛相似的字語流的生產中變得偉大而神聖。
因此字語的流動性在其中相當重要。陰性書寫構築在由男性世界所統治的言論與政治的對面,西蘇的倡導並非單純為了挑戰男權,乃是身處於其中的不自由,進而蛻變出的渴求找尋女性自我的一種書寫方式,這份出發點源自對自我的掙扎:
對我而言寫作的故事總是從地獄開始,如同一則生命的故事。首先是自我的地獄,這個早期原始的渾沌,這些個黑暗,我們年輕時於其中掙扎,也從這裡建構出自我。
西蘇提出的陰性書寫,致力破壞男性父權邏輯之控制,突破二元對立之說,享受一種開放文本的喜樂(the pleasure of open-ended textuality),這是一種寫作方式,與作者的生理性別並無必然關聯。旨在透過陰性書寫找回女性發聲權,進而找回女性自我權,最終確立女性自己的地位,而這些找回自我的方法,就在於寫作,也就是陰性書寫的目標。對於女性發聲權在男性社會中的檢視,高彥頤表示,明末清初時,有「女史」、「女士」、「女文人」、「女丈夫」、「女而不婦」,等對女性的分類和命名,這些新標籤表示了社會中性別混亂外,再建秩序的一種需求。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微物與幽情──重讀《紅樓夢》的陰性書寫的圖書 |
 |
微物與幽情:重讀《紅樓夢》的陰性書寫【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郭惠珍 出版社: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5-05-12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微物與幽情──重讀《紅樓夢》的陰性書寫
本書以《紅樓夢》的陰性書寫為主題,通過「重讀」《紅樓夢》中的微物,樹立不同於西方的陰性書寫。這個陰性書寫與西方「陰性書寫(Écriture féminine)」不同處,所指著重在鬼怪傳統,在於漢文化傳統中的「陰」,有其陰間、幽冥等漢字引申義可循,若將文本置於傳統文學史,則可於志怪文學、文人筆記傳統脈絡之中。
商品特色
中國傳統的陰性書寫,與法國的陰性書寫(Écriture féminine),如何對照,敬請期待!
作者簡介:
郭惠珍
學歷
中央大學中國語文博士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
現職
育達科大通識教育中心從事華語文教學
學術成果
曾獲臺北文學獎和若干散文獎項
章節試閱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動機與目的
一、從人物到微物與幽情
幽微靈秀地,無可奈何天。(5回)
《紅樓夢》是一個世界,每個人物都確實存在且具有意義。作者碩士論文《另類索隱:《紅樓夢》小人物探微》,將人物按書中出現的文字篇幅多寡區分,大小是對舉言之,無褒貶意思,探索回目中匆匆一過的人物,逐一說人物的文辭諧隱、文學功能等意義,凸顯各人物皆是《紅樓夢》作者匠心塑造。
本書從人物到微物,延續碩士論文中對「物」的闡釋,著重於微小細微之物及其闡發隱微的幽情,畢竟「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微物,寶玉與蔣玉菡交...
第一節 動機與目的
一、從人物到微物與幽情
幽微靈秀地,無可奈何天。(5回)
《紅樓夢》是一個世界,每個人物都確實存在且具有意義。作者碩士論文《另類索隱:《紅樓夢》小人物探微》,將人物按書中出現的文字篇幅多寡區分,大小是對舉言之,無褒貶意思,探索回目中匆匆一過的人物,逐一說人物的文辭諧隱、文學功能等意義,凸顯各人物皆是《紅樓夢》作者匠心塑造。
本書從人物到微物,延續碩士論文中對「物」的闡釋,著重於微小細微之物及其闡發隱微的幽情,畢竟「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微物,寶玉與蔣玉菡交...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這是在中央大學五年半期間完成的學位論文,這五年半發生了很多事情。親情、愛情一度分崩離析,我的身心狀態到達了臨界,我自怨自艾、自貶自毀,搖搖晃晃地尋找出口。
最要感謝指導教授康來新教授,在我殘破、不能自已的時候,帶著我尋找生命的價值。我們曾在餐館、咖啡廳度過整個午后,曾一起觀展,曾在夜晚漫步臺北街頭,曾參加平安夜的教會團聚,曾整理並搬離在中大的教師研究室,曾一同慶祝「重生日」,她也曾陪伴醉倒在街邊的我……。老師生病前,正著手一篇書稿,我為助理,我們約好某個時間通電話進行第N次討論,然後至今我再沒聽...
最要感謝指導教授康來新教授,在我殘破、不能自已的時候,帶著我尋找生命的價值。我們曾在餐館、咖啡廳度過整個午后,曾一起觀展,曾在夜晚漫步臺北街頭,曾參加平安夜的教會團聚,曾整理並搬離在中大的教師研究室,曾一同慶祝「重生日」,她也曾陪伴醉倒在街邊的我……。老師生病前,正著手一篇書稿,我為助理,我們約好某個時間通電話進行第N次討論,然後至今我再沒聽...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作者序
摘 要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動機與目的
一、從人物到微物與幽情
二、重讀陰性書寫
三、目的
第二節 範圍
第二章 〈美杜莎〉與《紅樓夢》── 陰性書寫釋義
第一節 法國陰性書寫(Écriture féminine)
一、西蘇的發現
二、東方的差異
第二節 重讀陰性書寫
一、如何重讀
二、微物幽情
第三節 陰性書寫之於曹雪芹《紅樓夢》
小結
第三章 微物寄情── 身體、凝視與燒焚
第一節 物之感觸
一、觸物傷情
(一)黛玉獲土物
(二)寶玉收指甲與紅綾襖
二、信物交換
(一)絹帕
(二)汗巾子
(三)...
摘 要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動機與目的
一、從人物到微物與幽情
二、重讀陰性書寫
三、目的
第二節 範圍
第二章 〈美杜莎〉與《紅樓夢》── 陰性書寫釋義
第一節 法國陰性書寫(Écriture féminine)
一、西蘇的發現
二、東方的差異
第二節 重讀陰性書寫
一、如何重讀
二、微物幽情
第三節 陰性書寫之於曹雪芹《紅樓夢》
小結
第三章 微物寄情── 身體、凝視與燒焚
第一節 物之感觸
一、觸物傷情
(一)黛玉獲土物
(二)寶玉收指甲與紅綾襖
二、信物交換
(一)絹帕
(二)汗巾子
(三)...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