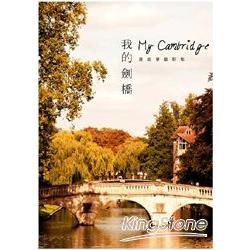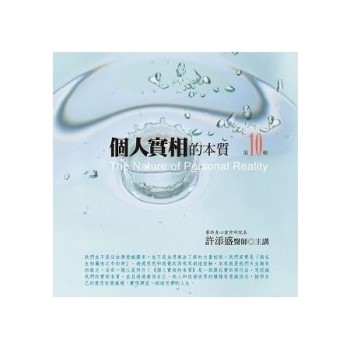一個好學深思的青年企業家,來到世界首屈一指的學術重鎮--劍橋,他的眼光越過(火宣)赫名聲,越過了歷史歲月,他不只看到了劍橋的美,更看到了信仰和虔敬編織而成的劍橋,他看到了深髓的智慧與生命。
作者簡介
羅旭華
羅旭華舉起相機,用另一種眼光記錄了劍橋。
現在,讓我們跟著他的眼光,一起漫步。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管理博士、東海大學管理碩士。
東海大學財務金融系EMBA兼任助理教授;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學院研究所兼任副教授級專家。
現任華頓投信總經理。
曾任金鼎證券集團策略長、新竹國際商業銀行副總經理、花旗銀行副總裁、荷蘭銀行協理、美國銀行資深經理。
曾獲全國攝影獎與全國學生新詩、散文、小說等文學獎獎項、以及東海大學報導文學首獎。
著有:《一個宇宙的距離--全球化趨勢中服務業的國家競爭力》(葡萄樹2009)、《霧裡梧桐》(葡萄樹2008)、《原鄉活泉攝影集》(海峽文化2007)、《理財宏觀》(商周2004)。
中英文期刊論文散見:《管理評論》、《台灣金融財務季刊》、《亞太經濟管理》、《經濟前瞻》、《證券暨期貨發展季刊》、《銀行家》、《國際投資月刊》、《The Journal of Global Business Management》、《Journal of Accountingm, Finance and Management Strategy》、以及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等國內外學術研討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