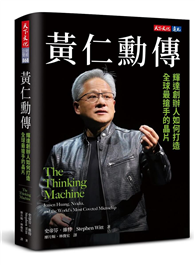導讀 /夏千紅
這是一本拍攝雨林生態的珍貴記錄,也是一本以攝影展現生命之美的散文集。作者是出身於台灣商業攝影圈,後又轉戰於新聞前線的前《中時晚報》攝影記者吳方明,此書是他移居中美洲貝里斯之後,在那裡生活十七年的生態觀察記錄。
吳方明喜歡大自然,以前在台北時,他就常常帶著全家到郊外享受與大自然的對話。有時是在月色中驅車前往台北烏來山區,在靜僻的路燈下與孩子一起觀察鍬形蟲。如果有長假,便一路南下直達墾丁公園,順著沿海公路,白天觀察各種鳥類、昆蟲,夜晚尋找椰子蟹。暑假來了,那就再直奔屏東,辦個入山證,領著孩子進山,去尋訪排灣族人傳說中的神祕鱒魚。再不,就是帶幾枝筆,幾瓶水溶性原料,領著孩子到海邊或溪邊為石頭畫上眼睛鼻子或嘴巴……,反正大雨一來,就將一切沖刷乾淨,他們只要將美麗的記憶裱框掛在腦海中……
1996 年一月,吳方明辭去報社工作,帶著妻子兒女,在親友憂心忡忡的眼光下,毅然踏上移民之路。當時的貝里斯對台灣人而言,不但十分陌生,也是一個在吳方明童年的地理課本上,根本沒有記錄的國家,那裡,除了熱帶雨林,還是熱帶雨林!
貝里斯,一個位於中美洲,上接墨西哥,東瀕加勒比海,西鄰瓜地馬拉的小國,全國僅三十萬人口,土地面積只有台灣的三分之二,是一個尚未遭受工業污染的地方,早年只有馬雅人在其間生活。十六世紀後,開始有加勒比海海盜與西班牙艦隊登岸探險,當時貝里斯幾乎都是原始雨林,林業資源豐富,盛產世界最頂級的桃花心木,後來成為英國人與西班牙人爭相奪取利益之地。及至十八世紀,英國戰勝,逐出西班牙人,把貝里斯據為殖民地,取名:英屬宏都拉斯,直到1981 年,才正式獨立,更名為「貝里斯」,並加入聯合國。
貝里斯的雨林佔全國總面積70%以上,其中孕育珍貴的生物物種,比已開發的巴西,印尼等雨林國家都豐富完整。它擁有超過六十個以上的植物、動物、鳥類、海洋及堡礁等保護區,有些地方甚至還是完全原始、與世隔絕、人煙罕至的熱帶雨林,也因此吸引世界各國生態專家,動、植物學者前來研究。
熱愛大自然的吳方明,一來到貝里斯,就像拜訪一座大自然生態博物館,遠離了台北市的繁華喧囂,不再整天追逐社會新聞四處奔波,沒有BB call 的呼喚。移民貝里斯的第一年,吳方明一家四處探險遊玩,雨林賞鳥觀蟲,馬雅古蹟巡禮,攀登神殿,探尋神祕古老洞穴,加勒比海浮潛,在星空下的貝里斯河坐在獨木舟上夜釣……。尤其,他最常做的一件事,便是手執當地人的長刀,進入雨林探險。在他眼中,每每揭開一片地上的落葉、石頭或移動一截倒下的樹幹,都是一陣驚喜,他總是可以發現藏身其中,不曾見過的物種。
他也常帶著家人到海邊垂釣,僅一兩個鐘頭就可以拉上一百多條小黃魚,在南方的海灘隨處一坐,屁股底下,腳邊踩的,手上摸到的,除了海水及細沙,就是一粒粒人稱海瓜子的一種淡白鑲紫的海蜆,牠們多到幾乎連移動位置都不需要,閉眼隨手撿拾,輕輕鬆鬆就揀滿一大桶,分送鄰居後,還是多得吃不完。
雨季來臨之前,住在首都貝爾墨邦(Belmopan)的他,每天清晨第一件事,就是得清掉幾乎滿滿一大畚斗前一夜落在門前燈下的獨角仙及金龜子,每年約八、九月份,每天都有數以萬計的燕蛾,從早到晚成群的北飛遷徙而去。
然而,不過是短短的幾年,沙灘上的海瓜子已幾乎絕跡,海裡的魚也大量銳減,就連獨角仙與金龜子也少得一年見不到幾隻,至於遷徙的燕蛾,更是不知從何時起,再也不見蹤影,吳方明驚覺因為溫室效應,導致整個地球生態受到影響,連幾乎沒有任何工業污染的小小的國家――貝里斯的昆蟲、鳥類等物種也正銳減中。
吳方明便與我一起邀請長期在貝里斯做熱帶水底生物研究的美國籍河川生態學者Ray Edward Boles 與荷蘭籍的環境生態學者 Jan Cornelis Meerman ,四人一起創立「貝里斯熱帶生態昆蟲基金會」,以傳遞拯救生態環境為宗旨,開始宣導推廣生態保護。同時,吳方明也將他觀察過的昆蟲花鳥等生態拍攝下來,在《宇宙光》雜誌「世界真奇妙」專欄中連載。
2009 年五月吳方明的首篇生態散文〈我家後院――記一個小小的伊甸園〉在《宇宙光》雜誌以專欄問世,除了攝影,他也撰稿,此專欄一寫就寫了二十餘篇,為期兩年多,不但叫好叫座,也博得廣泛讀者熱烈迴響。本書就是收錄吳方明在《宇宙光》雜誌上登過的二十餘篇「世界真奇妙」專欄,集結而來,篇篇精彩,生動活潑,讀來十分親切可喜。透過他的攝影和細膩的描述,鳥類、蜥蜴、昆蟲……,一一躍然紙上,讓許多原本對戶外生物退避三舍或一無所知的讀者印象深刻,興味盎然,值得一提的是,這本書中大部分的主角,都是在吳方明家後院、我家後院,或附近發現拍攝的,他一共拍了幾萬張,最後才精挑細選,將最精華的照片呈現給讀者。
吳方明個頭很大,身高一百八十五公分的他,寫起散文十分細膩,尤其是描寫他與昆蟲、花鳥之間的追逐、跟拍、觀察及互動過程,都很觸動人心。更難能可貴的是,他棄而不捨的觀察、求證,使得他的文章更加彌足珍貴,因為有許多動植物的習性或現象,都是不為人知的,他的「法布爾式」的求知精神,在在都增加了文章的知性與可讀性。像他寫〈雨後的怪客――墨西哥挖洞蟾〉,是以屁股左右扭動,倒退著將身子埋進土裡,再用牠平整的嘴將土夯實,就著實讓人大開眼界,〈百萬娘子軍團〉的行軍蟻與殺人蜂大戰,行軍蟻殘酷盡情略奪幼蜂與卵為戰利品,也令人驚心動魄,而〈天才毛毛蟲鹿子蛾〉用身上的毛築一個安全的家;〈先醜後美的金花蟲〉,從小蟲蟲欣賞大智慧;「跳蜘蛛」隨風擺姿,雙肢高舉過頭,猶似一個睥睨群眾的演說家……在在都令人拍案稱奇。
一般人平常根本不太會注意的昆蟲花鳥,在吳方明的尋覓、觀察、拍攝、撰寫之下,也自成為一個有趣可愛的生態王國,這些都得耗費他難以計數的時間、力氣、耐心、汗水、犧牲睡眠……。有時,得連續守好幾天,才得以捕捉到僅僅一兩張珍貴的畫面,因為那些鏡頭下的主角有些是夜行性的,像偽蠍;有些是幾年,甚至是一輩子都很難得碰上一次的,像挖洞蟾;還有的是危險的,像蠍子;也有一年才見上一面的,像貓鳥、麗色彩鵐……,牠們可都不是肯乖乖合作聽話的模特兒,只稍稍一個不留神,就逃之夭夭了!
從拍攝熱帶昆蟲花鳥及小生物,吳方明覺得樂趣無窮,透過鏡頭和高倍放大鏡、顯微鏡頭等器材,他體認到,原來生物的構造竟是如此精密,生命的嬗遞竟是如此偉大,無論是一足一鬚、一翼一肢、紋彩器官等都有妙用,都是為天敵環繞的生存環境中專門設計的基因程式。
而牠們,正是我們在這個美麗的地球村裡的一群小小小小的鄰居,牠們也與我們共存在這片大地上,或許,我們平日不太關注,可是牠們造形奇特可愛,有的色彩鮮豔,種類繁多,正是地球生態系統中最不可或缺的一環。
現代人忙於都會生活,何妨在工作之餘放慢腳步,走向大自然,佇足田野,聽一聽天籟,聞一聞草香,讓我們一起關心地球,愛護大自然,並珍惜天然資源!
這是一本生態之美的記錄,也是一本提醒人類應該謙卑自省、尊重生命、愛護地球、珍惜大自然資源的最佳教材。
由衷與你一起分享!
漫步伊甸園中 /吳方明
淡淡的三月天,早晨散步在門前的小路上,微亮的天空中只剩下最後一顆還沒西下的星星,它微弱的星光指引著那一群向東方飛去的白鷺。晨霧像是澆了淡墨色的筆,刷在濕漉漉的路面上,我就是踩在暈開的淡墨色中。大地出奇的寧靜,那些鳴了一夜的螽蟖、夜鷹,及遠方的吼猴,想必都累了,可能現在睡得正甜呢!
晨霧漸漸散去,路邊彎著腰的小草鑲滿著一顆顆大小不一,晶瑩剔透,圓滾滾的露珠,不知是小草捨不得美麗的水珠,即將在太陽出來後離開它,還是水珠依戀著軟綿綿的小草。
草地上的一株馬利筋,直挺挺的佇立在路邊,是昨夜才從花苞抽出的一簇小紅花,黃色狀似冠冕的花蕾昂首向著天空,橘紅色裙襬似的花瓣上點綴了小小的露水,雖然花香被空氣凍結在晨霧中,仍然嗅得到微微散發出淡淡的清香,馬利筋高挑的身材加上它這身濃妝豔抹,既是鶴立雞群,又是萬綠叢中的一點紅。
當第一道陽光穿過樹梢,照射在草叢上,霎時點亮了所有的露珠,大珠小珠在陽光中閃閃發光,像散落在草地上的鑽石珍珠。這時逆光中的小草變成透明的綠,綠得就像是翡翠,上面的水珠像是鑲在翠玉上的鑽石,這時微風來了,它輕輕拂過小草,晃動中的露珠更是光芒四射,一一釋放出五顏六色的光輝。
霧完全散了,更多的風景出現了。小草後面的灌木叢上開滿了紫色牽牛花,紅色的野百香果掛在不同的枝頭上,黑椿象用牠長長的口器,像吸管似的插入果肉中,享受果汁。牽牛花後面是高大的木棉樹叢,這個季節的木棉樹,綠葉落盡,它們是先開花,後長葉,所以木棉樹枝上,只剩下鮮黃色的木棉花,花像是用油畫的刮刀,抹在光禿禿的樹幹上的顏料,深藍色的天空背景,加上枯枝、黃花,真是好看極了。
松鼠阿棕跑到小路上,撿拾工人昨天掉落的食物。看到我時,不慌不忙,用手捧著撿來的花生米,鼓著腮幫子,一雙圓滾滾的大眼睛瞅著我,當我拿起相機要拍牠時,阿棕一溜煙的竄入草叢躲起來,不知道是牠不喜歡照相,還是嫌我拍攝技術不好。之後我在後院的脫皮樹上看到牠,正與另外兩隻小松鼠在樹上大嚼果實,這時我才明白,原來阿棕是母的,那兩隻小松鼠一定是牠的小孩。
小木屋前的小紅花又開了,每年的二月底,美麗的麗色彩鵐總是帶著家人路過這裡,牠們是來自美國繞道墨西哥的小客人,一家人長途跋涉,一路為大地播種的小候鳥,每年在這裡停留兩個星期後飛回美國。
椰樹公寓的住戶,紅頭綠鸚鵡夫婦不再回到椰樹公寓,不知道牠們是不是分開了?倒是啄木鳥小紅帽夫婦,每天都準時到我餵鳥的餐桌報到,只是我不曾見過牠們帶小孩來,反正人家有牠們的生育計畫,我又不是生育單位的,能做的就只能默默的祝福。至於椰樹公寓,自從鳥走後,來了一群白蟻居住,在雨後就可看見樹幹上會長出白色的蕈菇。
小角蟬們還是同樣沒有節制的啃食新長的木瓜樹,到最後木瓜樹死了,還來不及羽化的角蟬小孩,只好淪落到與木瓜樹同樣悲慘的命運。
屋後的彩虹農場剪葉蟻,全部不見了,整個剪葉蟻數萬成員,全「走了」。消失的原因不明,剪葉蟻家族是從不搬家的,除非……牠們的消失讓我難過了好久好久。
小精靈無螫蜂,依舊忙碌的在花叢裡幫花授粉。可怕的殺人蜂還是住在小木屋的木板牆壁中,牠們的數量增多了,與我同住在一個屋簷下,我住在屋裡面,牠們住在牆裡頭。這群數量龐大、脾氣不好同居者,一點都沒遷走的跡象,雖然與牠們為鄰,時刻心驚肉跳,偶爾有少數的幾隻,會飛過來打招呼,常常,不是我就是工人們,被牠們熱情的親得鼻青臉腫,醫生看到我腫到只剩看得見一隻眼睛的臉,嚴重的警告我說:「你對蜂毒已經開始過敏,不能再被蜂螫,再螫會有生命的危險!」
所以,此後我的身邊總是帶著過敏針劑,很多人勸我找專人將牠們移走,我考慮到移蜂巢將給蜂帶來嚴重傷亡,因為蜜蜂是植物的大媒人,森林裡有多少花等待著牠們去授粉,要我動手去殺害這群「媒人」,我實在做不到,最後,我選擇……搬離小木屋。
自上次觀察切葉蜂之後,就再也不曾見過切葉蜂了。我猜測那次在辦公室附近出現大量築巢的切葉蜂,應該是遇到牠們正在大遷徙,正好路過我家附近,因為之前之後的幾年,都沒有見過切葉蜂,按理說,切葉蜂的食物、花粉到處都有,也不知是否是氣候變遷的因素,迫使牠們遷徙,真的希望牠們平安無事。
在後院發現了一種有著透明薄趐的螳螂,在昆蟲盒產卵,約有數千個黃色小卵,整齊的平鋪在盒子上。我將拍完照的螳螂放走後,經過十多天,盒內的卵孵化出小小的幼蟲,牠們一點都不像小螳螂,後來經過多方查證,才確定牠是螳蛉,而不是螳螂,牠們和螳螂一樣,都是肉食牲的昆蟲。
行軍蟻的數量少很多,我想是草叢中的昆蟲減少後,這些食蟲的殺手自然就減少了。
後院的芒果樹結滿了小小的芒果,蓮霧開滿了白色的花,三棵檸檬樹也長出了好多小檸檬,風琴鳥霸佔了芭蕉樹上黃澄澄的芭蕉,光禿禿的鳳凰樹,下個月就將換上大紅色的新衣,前院鄰居家的五月花樹,也將開出粉紅色的大花,到時候前面的草皮會披上粉紅色的地毯。農業上的害蟲「果蠅」,仔細的看牠,也是挺漂亮的。後院的棗子樹上,戀愛中的這對斑鳩,像是連理枝頭上的一對比翼鳥。
日出日落,花開花謝,牠們來了,又走了,有時候想想候鳥及昆蟲,牠們好似牆上時鐘的指針,只在每一個時間點上停留片刻,又按著季節的指引,飛到不同的地方,牠們在大地上繞了一圈,明年這時又準時飛回原點。誰說雨林沒有四季,候鳥來時是初春,鳳凰花開時是盛夏,昆蟲最活躍的時候是秋季,至於冬季,那可是最舒服的季節,白天暖暖的,入夜涼涼的,是享受鳥語花香的季節。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一個小小的伊甸園:貝里斯雨林生態筆記(精裝)的圖書 |
 |
一個小小的伊甸園:貝里斯雨林生態筆記(精裝) 作者:吳方明 出版社: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 出版日期:2013-02-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60 |
二手中文書 |
$ 457 |
中文書 |
$ 458 |
自然科學 |
$ 468 |
生物 |
$ 468 |
生態/動物行為 |
$ 468 |
普及科學 |
$ 468 |
科學‧科普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一個小小的伊甸園:貝里斯雨林生態筆記(精裝)
本書是攝影記者吳方明在貝里斯長達十七年的生態觀察記錄。
以極為精緻的攝影和細膩動人的散文,吳方明描寫自己與昆蟲、花鳥之間的追逐、觀察及互動,處處趣味盎然,字字觸動人心……他鍥而不捨的求證、追問,堅持「法布爾式」的求知精神,使本書的知識性與可讀性,完全合一,精彩無比。
本書收錄的兩百餘幅照片,選自作者五萬餘幅生態攝影作品,彌足珍貴,舉世難得一見。所有作品傳達的是造物的創造與偉大,無論一足一鬚、一翼一肢,都訴說造物的奇妙,也提醒人類必須謙卑自省、尊重生命。
一本拍攝雨林生態的珍貴記錄 以最精緻的攝影,展現造物美妙的讚歌 ■名作家張曉風序文推薦
作者簡介:
吳方明
曾任雜誌美術主編、中時晚報攝影記者。1996年移民貝里斯,事業之餘專事生態記錄,為「貝里斯熱帶生態昆蟲基金會」發起人之一。
章節試閱
導讀 /夏千紅
這是一本拍攝雨林生態的珍貴記錄,也是一本以攝影展現生命之美的散文集。作者是出身於台灣商業攝影圈,後又轉戰於新聞前線的前《中時晚報》攝影記者吳方明,此書是他移居中美洲貝里斯之後,在那裡生活十七年的生態觀察記錄。
吳方明喜歡大自然,以前在台北時,他就常常帶著全家到郊外享受與大自然的對話。有時是在月色中驅車前往台北烏來山區,在靜僻的路燈下與孩子一起觀察鍬形蟲。...
這是一本拍攝雨林生態的珍貴記錄,也是一本以攝影展現生命之美的散文集。作者是出身於台灣商業攝影圈,後又轉戰於新聞前線的前《中時晚報》攝影記者吳方明,此書是他移居中美洲貝里斯之後,在那裡生活十七年的生態觀察記錄。
吳方明喜歡大自然,以前在台北時,他就常常帶著全家到郊外享受與大自然的對話。有時是在月色中驅車前往台北烏來山區,在靜僻的路燈下與孩子一起觀察鍬形蟲。...
»看全部
作者序
張序
在那裡,蜥蜴與他互換眼神 /張曉風
「如果你死了,你要埋骨在什麼地方?」
這句話,我好像並沒有機會去問方明。當然,他還年輕,一時還不急著被人家問起這種怪問題。何況我既不是家屬,也不是葬儀社職員,並不具備充分的發問權。
其實,我大概也可以猜到答案:
他應該不會去埋骨江西,雖然那是他父親的故土。啊,說起江西,那是歐陽修和王安石的老家呀,那多山多水卻又窮兮兮的地方,但窮來窮去卻又人才不絕的好地方,那白居易「潯陽江頭夜送客」的地方,那陶淵明種豆採菊的老家,許多台灣客家人...
在那裡,蜥蜴與他互換眼神 /張曉風
「如果你死了,你要埋骨在什麼地方?」
這句話,我好像並沒有機會去問方明。當然,他還年輕,一時還不急著被人家問起這種怪問題。何況我既不是家屬,也不是葬儀社職員,並不具備充分的發問權。
其實,我大概也可以猜到答案:
他應該不會去埋骨江西,雖然那是他父親的故土。啊,說起江西,那是歐陽修和王安石的老家呀,那多山多水卻又窮兮兮的地方,但窮來窮去卻又人才不絕的好地方,那白居易「潯陽江頭夜送客」的地方,那陶淵明種豆採菊的老家,許多台灣客家人...
»看全部
目錄
在那裡,蜥蜴與他互換眼神/張曉風
自序
導讀 /夏千紅
我家後院 記錄從這裡開始……
鳥來了 雨林中的小歌手
飛行中的任務 會播種的候鳥
椰子樹公寓 鳥鄰居的鳥事件
雨林中的小精靈 勤勞的無螫蜂
可愛的獨行俠 慧質巧思的切葉蜂
彩虹農場的農夫 會培育真菌的剪葉蟻
百萬娘子軍團 勇往直前的行軍蟻
森林裡的清道夫 小小白蟻建築師
木瓜樹下的哲思 小角蟬的生與死
用身上的毛築安全的家 天才毛毛蟲鹿子蛾
從小蟲蟲欣賞大智慧 先醜後美的金花蟲
仲夏夜尋蟲記 柳橙樹上的隱行俠
棗樹上的怪蟲 沒頭沒腳的王字蟲
星光下的婚宴...
自序
導讀 /夏千紅
我家後院 記錄從這裡開始……
鳥來了 雨林中的小歌手
飛行中的任務 會播種的候鳥
椰子樹公寓 鳥鄰居的鳥事件
雨林中的小精靈 勤勞的無螫蜂
可愛的獨行俠 慧質巧思的切葉蜂
彩虹農場的農夫 會培育真菌的剪葉蟻
百萬娘子軍團 勇往直前的行軍蟻
森林裡的清道夫 小小白蟻建築師
木瓜樹下的哲思 小角蟬的生與死
用身上的毛築安全的家 天才毛毛蟲鹿子蛾
從小蟲蟲欣賞大智慧 先醜後美的金花蟲
仲夏夜尋蟲記 柳橙樹上的隱行俠
棗樹上的怪蟲 沒頭沒腳的王字蟲
星光下的婚宴...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吳方明
- 出版社: 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 出版日期:2013-02-01 ISBN/ISSN:978957727430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精裝 頁數:176頁
- 類別: 中文書> 科學> 自然科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