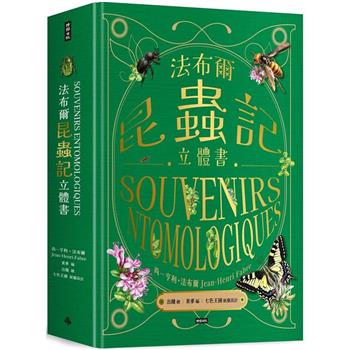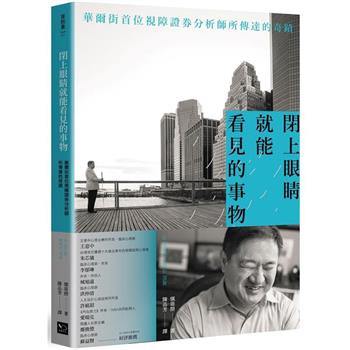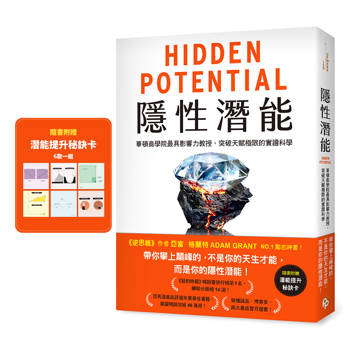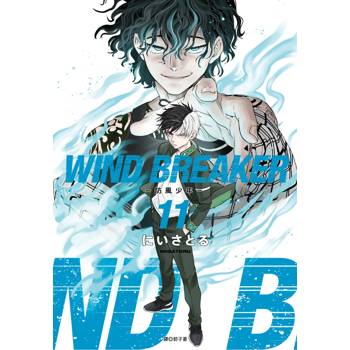從大溪陣頭百年來為關帝誕辰繞境、到北投公民團體十幾年來創造優質環境、再到台馬(來西亞)跨國婚姻中的夫婦努力維護家庭和睦,本書試圖以一個互信模型解釋這三種可分稱為傳統、現代與後現代的社群內部,如何能夠持續合作追求目標。
我們發現最能夠解釋社群合作的變項,是社群自發的非正式互惠規範。因為這一規範不但能夠協調成員的利益,也被內化心中成為生活意義(得到名聲)的泉源。
在理論層次上,雖然Alasdair MacIntyre以其社群觀嚴厲批評互信模型所代表的理性選擇社群觀,本書卻在經驗檢證的基礎上提出綜合兩者所長的新觀點。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從大溪繞境到跨國婚姻:台灣社群的互信與合作探微的圖書 |
 |
從大溪繞境到跨國婚姻:台灣社群的互信與合作探微 作者:方孝謙 出版社: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12-15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11 |
二手中文書 |
$ 315 |
社會與社工 |
$ 315 |
中文書 |
$ 315 |
高等教育 |
$ 315 |
社會休閒 |
$ 315 |
社會 |
$ 326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從大溪繞境到跨國婚姻:台灣社群的互信與合作探微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方孝謙
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
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兼國際傳播英語碩士學程主任
經歷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研究員,柏林自由大學客座教授
專長
社會變遷、政治人類學
研究成果
殖民地認同、大陸鄉鎮企業、社群合作
著有《殖民地台灣的認同摸索》(2001年初版、2008年增訂版,台北:巨流。)及中、英論文近四十篇
方孝謙
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
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兼國際傳播英語碩士學程主任
經歷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研究員,柏林自由大學客座教授
專長
社會變遷、政治人類學
研究成果
殖民地認同、大陸鄉鎮企業、社群合作
著有《殖民地台灣的認同摸索》(2001年初版、2008年增訂版,台北:巨流。)及中、英論文近四十篇
目錄
誌謝 i
自序 iii
緒論 001
一、後現代社會關係?/ 004
二、MacIntyre 的理念型社群/ 012
三、本書結構/ 021
第一章 互信理論模型 025
一、兩個遊戲/ 029
二、Ostrom-Hardin 互信模型/ 033
第二章 大溪繞境 063
一、老13 社與新4 社的比較/ 067
二、普濟堂與社團促進會(及老9 社)/ 073
三、互惠與名聲的分析/ 081
四、經驗分析與Ostrom-Hardin 互信模型/ 103
五、小結/ 116
第三章 北投社區營造 119
一、公民社團的發展/ 125
二、社區發展協會、里辦公室及文化基金會/ 134
三、小結/ 150
第四章 台籍與馬華女性的跨國婚姻 163
一、資料介紹與個案選擇/ 166
二、F 與VI 故事的隱藏價值:敘事身分的分析範疇/ 175
三、實踐價值的情況與互信模型/ 186
四、小結/ 202
結論 209
一、互信模型命題的檢證/ 211
二、理性選擇論還是美德社群觀?/ 238
三、尾聲/ 241
參考書目 245
索引 257
自序 iii
緒論 001
一、後現代社會關係?/ 004
二、MacIntyre 的理念型社群/ 012
三、本書結構/ 021
第一章 互信理論模型 025
一、兩個遊戲/ 029
二、Ostrom-Hardin 互信模型/ 033
第二章 大溪繞境 063
一、老13 社與新4 社的比較/ 067
二、普濟堂與社團促進會(及老9 社)/ 073
三、互惠與名聲的分析/ 081
四、經驗分析與Ostrom-Hardin 互信模型/ 103
五、小結/ 116
第三章 北投社區營造 119
一、公民社團的發展/ 125
二、社區發展協會、里辦公室及文化基金會/ 134
三、小結/ 150
第四章 台籍與馬華女性的跨國婚姻 163
一、資料介紹與個案選擇/ 166
二、F 與VI 故事的隱藏價值:敘事身分的分析範疇/ 175
三、實踐價值的情況與互信模型/ 186
四、小結/ 202
結論 209
一、互信模型命題的檢證/ 211
二、理性選擇論還是美德社群觀?/ 238
三、尾聲/ 241
參考書目 245
索引 257
序
序文
在2001 年出版了第一本小書《殖民地台灣的認同摸索》之後,就開始尋找第二個中程的研究計畫。那時只有懵懂的兩個想法:一方面認為在時序上應該離開日據台灣的範圍,著眼現代的台灣研究;另一方面則對前書中大量使用的後結構與後現代社會理論滋生困惑,懷疑它們真有幫助自己進一步了解台灣在日本占領下的社會真際。
現在展現在讀者面前的第二本小書,應該說是具體回應了原先模糊的想法。首先,透過台北藝術大學劉蕙苓教授從2004年起引介我認識社區總體營造,我跟研究生開始在國科會計畫的支援下,以北投、大溪、及古亭「南村落」為試點,有系統地參與式的觀察三個社區如何在內政部與台北市府的經援下,展開內部更新的工作。當然其間有捨棄「南村落」而取兩岸的「獨立樂團」,再捨獨立樂團而代之以台、馬之間的跨國婚姻群的決定,那是因為在研究途中,我的教學逐漸發展出對全球化下的「離散」社群乃至在台灣的所謂「外籍新娘」的興趣;也因為帶入跨國婚姻的觀察,使我可以把大溪、北投、及台馬婚姻各自要完成的社群目標,即繞境敬神、環境優化及家庭和諧,放在從傳統到現代,再到後現代(或稱全球化時代)的時間軸上來了解,也就是分別視為代表傳統、現代以及後現代的社群。
其次,因為體會到大部分的後學理論者,除了Foucault 之外,幾乎都不曾動手動腳找資料,他們難免受到為理論而理論或視理論為美學創作之譏。所以在本書中,我回到把對三個社群的觀察視為檢驗所謂互信模型的14 個假設的證據之老路,姑稱為是回到「新」實證主義的路徑。以質性證據檢驗假設如何能稱為是「新」實證?我的理由奠基於 Luntley( 1995)這位不太出名的哲學家的一本小書。書中認為後現代理論至少提醒我們,實證主義教我們唾棄日常語言轉而相信數學語言描繪的宇宙真理,只因為後一語言的意義是自足的;它不容許在運算中得出不同的歧義。這樣的實證主義Luntley 認為是無法用來理解人文社會的,試想人際的受想行識或悲歡離合有多少是出自日常語言造成的「誤會」?進而言之,Darwin 的演化論與Smith 的國富論不都是用當時洗練的英語寫的,看看他們所創始的學門在20 世紀所造成的波瀾!既然本書是用許多的小故事來驗證理論,參酌Luntley 之說我只得說奉行的是新實證主義。
最後,我想回答我的研究生看完本書初稿提出的問題:如何定位本書,即這本書寫給誰看?我的就業經驗使我很難成為堅守本位的社會學者,加上意志不堅使我常常遭到廣泛學術圈有趣議題的吸引,本書就是明證。如果只限於圈內人,我會希望至今相信演化作用於人文社會的社會學者成為讀者;但就像本書結尾處所言,我更希望這本小書能夠得到腳踏實地、為社區打拚的人的眷顧。
在2001 年出版了第一本小書《殖民地台灣的認同摸索》之後,就開始尋找第二個中程的研究計畫。那時只有懵懂的兩個想法:一方面認為在時序上應該離開日據台灣的範圍,著眼現代的台灣研究;另一方面則對前書中大量使用的後結構與後現代社會理論滋生困惑,懷疑它們真有幫助自己進一步了解台灣在日本占領下的社會真際。
現在展現在讀者面前的第二本小書,應該說是具體回應了原先模糊的想法。首先,透過台北藝術大學劉蕙苓教授從2004年起引介我認識社區總體營造,我跟研究生開始在國科會計畫的支援下,以北投、大溪、及古亭「南村落」為試點,有系統地參與式的觀察三個社區如何在內政部與台北市府的經援下,展開內部更新的工作。當然其間有捨棄「南村落」而取兩岸的「獨立樂團」,再捨獨立樂團而代之以台、馬之間的跨國婚姻群的決定,那是因為在研究途中,我的教學逐漸發展出對全球化下的「離散」社群乃至在台灣的所謂「外籍新娘」的興趣;也因為帶入跨國婚姻的觀察,使我可以把大溪、北投、及台馬婚姻各自要完成的社群目標,即繞境敬神、環境優化及家庭和諧,放在從傳統到現代,再到後現代(或稱全球化時代)的時間軸上來了解,也就是分別視為代表傳統、現代以及後現代的社群。
其次,因為體會到大部分的後學理論者,除了Foucault 之外,幾乎都不曾動手動腳找資料,他們難免受到為理論而理論或視理論為美學創作之譏。所以在本書中,我回到把對三個社群的觀察視為檢驗所謂互信模型的14 個假設的證據之老路,姑稱為是回到「新」實證主義的路徑。以質性證據檢驗假設如何能稱為是「新」實證?我的理由奠基於 Luntley( 1995)這位不太出名的哲學家的一本小書。書中認為後現代理論至少提醒我們,實證主義教我們唾棄日常語言轉而相信數學語言描繪的宇宙真理,只因為後一語言的意義是自足的;它不容許在運算中得出不同的歧義。這樣的實證主義Luntley 認為是無法用來理解人文社會的,試想人際的受想行識或悲歡離合有多少是出自日常語言造成的「誤會」?進而言之,Darwin 的演化論與Smith 的國富論不都是用當時洗練的英語寫的,看看他們所創始的學門在20 世紀所造成的波瀾!既然本書是用許多的小故事來驗證理論,參酌Luntley 之說我只得說奉行的是新實證主義。
最後,我想回答我的研究生看完本書初稿提出的問題:如何定位本書,即這本書寫給誰看?我的就業經驗使我很難成為堅守本位的社會學者,加上意志不堅使我常常遭到廣泛學術圈有趣議題的吸引,本書就是明證。如果只限於圈內人,我會希望至今相信演化作用於人文社會的社會學者成為讀者;但就像本書結尾處所言,我更希望這本小書能夠得到腳踏實地、為社區打拚的人的眷顧。
方孝謙
2014.09.17
2014.09.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