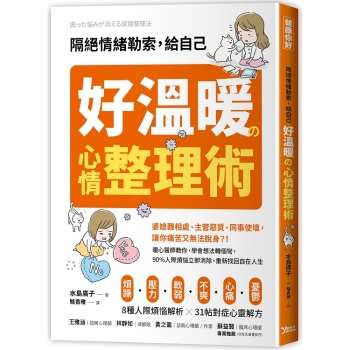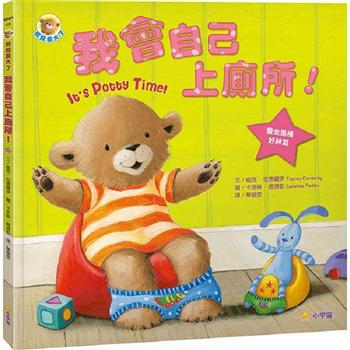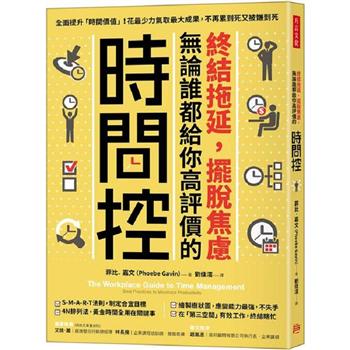學者未必墮落,墮落的學者卻時有所聞。一個學者失足,頂多是個人麻煩,也許事小;許多學者向下沉淪,就是社會問題,兹事體大。
從教育部長、大學校長到個别教授與學生,由官僚體系到學術社群,台灣的學術尊嚴與研究品質,在論文發表前的寫作參與和事後的評鑑過程中,都發生數據不實、論文造假、抄襲與爛竽充數等案例,看起來似乎只是少數人的個人麻煩,其實已涉及社會、學術和行政資源的濫用和浪費,特別是學者與政客之間的互動。
不論是個人麻煩或社會問題,學者一旦不能反思與反省,縱使不至於集體墮落,一個社會注定要在學術醜聞中糟蹋大學的信任與知識的尊嚴,推到極致,喪失的恐怕不會只是學者的人格而已,整個社會為學術弊病所付出的代價難以衡量。
《墮落的學者》是一本介於學術與實用之間的書,在學術方面,批判多於理論探討;在實用方面,規矩多於實際操作。書中所關注的是學者在研究、知識生產與宣稱方面,是否堅持有所為與有所不為,以及留意可能的預期與非預期後果。這些都跟知識技藝和學術研究的養成息息相關,也隱含倫理的拿捏。
作者簡介:
張讚國
學歷: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新聞學博士
經歷:
• 教授,傳播研究所,國立交通大學(2018/9-2021/1)
• 客座教授,傳播與科技學系,國立交通⼤學(2017/8-2018/8)
• 客座教授,傳播學院國際傳播碩⼠學程,國立政治⼤學(2016/8-2017/7)
• 名譽教授,新聞與⼤眾傳播學院,美國明尼蘇達⼤學-雙城校區(2009-)
• 教授,媒體與傳播系,香港城市⼤學(2009/6-2016/6)
• 教授,新聞與⼤眾傳播學院,美國明尼蘇達⼤學-雙城校區(2005/9-2009/5)
• 副教授,新聞與⼤眾傳播學院,美國明尼蘇達⼤學-雙城校區(1993/9-2005/6)
• 助理教授,新聞與⼤眾傳播學院,美國明尼蘇達⼤學-雙城校區(1990/9-1993/6
• 資深研究員,傳播學院,新加坡南洋理⼯⼤學(1996/6-1997/6)
專長領域:
• 國際/全球傳播
• 知識社會學
• 比較傳播研究
• 媒介與外交
章節試閱
前言
我計劃要寫的有關流行文化、新聞、社會評論與學術批判的中文書之一,主要依據我多年來在大學教書與從事學術研究的經驗與反思。其它三本——《塗鴉香港》(第一版,2012;第二版,2016)、《匆促的記者》(2013)與《民主、民意與民粹》(2016)——先後在香港出版,它們多少都是我以記者的視野,對中國、香港與臺灣社會現實所做的片段觀察、紀錄與批判。
反思與謝詞
《墮落的學者》是反思多於實證、評論多於理論的書籍,談不上是系統化的學術研究與紮實的知識宣稱。即使如此,没有許多人的對話、協助與支持,這本書要出版大概不容易。書中對臺灣學術界一些現象與學者的觀察和挑剔未必會引起認同,更可能會帶來文人相輕的譏諷或爭議,特别是以「墮落」評斷他人是非。
在社會科學領域裏,學術辯證與知識宣稱很難定於一尊,而是一個反覆觀察、分析和驗證的作用過程,其間有太多可能的視野轉折與方法取徑。知識社會學的一個根本主張是,我們看到的現實,不可能不受地理與心理位置的影響,尤其是個人幾十年的時空歷程和經驗。
Mannheim(1936)對知識社會學的定義是,一個有關思想的形成如何受到社會情境或存在的制約影響。在他看來,儘管程度有别,在社會結構與歷史過程中,所有知識和觀念都受制於與地點相關的各種條件。由於觀念根基於倡導者的差别時空和社會結構,思想因此無可避免的被觀點或視野所侷限。視野是思考的一種正式鑑定,它顯示我們看現實的方式,我們從中感知到的,以及我們如何在思考中建構現實。
横看成嶺側成峰,這是中國宋朝蘇軾七言絶句裏的第一句。過去幾百年,中國學者卻從來没有發展出類似知識社會學的一套理論和研究方法。蘇東坡的敏鋭觀察、想像力和寫作只停留在文學的詩詞裏,後來的學者顯然未能從歷史與文化經驗中學到知識、教訓與啟發,並在抽象層面延續前人的智慧。
概念,不會無中生有,每一個概念所指涉的現實操作,也都有歷史軌道可尋。即使在概念未出現前,我們很難説,它所指涉的相關行為或動作不曾存在,總有一點蛛絲馬跡,只是還無以名狀。至少,前人為後來者開疆闢土,指引路徑,讓我們可以在既有的學術路上,跨出第一步,不至於舉步維艱。
本書提到的相關理論與研究方法,特别是内容分析與問卷調查,大部分可以上溯到我在美國奥斯汀德州大學新聞系博士課程的知識技藝基礎訓練,一些教授——Wayne Danielson、James Tankard Jr.、Maxwell McCombs、Pamela Shoemaker、Alfred Smith和Stephen Reese——亦師亦友,我才有機會擔任他/她們的研究助理和共同作者,經由「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理解學術並非光説不練,更非虛晃一招,總有實踐的起點與路徑。
良禽擇木而棲,適當的場域是學者操練知識技藝的必要條件,但非充分條件。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二年的經歷顯然只是個起步,打下的基礎薄弱。我的學術生涯真正開始於德州大學新聞系,五年半的博士班訓練讓我深刻感受到,所謂一山比一山高。明尼蘇達大學新聞與大衆傳播學院(SJMC, 1990-2009)則提供了最後的踏脚石,我得以攀爬學術界的梯階,環顧沿路的風景線與人文景觀。
明大是美國大衆傳播研究的重鎭,幾位同事,特别是李金銓(Chin-Chuan Lee),Phillip J. Tichenor,Donald M. Gillmor,Hazel Dicken-Garcia與Ron Faber,在量化和質化研究方面所做的努力與知識宣稱,使我認識到明大所以在美國學術界叱吒一時的學者風範與學術尊嚴,他/她們都是他山之石。
在我加入之前,明大SJMC的全美排名曾經在前五名内。雖然我們從未合作做過任何研究,這些學者促使我在一個不錯的學術場域更上層樓,與他/她們多年為伍,是任何學者的榮幸。不幸的是,在他/她們於2000年起相繼退休後,SJMC的全美學術光環不再,排名頂多是中庸而已。SJMC的興衰説明一個事實,江山代有人才出,再好的學術排名,不進則退,甚至隨風而逝。
在明大20年間(1990-2009),我有機會教授幾門博士班的課程,並短暫出任研究部主任(1994-1995)。為了讓博士生在畢業前能實際演練,我跟同事設計了一套有關學術會議報告、期刊發表和求職面談的步驟要領,也根據學生需要和反應,每年修改與增添内容,整體綱要逐步成形,不過還是少了實務經驗的佐證和案例。
我曾擔任多年期刊副編輯(JMCQ, 2002-2012),也替中英文學術期刊評審過不少投稿論文,具有旁觀者的經驗和心得。另外,自己還發表了一些主要期刊(major journals)的論文,同時出了兩本書,多少有理論與操作結合的親身體會。我在明大SJMC從助理教授一路升到教授,在取得終身職(tenure)後,其實可以安穩的待在明大,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直到垂垂老矣。明大没有退休年齡限制,去留,全憑教授自己決定。
在美國大學,許多學者在升上副教授後,除了教書(還未必教得好),不再從事任何學術研究,對知識與文獻毫無貢獻,成了所謂的「死木頭」(deadwood),或一潭死水。原因自然是,他/她們安於現狀,佔著茅坑,甚至尸位素餐。教授名額固定,若非退休或辭職,年輕學者很難取得一席之地。
一個蘿蔔一個坑,學者佔著位置而無所事事,影響的不僅是他人,更故步自封Benedict Anderson是研究民族主義的美國學術泰斗,2015年在校對自傳初稿後去世,A Life Beyond Boundaries(《超越藩籬的一生》)於2016出版。他在自傳中説,人不能在一個地方停留太久,甚至安頓下來,以免心胸狹窄,屬於地方性,又自我感覺良好。
換句話説,一旦我們對環境中的人事物習以為常,或視為理所當然時,盲點的産生將無可避免,難以做批判性的觀察和思考,學者也一樣。Anderson(2016)的訓誡在我提前從明大退休,並在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任教的7年間,得到對比的驗證。如果我繼續留在明大,這本中文書應該不會見到天日。
城市大學是我在香港任教的第二所大學,1993-1994年,我在美國明大升為副教授後,到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系擔任訪問學者一年。在1997年之前,香港的學術自由與新聞自由大致無礙,政治與學術基本上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一方面教書,一方面在當地的中文報紙發表評論文章,不曾感受到任何有形或無形的政治壓力,學術上也没有以量取勝的傾向。
過了14年,我在2009年再次踏上香江,停留的時間較長,深深發覺到整個學術環境已然變質。城市大學尤其走火入魔,不僅在聘任上以量化數字(期刊論文數目)為主要指標,在學術品質方面的追求,更逐漸以SCI和SSCI的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來區隔學術期刊的份量與影響力,甚至在校内升等申請時,堅持校外評審必須是大學排名在世界百大之内的教授才够份量。種種措施,都以類機械化的操作為出發點,讓人嘆為觀止。
城大時常以名列世界百大自豪,似乎無視在香港八所政府資助的大學間,不論是主觀評價(家長與學生多年的看法)或客觀認定(大學評鑑),最好的排名頂多是第四(偶而第三),也就是中等而已,排在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與香港科技大學之後。大學排名,就像政治一樣,都是在地的才算數,所謂世界百大,不過是一個自欺欺人的假相。
在申請城大教授職位時(2008),校方要我依照表格規定(圖0.1),列舉過去十年每一篇學術期刊論文被引用的次數(citations),並從最高排到最低,再統計總數。城大的用意相當明顯,作為學者,我的所有論文被引用的次數加起來如果達不到一定門檻,就微不足道了,至於門檻如何訂定與是否合理,則是另外一回事。
因為在明大就職與升等(助理教授到教授)時,校方從來没有如此要求過(其實也不太注重),我花了點時間在網路上收集相關數據。原來,學術研究早已被簡單量化,一個學者的份量可以透過引用數字來概括,其中最普遍的數據是Web of Science Citation Indexes和Google Scholar Citations。這個事實説明的是,美國大學的學術遊戲規則延自歷史經驗與學術的獨立自主,根本不適用於其它情境。孰好孰壞,全憑數據的用途與目的。
到了香港後,因為距離近,我跟臺灣的學術界開始有些具體接觸。2010年11月24日,我應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邀請,第一次以國語報告本書中的一些概念。新研所的研究生與幾位教授——林麗雲、洪貞玲與張錦華——跟我分享臺灣學生和學者面對的知識技藝問題,謝謝他/她們提供一個機會,讓我能以局外人的身分,進一步思索局内人的難題。局外人的好處是可以暢所欲言,不過局内人會充耳不聞;局内人的壞處則是不敢相互批評,投鼠忌器(Schweizer, 2020: 23-124)。
圖0.1 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著作引文表格
在香港任教七年間(2009-2016),本書中的主要概念更進一步在博士班課程裏探討,另外也在人文與社會科學院的研究生講座課上報告過。系上博士生幾乎都來自中國的頂尖大學,知識程度與研究態度代表一個變項,可以查驗因地域不同而造成的視野差異。媒體與傳播系的同事,特别是李金銓(我在明大的20年同事)、祝建華、何舟、李喜根與假芝雲,在教學和研究方面,或多或少啓發我對本土學術活動及知識生産的觀察與反思。
一個深刻的感受是,機構(城大)和制度(香港的大學體系)對學者的知識技藝有直接或間接的社會化作用。感謝城大同事與幾位研究生(尤其是易妍、劉娜、宋韻雅),陪我渡過一段不算短的歳月,讓我在教學之餘,能够對中國、香港和臺灣就近觀察,並訴諸文字,在報紙與書籍中記載一些兩岸三地的社會檔案,盡到一點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在他/她們看來,作為傳播學者,我似乎不務正業,尤其是寫《塗鴉香港》,它們卻是我對知識生産不能脱離社會現實的一種堅持和實踐。
從1980年辭去《聯合報》的記者工作到美國唸書起,我在國外停留了約40年,其中在美國的大學任教24年(1986-2009)與香港七年(2009-2016),包括在香港中文大學(1993-1994)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1996-1997)各客座一年。全部以英文授課,發表的學術期刊論文也幾乎都是英文(1994年《台大新聞論壇》的一篇文章算是例外),没有任何中文講課與論文寫作的經驗。這是一種個人歷史的缺口,多少是人生歷練的遺憾。
由於少了一段耳濡目染的親身歷練,一個大致合理,而且容易被當成口實的評斷是,我的教學與研究都跟臺灣本土無關,對當地學術界因此缺少實質參與和具體貢獻。這樣的論斷合乎我離鄕背井快40年的事實,不過也多少排除了一個局内人的地位,不受小圈子與人情世故的干擾,讓我具有局外人冷眼旁觀的一點自在。
我在臺灣當過安三年《聯合報》記者(1976,1978-1980),總編輯是張作錦。剛開始在美國教書後,我到紐約探訪在《世界日報》任職的研究所同學與前同事盧世祥。張作錦正好也調到《世界日報》當總編輯,我們有機會交談了一陣子。走在法拉盛街道上,他問我當記者與學者有什麽感受,我無法確定他問的真正用意,那時他也不太可能知道我曾經用筆名(端木少華)在黨外雜誌《八十年代》發表《聯合報》不可能或不願意刊登的文章。
由於論文發表的理論需求,我開始接觸知識社會學的相關文獻,尤其是社會現實建構的理論框架,加上我當記者(臺灣)和學者(美國)的地方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場域,情境不同,心境也就會有所變異。簡單説,我們所處的地理和心理位置,影響對現實的觀察和評斷。我記不得當時回答張作錦的確切内容,但不外是局内與局外視野的差别。
即使事過境遷,張作錦可能忘了,他的問題卻點出一個學術上的難題:如果與本土脱節,學者的社會角色與作用到底是什麽?經過多年觀察與反思,這本《墮落的學者》與2013年出版的《匆促的記者》放在一起閱讀,也許會有比較完整的答案,感謝他在紐約法拉盛街道上提出的一句話,讓我沉吟至今。
因為終身制的保障(Childress, 2019),明州大學没有退休年齡的限制(實際上很少人教一輩子書,通常接受校方提出的優厚條件卸任),香港城市大學則規定65歳必須退休。2016年我剛好達到法定年限,前一年我開始計劃何去何從:回美國明州,還是回臺灣定居?由於臺灣科技部推出的客座教授計劃,我覺得是用中文教書的唯一機會,決定申請,也獲得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的支持。
科技部竟然很快就通過申請案,讓我在2016年暑假正式到政大擔任客座教授。在申請時,我原本希望能在新聞系教新聞報導或寫作課程,以及一堂影音編輯課。後者是因為從2014年起,我在香港以公民記者身分,在臺灣公共電視的PeoPo公民新聞平台上發佈了不少影音報導,自信能帶給政大一些非傳統的新聞視野與編輯手法。
雖然我在政大唸了二年的新聞研究所,與新聞系的淵源並不深,儘管有幾年的實務經驗,在講究科班出身的新聞系看來,大概算是雕蟲小技。不管是什麽原因,我最後未能以國語開授新聞報導或寫作的任何課程,反而被安排在國際傳播英語碩士學位學程,以英語教授本地生與國外生各半的碩士課。在非英語國家成立一個英語碩士學程,真是一個很奇怪的設計,也許,我的國外教學經驗正好解決了它師資短缺的問題。
前言
我計劃要寫的有關流行文化、新聞、社會評論與學術批判的中文書之一,主要依據我多年來在大學教書與從事學術研究的經驗與反思。其它三本——《塗鴉香港》(第一版,2012;第二版,2016)、《匆促的記者》(2013)與《民主、民意與民粹》(2016)——先後在香港出版,它們多少都是我以記者的視野,對中國、香港與臺灣社會現實所做的片段觀察、紀錄與批判。
反思與謝詞
《墮落的學者》是反思多於實證、評論多於理論的書籍,談不上是系統化的學術研究與紮實的知識宣稱。即使如此,没有許多人的對話、協助與支持,這本書要出版大概不容易...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學者、政客與學術
第二章 知識技藝:學術研究的基礎與虛實
第三章 問題與難題: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
第四章 無形學院:文獻經典與原典
第五章 學術大拜拜:看與被看的市集
第六章 “I”的荒唐:影響因子的霸道與濫用
第七章 知識宣稱:語不驚人死不休
第八章 學術墮落:非作者、真作假、自作孽
第九章 結論:十年磨一劍
參考書目
前言
第一章 學者、政客與學術
第二章 知識技藝:學術研究的基礎與虛實
第三章 問題與難題: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
第四章 無形學院:文獻經典與原典
第五章 學術大拜拜:看與被看的市集
第六章 “I”的荒唐:影響因子的霸道與濫用
第七章 知識宣稱:語不驚人死不休
第八章 學術墮落:非作者、真作假、自作孽
第九章 結論:十年磨一劍
參考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