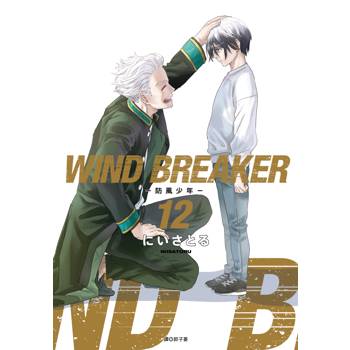當代學術研究之中,臺灣少數族群文化發展的性質、功能及其制度定位,以及地方社會的發展,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新興研究議題。本書藉著理論、政策、族群研究、族群資料庫四個面向,以批判理論的觀點,從理論、社會事實、族群政策三個層次,在過去的多元文化/族群/客家研究上,開始「重構客家」,作為未來族群政治發展的基礎,並找出客家文化再創造的結構力量與機制。
*本書為〝客家研究Hakka Studies〞叢書新書。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客家研究與族群研究的對話的圖書 |
 |
客家研究與族群研究的對話 作者:張翰璧、蔡芬芳 出版社: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3-01-17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05 |
中文書 |
$ 405 |
文化評論 |
$ 405 |
高等教育 |
$ 419 |
社會人文 |
$ 428 |
社會與社工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客家研究與族群研究的對話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陳秀琪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副教授
賴維凱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黃雯君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王保鍵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語言平等及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孫煒
國立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特聘教授兼永續發展暨社會責任辦公室主任
黃菊芳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張陳基
國立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學系教授兼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主編簡介
張翰璧
現職: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特聘教授、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合聘研究員。
簡歷:學術專長為族群與多元文化、性別與客家婦女、族群經濟、東南亞客家研究。
蔡芬芳
現職: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副教授。
簡歷:德國法蘭克福約翰.沃夫岡.哥德大學(Goethe-Universität Frankfurt am Main)文化人類學暨歐洲民族學博士。研究領域主要為族群關係、認同研究、族群通婚、性別與族群之交織性。研究重心則為臺灣客家女性研究、東南亞客家研究。
陳秀琪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副教授
賴維凱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黃雯君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王保鍵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語言平等及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孫煒
國立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特聘教授兼永續發展暨社會責任辦公室主任
黃菊芳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張陳基
國立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學系教授兼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主編簡介
張翰璧
現職: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特聘教授、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合聘研究員。
簡歷:學術專長為族群與多元文化、性別與客家婦女、族群經濟、東南亞客家研究。
蔡芬芳
現職: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副教授。
簡歷:德國法蘭克福約翰.沃夫岡.哥德大學(Goethe-Universität Frankfurt am Main)文化人類學暨歐洲民族學博士。研究領域主要為族群關係、認同研究、族群通婚、性別與族群之交織性。研究重心則為臺灣客家女性研究、東南亞客家研究。
目錄
導論族群理論與政策的反思:以「客家」為核心的思考
張翰璧、蔡芬芳
第一章來回部落主義與多元文化之間的「族群」足跡
張翰璧、蔡芬芳
第二章從「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看客語的語言活力
陳秀琪、賴維凱
第三章從臺灣客語政策檢視客家少數腔調的現況
賴維凱、陳秀琪
第四章族群互動下的語言影響:以桃園客庄分類詞使用為例
黃雯君
第五章選舉制度與族群政治:苗栗縣及新竹縣立法委員選區劃分對閩客族群政治影響
王保鍵
第六章客家社區推動都會環境保育的客家族群性:制度分析與發展架構
孫煒
第七章客家文學中的族群與臺灣主體性敘事:《殺鬼》及《邦查女孩》
黃菊芳
第八章臺灣族群主流化政策指標的建構
張陳基
張翰璧、蔡芬芳
第一章來回部落主義與多元文化之間的「族群」足跡
張翰璧、蔡芬芳
第二章從「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看客語的語言活力
陳秀琪、賴維凱
第三章從臺灣客語政策檢視客家少數腔調的現況
賴維凱、陳秀琪
第四章族群互動下的語言影響:以桃園客庄分類詞使用為例
黃雯君
第五章選舉制度與族群政治:苗栗縣及新竹縣立法委員選區劃分對閩客族群政治影響
王保鍵
第六章客家社區推動都會環境保育的客家族群性:制度分析與發展架構
孫煒
第七章客家文學中的族群與臺灣主體性敘事:《殺鬼》及《邦查女孩》
黃菊芳
第八章臺灣族群主流化政策指標的建構
張陳基
詳細資料
- ISBN:9789577326843
- 叢書系列:客家研究Hakka Studies
- 規格:平裝 / 320頁 / 17 x 23 x 1.6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