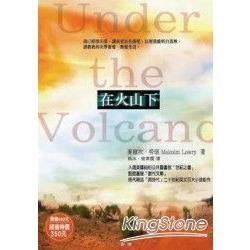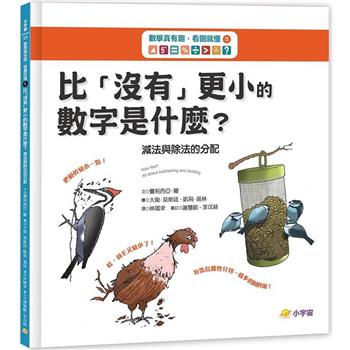觥籌交錯中的瘋狂世界
笑之
由麥爾坎.勞瑞(Malcolm Lowry)所著的《在火山下》(Under the Volcano)於一九四七年出版,在一九九八年被美國紐約公共圖書館選編的《世紀之書》以及藍燈書屋的《當代文庫》編輯小組選為二十世紀一百大英文小說之一。
《在火山下》是一部半自傳體小說,作者以墨西哥的誇恩納華克鎮(Quauhnahuac)為場景,並以西班牙內戰為背景,述說酗酒的英國領事傑佛瑞費明的悲劇故事。這部作品探索著領事的過去與現在,並將他個人的厄運與墨西哥悲劇般的宿命相結合。
故事從傑佛瑞的兒時玩伴──拉呂爾的倒敘開始,他回憶起傑佛瑞生命走到盡頭的最後一天,回憶起自己見到傑佛瑞的最後一面,接著還回溯到他與傑佛瑞的兒時回憶。就像經過剪接的電影一樣,倒敘中包含了另一個倒敘,並從這些延伸的畫面中突然轉換到特寫鏡頭。勞瑞巧妙地將電影的拍攝手法應用在文學作品上,讓讀者在拜讀此作品的同時,就像在看一部電影,在鮮明的畫面中跌入了傑佛瑞、休、拉呂爾與伊溫妮四人之間的情愛糾葛。
有別於其他英雄主義式的小說,本作品全文幾乎都圍繞在傑佛瑞酗酒的主題上,主角是個不折不扣的酒鬼,故事中四分之三的時間,主角都是醉醺醺的。政治失意、婚姻失敗的傑佛瑞藉由一杯杯的麥斯卡爾酒來逃避現實,逃避他不想面對的醜惡世界,然而在他選擇以酒精麻痺自己的同時,他卻也從關愛他的人身邊逃開了。當伊溫妮再度回到他身邊時,他放任自己墮落的決心確實有所動搖,他確實考慮過要放下酒杯,重新處於太陽的照耀下,和伊溫妮重新開始。然而,在半空中遲疑的酒杯並不能延緩他墮落的速度──「不管他是否再喝很多酒,黑夜都必然會等候著他」。而且儘管步履蹣跚,他還是一心要走到那在火山下的法羅立特──「這裡是他絕望的天堂」。
但不管小說最後的結局如何,傑佛瑞都可以說是悲劇性的英雄,或者說是反英雄主義者。領事基本上是個文雅的人,這個儘管不是最正常,但卻最感性的人提供了最具代表性的「崩潰」表現,為其他人帶來了他們幾乎沒有察覺到的影響。領事的心路歷程在某種程度上似乎也反映了其他人的心境,只是並非所有人都會做出和他一樣的選擇。傑佛瑞的酗酒、自甘墮落自然偏離了正常人生活的軌道,但他至少不像休那樣虛偽、沽名釣譽,表面上是個熱血的好青年,實則只是為了用「煽情」的宣傳手法讓自己成名而出海。休還因為猶太唱片發行商沒有發行他的唱片,而從一位親猶太主義者成了反猶太主義份子,甚而在心中暗自幻想挑起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以洩自己的心頭之恨。相對於傑佛瑞的自責,休則是將自己的失意怪罪到其他人身上。他厭惡拉呂爾的濫交,卻喜歡用自己引以為傲的吉他來誘惑別人的妻子。從這個角度看來,休這個外表爽朗的青年其實並沒有比酗酒的傑佛瑞好到哪去,他們同樣都對現實感到不滿,而差異只在於:休選擇以冒險和迎合現實的方式,而傑佛瑞則選擇用酒精和逃避現實的方式來填補自己的空虛和無助罷了。
《在火山下》充滿了複雜和隱喻的象徵主義,成功地描寫了傑佛瑞酗酒的心理狀態。在勞瑞筆下,讀者可以從酒鬼迷茫的眼中去看世界,了解酒鬼的思維、感受和生活體驗,並隨著傑佛瑞的腳步,看見了酗酒者眼中分崩離析的瘋狂世界。而領事的悲劇故事便隨著啤酒、茴香酒、龍舌蘭酒、麥斯卡爾酒等不同風味的酒,與真實世界產生了連結。
象徵主義主張發掘隱匿在自然界背後的理念世界,憑個人的敏感和想像力來創造超自然的藝術。因此,在《在火山下》中,作者除了細膩地描繪出一幕幕栩栩如生的畫面以外,也為自然的景物注入了故事中人物的情感,貼切地反映出傑佛瑞的孤獨與淒愴,甚至預示了主角自取滅亡的悲慘命運──「一個孤獨的影子猶如鐵道上的一把傘,遮蔽住一處尖樁籬柵;末日的徵兆,心力交瘁的徵兆……」。
傑佛瑞酗酒的根源來自孤獨,而在勞瑞的筆下,連小說中的種種景物都可映襯出傑佛瑞孤單的身影──「我相信那是一隻銅尾咬雀。牠沒有紅色的胸部。牠是個孤獨的傢伙,可能棲息在那邊的狼峽谷中,因為有自己的想法,離開了其他傢伙,以便能安靜地考慮清楚,自己並不是一隻紅雀」、「外面那棵孤零零的楓樹……」、「穿越孤獨的鐵路線……」、「今晚,這個孤獨的月臺上只會站著他一個人,還有他的行囊」、「雲層上的某處,一架孤獨的飛機發出一陣短促的聲音」。
作者也以傑佛瑞的墮落來象徵二十世紀的價值崩壞。就像在《李爾王》中,透過國王疲憊不堪的心想像著政權的喪失一樣,在《在火山下》中,墨西哥悲劇性的絕望似乎也隨著西班牙內戰,在領事和休的心中放大並扭曲。傑佛瑞和休對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爭論,反映出西班牙內戰的時代背景,而透過故事中人物的對話及敘述,也可約略看出作者對傳統基督宗教精神和自由意志的看法。
故事中的領事雖然有時也厭惡自己的不清醒狀態,甚至不時發出求救信號──「……我就會幻想你就在飛機上,每個早晨都在那架經過的飛機上,你會來拯救我的」、「他做了些什麼?在某個地方睡覺,這是肯定的。滴答:滴答:救命:救命…」,但領事是真心想得救嗎?「救救我,領事心?模糊地想著……但那隻蠍子在將自己蟄死的時候,也許並不想被得救」,答案似乎已呼之欲出,或許領事還是寧願選擇墮落,只是不喜歡一個人孤孤單單地墮落而已。
《在火山下》的主角是領事的意識,也是作者勞瑞的人格面具。《在火山下》的故事反映了作者勞瑞的真實人生,酒精與文學支配著他的生命。年輕時期的他,就像故事中的休一樣熱血、富有冒險精神,曾航行至遠東,也曾造訪美國及德國。他在法國娶了他的第一任妻子,曾為了挽救他們漸行漸遠的婚姻關係而到紐約進行戒酒的治療,然後在好萊塢開始嘗試劇本的創作。但當這對夫妻遷移到墨西哥,試圖為他們垂死的婚姻做最後一次的掙扎時,他們的關係最後卻仍以失敗告終。而晚年的勞瑞就像故事中的傑佛瑞一樣,是個無可救藥的酒鬼,但不同的是,酗酒為勞瑞帶來了平靜和創造力,雖然最終因飲酒過度和濫用藥物逝世,但比起孤獨的傑佛瑞,勞瑞至少還有第二任妻子相伴。
而讀者也會注意到,即便勞瑞過著到處遊歷和離群索居的生活,《在火山下》這部作品仍顯示出他對時事並非漠不關心,甚至隱約透露出他的政治理念及對戰爭的看法──「他對戰爭沒有什麼感想,只是覺得它不是件好事。這一方或者那一方總會取得勝利。不管出現哪種情況,生活都會艱難起來。可是,如果協約國贏了的話,日子會更難過。無論怎樣,每個人自己的戰爭都將繼續下去」。
《在火山下》整部作品充滿著法西斯主義。墨西哥警察在善與惡的平衡中,就相當於西班牙的法西斯警察。他們是法西斯主義份子,謀殺了傑佛瑞、休與伊溫妮在路上見到的那位印地安人。而天真地抱持著贊成西班牙共和想法的休,則在一次酒酣耳熱之際,傑佛瑞談起納粹制度──「……即使已死,還繼續吞咽下活生生的抗爭著的男男女女!」。
評論家大衛馬克森(David Markson)指出,《在火山下》所採用的神話式聯想法很有「喬伊斯」的味道,在小說中引用了荷馬史詩中的平行對應關係,就像喬伊斯所著的《尤利西斯》一樣,而且還帶有巴克萊(George Berkeley)的哲學思想。
不過若與他崇拜的同時期意識流作家喬伊斯(James Joyce)及象徵主義作家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等人相較下,勞瑞的寫作手法較偏向自傳體、個人而主觀,而另兩名作家則試圖創造去除自傳和主觀成分的「客觀」文學。他們的目標是個人的抽離,而非個人的表達。在他們的美感觀念中,詩人是感性的工具,會依其生活狀況而發揮作用,將過去的秩序與現在的混亂相連,並表示意見,但並不傳達創作人本身的個性。
此外,《在火山下》還融入了大量名家的文學著作,與作者本身優美的文字一同演繹出扣人心弦的動人樂章,無論在思想或文句上顯然都是部不容錯過的經典之作,絕對不會受到時空所限制。被選為二十世紀百大英文小說不是沒有原因的。
(本文作者為專職譯者,喜愛歐美文學並有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