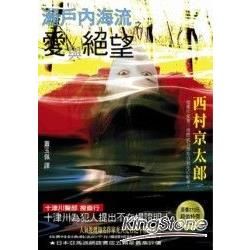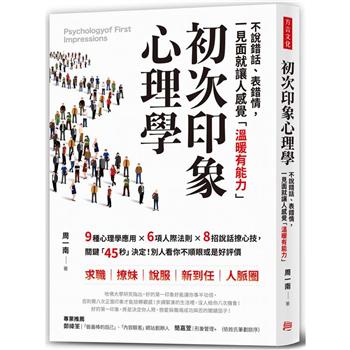十津川為犯人提出不在場證明!
人氣推理知名作家光天化日之下慘遭殺害
推理作家筆下情節成為預知自我死亡紀事?
玩弄時刻表戲法的不在場證明該如何破解?
★日本亞馬遜網路書店五顆星最高評價
交織著愛與絕望的壯麗渦流,激起無限殺意……
旅遊推理小說家北川京介
在鳴門當地的寫作取材行程中駭人地被謀殺
同行的年輕編輯具有最大的嫌疑
在東京深大寺發生的女大學生命案調查過程中
竟然共同串連起令人匪夷所思的線索
同時,新的嫌疑犯產生!
但其卻擁有堅若磐石的不在場證明……
作者簡介
西村京太郎
東京都立電機工業學校畢業,在擔任了十一年的國家公務員後離職開始作家生涯。以《歪斜的早晨》獲「ALL讀物」第二屆推理小說新人獎,在文壇上嶄露頭角。後又以《天使的傷痕》獲江戶川亂步獎,《終點站殺人事件》獲得第三十四回日本作家推理協會獎。作品善於從尋常的生活中來挖掘重大題材,情節高潮迭起,環環相扣,其中又以推理謹慎、老謀深算,視正義為職志的十津川警部為代表性人物。
西村氏創作豐富,至今出版作品已超過三百五十種,堪稱日本推理小說大家。2001年,「西村京太郎紀念館」在日本神奈川縣開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