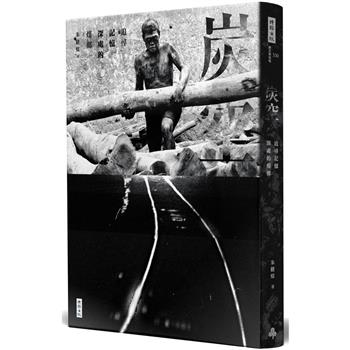序言
學成君的《史記綜論》即將問世,讓我寫一序言。說實話,我既非學界名流,又非《史記》研究專家,如何擔當得起!我也理解到學成君讓我為序,並非是為了給他的大著錦上添花,而是因為我們多年彼此相知的交情。於是,我便決意趁機寫一點讀後心得,作為對他階段性收穫的紀念。
憑實說,就學成君所處的教學條件、科學研究環境而言,能推出一部像樣的著作實屬不易。當讀到他發來的《史記綜論》初稿時,我頗感喜出望外。之所以有這樣一種感覺,主要是因為:
其一,《史記綜論》是學成君用心體悟的結果,包涵著其心路歷程,讀來親切。
透過該書的內容以及用筆語氣,我們不難感受到,學成君對《史記》情有獨鍾,感悟頗深。可以說,他時常把自己從現實世界投入到《史記》所敞開的情感世界中,與這部巨著的作者共哀樂,和這部作品中的人物同悲喜。眾所周知,撰寫學術著作是苦的。如何做到苦中有樂?最有效的策略就是選擇自己喜歡的研究對象,在愛好和興趣的基礎上研讀、著述。學成君與《史記》研究結緣,並非偶然。
我很瞭解學成君的為人處世、人格情操,也每每在人前說他好話。追溯起來,我們的交情是從1992年我做他大學導師開始的,那時他就給了我「很仗義,也很性情」的印象。在以後的交往中,這一點不斷地得到驗證。我們名義上是師生,實際上彼此年齡相差不甚大,我常視其為情同手足的兄弟。在眾人眼裡,學成君很有正義感,敢想敢做,不平則鳴;又極重人際情誼,在「熙來攘往」、「翻雲覆雨」、「人走茶涼」的世俗社會裡,他能夠難得地「保溫」,不改初衷,一往情深。如此,《史記》中的「憤氣」、「熱情」便容易得其心,適其意。再說,多年來,他學業刻苦,不斷上進,大學畢業後就到大學任教,期間他赴浙江師大讀研,深受《史記》研究專家的影響,也助燃了他研究《史記》的熱情。而後,在教學工作中,他堅持給學生開「《史記》研究」這門選修課,教學效果良好,受到歷屆學生好評,終得厚積薄發,成就了《史記綜論》這部著作。
作為一部傾情之作,學成君在探討《史記》寫人藝術時,能不時地聯繫一下當下社會現實,並發表一些人生感悟。如在談到「互見法」問題時,學成君有感而發,寫下了這樣的話:「因為對互見法的深入解讀,我們會發現歷史就是由活生生的人構成的歷史,歷史是血淚史,歷史是勝敗史,歷史是一部分人得意與一部分人失意的歷史,所謂勝者王侯敗者寇是也;歷史的成敗往往是以無數無辜生命做代價堆積而成的歷史。歷史有時又是人整人、人治人的歷史。歷史還常常是少數人透過絕大多數人實現自我利益的歷史。所以,歷史從根本上說應該是自私的。」這些議論感慨萬端,因觸發於研究對象,而不顯空洞,令人不禁嘖嘖稱讚。
其二,《史記綜論》注意面向文本,進行現代闡釋,讀來質實。
在當下學術著作寫作中,有的人喜歡誇誇其談,要麼繁文縟節地堆積一套一套的理論,要麼長篇大論地說一些不著邊際的話,乃至拋開研究對象,把話題扯得老遠。由於不具有文本針對性,這毋寧說是在放空炮。學成君的寫作理路與此不同,他的論述語言來自教學實踐,娓娓道來,明白曉暢。為給學生以直觀而切實的認識,該書除了大量引用前人研究成果,更注重引證《史記》及其他著述文本,尤其是不惜筆墨地引用了許多經過精選的著名片段。如此行文,讀來實實在在,給人血肉豐滿之感。
當然,學成君並不停留在對文本泛泛的羅列層次上,而是在引用的每一段文字後,進行翔實而飽滿的闡釋。而所進行的各種闡釋又往往避免人云亦云,致力於面向現代,迸發出現代意識的火花。如他在探討《報任安書》中的「發憤著書」那段眾口皆碑的文字時,便提出了如下一番新見:「韓非囚於秦國而寫《說難》、《孤憤》,呂不韋的《呂氏春秋》的編撰在遭貶遷徙之後,周文王、孔子和左丘明的創作等等其實都缺乏歷史證據來證明,而說《詩經》三百篇『大氐聖賢發憤之所為作』,更是難圓其說,因為《詩經》大量的愛情詩,尤其是纏綿美好的愛情詩是難以與『聖賢發憤』扯上關係的。在有的人看來,這簡直是胡謅八扯,但是否可以說司馬遷不懂歷史呢?其實司馬遷很清楚有些例子並不可靠,但為了表達內心的激憤之情有意為之,抒發真情實感才是根本。」面對這段耳熟能詳的文字,人們往往不加深究,而學成君卻既指出了司馬遷列舉的不當,又提出了司馬遷明知故犯的理由,符合一代史學家、文學家當年撰述的情景。
再如,在論述心理描寫藝術時,學成君對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的愛情故事的闡釋也能貼近歷史人物的真實,做出了大膽而又貼近文本真實的論斷:「如果我們認真研讀這一看似美好而浪漫的愛情故事,其實並不浪漫,並不美好;或者簡直可以說這就是一個騙局,是司馬相如和王吉設計好了的欺騙良家少婦感情的一個圈套。」之後,學成君又據歷史文本進行了深入細緻的論述,「司馬相如與王吉密謀合作,假戲真演,達到了最佳的宣傳效果,終於製造了轟動效應,引起了卓文君的注意,透過席間的近距離接觸、優秀的才藝表演和周密的工作,終於抱得佳人歸,還連帶著借陰暗手段賺取了大量物質財富。」幽默詼諧,而又合情合理,令人心服口服。
其三,《史記綜論》能發前人所未發,時出新意,讀來閃眼。
除了感悟體味作品,學成君還注重《史記》作者及《史記》體例的研究,這些研究也不停留在照搬或重新整合傳統研究的水平上,而是不斷地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如關於「司馬遷生平」,學成君強調了「李陵事件」的決定性意義,從而指出:「李陵事件將一個平平常常的史官玉成了偉大的歷史學家和偉大的文學家,也使得司馬遷練就了一雙能夠透視歷史、直指人心的火眼金睛,從而將可能的符合歷史學規範的史書鍛造成為一部具有鮮明個性特徵的文史巨著。」
對《報任安書》,他也有自己獨到的看法:「這封書信,我們認為不可能送到任安手上,因為本篇與《史記》比,有著太直接太尖銳的議論,太真摯太複雜的抒情,這樣的書信如果寄出去,無疑會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這很可能只是司馬遷寫給自己寫給後人看的『心書』,一篇司馬遷內在心靈的自我告白。」如此之類的新見,不勝枚舉。
放在一部著作前面的話不宜過長,姑且寫到這裡。
我很喜歡東坡送給他方外友人參寥子的一句話:「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的確,交友要講境界,朋友不求多,但求投緣。在此,我也由衷地將這句話送給學成君,以示對彼此情誼的珍重。願學成君在保重身體的同時,繼續熱衷於《史記》研究,從而深切地感悟更豐富多彩的人生。
李桂奎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史記綜論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35 |
社會人文 |
$ 468 |
史記 |
$ 484 |
中文書 |
$ 484 |
中國歷史 |
$ 495 |
史記 |
$ 495 |
歷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史記綜論
《史記》是中國史學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開創了紀傳體通史的先河,在史學發展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同時又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部文學巨著,可以稱得上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座豐碑。它對於以後中國的文學、史學、文化的發展都造成了不可忽視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成為中華文化發展的源泉。《史記》當中涉及的內容非常豐富,人物傳記的文學價值、史學價值,乃至文獻學價值、文化學價值都很突出,所以《史記》又被稱為百科全書式的巨著。
本書意在透過對《史記》有關理論知識的講解和精彩片段的分析,引導讀者全方位多角度地把握《史記》,進而提高閱讀古書的能力,增強分析思考的能力,培養分析歷史人物、文學人物的興趣。透過對《史記》的學習,可以瞭解、認識和把握中國古老的燦爛的傳統文化,提高我們的文化素養,最終增強大家的民族自豪感和愛國熱情。
由於《史記》是一部偉大的文學巨著,所以,可以透過《史記》有關人物傳記的學習,初步掌握人物傳記的特點和寫法,把握其在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意義。《史記》是史學巨著,是透過活生生的人物來串起生動具體事件的紀傳體著作,同時又是非常優秀的敘事文學作品,對於後世小說、戲劇等敘事文學具有重大影響。
同時,學習《史記》可以對個人的立身處世有很強的指導意義。《史記》中最有價值的是其中幾百個活生生的歷史人物。司馬遷透過對歷史人物一生或詳或略的敘述,做出自己的考察和綜合分析評價。歷史人物的優缺點,歷史人物的長處和短處,歷史人物人生關鍵時刻或正確或錯誤的選擇而導致的不同結果都對現在的我們有著深刻的啟示。
作者序
序言
學成君的《史記綜論》即將問世,讓我寫一序言。說實話,我既非學界名流,又非《史記》研究專家,如何擔當得起!我也理解到學成君讓我為序,並非是為了給他的大著錦上添花,而是因為我們多年彼此相知的交情。於是,我便決意趁機寫一點讀後心得,作為對他階段性收穫的紀念。
憑實說,就學成君所處的教學條件、科學研究環境而言,能推出一部像樣的著作實屬不易。當讀到他發來的《史記綜論》初稿時,我頗感喜出望外。之所以有這樣一種感覺,主要是因為:
其一,《史記綜論》是學成君用心體悟的結果,包涵著其心路歷程,讀來親切。
透...
學成君的《史記綜論》即將問世,讓我寫一序言。說實話,我既非學界名流,又非《史記》研究專家,如何擔當得起!我也理解到學成君讓我為序,並非是為了給他的大著錦上添花,而是因為我們多年彼此相知的交情。於是,我便決意趁機寫一點讀後心得,作為對他階段性收穫的紀念。
憑實說,就學成君所處的教學條件、科學研究環境而言,能推出一部像樣的著作實屬不易。當讀到他發來的《史記綜論》初稿時,我頗感喜出望外。之所以有這樣一種感覺,主要是因為:
其一,《史記綜論》是學成君用心體悟的結果,包涵著其心路歷程,讀來親切。
透...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序言
導言 司馬遷和《史記》
第一章 《史記》的魅力、價值及其研究概況
第一節 《史記》的魅力和價值
第二節 《史記》研究概況
第三節 當代《史記》研究的特點
第二章 《史記》產生的環境和條件
第一節 漢武盛世
第二節 史官世家
第三節 讀萬卷書和行萬里路
第四節 師承大師
第五節 遭李陵之禍
第三章 司馬遷著作簡介及《史記》的創作宗旨
第一節 《史記》及其他著作簡介
第二節 《史記》的創作宗旨
第四章 《史記》的體制
第一節 五體結構
第二節 《史記》標題與主題
第三節 互見法的運...
導言 司馬遷和《史記》
第一章 《史記》的魅力、價值及其研究概況
第一節 《史記》的魅力和價值
第二節 《史記》研究概況
第三節 當代《史記》研究的特點
第二章 《史記》產生的環境和條件
第一節 漢武盛世
第二節 史官世家
第三節 讀萬卷書和行萬里路
第四節 師承大師
第五節 遭李陵之禍
第三章 司馬遷著作簡介及《史記》的創作宗旨
第一節 《史記》及其他著作簡介
第二節 《史記》的創作宗旨
第四章 《史記》的體制
第一節 五體結構
第二節 《史記》標題與主題
第三節 互見法的運...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