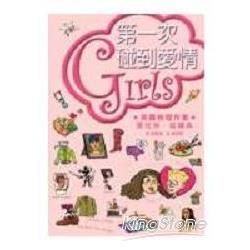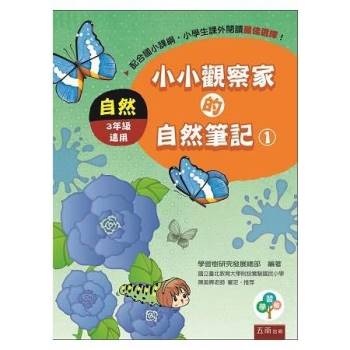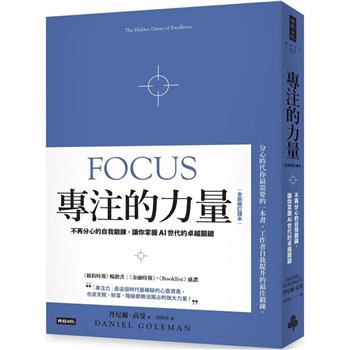梅格妲說:「感覺很棒吧!」她剛剛又跟我們講她的羅曼史。
娜黛一臉同情的看著我說:「艾莉,等妳有了男朋友就會了解的。」
真是夠了。
我一時脫口而出:「別擔心,我已經有男朋友了。」
娜黛瞪著我。
梅格妲瞪著我。
我像是靈魂出竅,在半空中瞪著自己。
我說了什麼?
我在幹什麼啊?
我怎麼會說出這種話?
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第一章 一個女孩
開學第一天,沒趕上校車,只好走路上學。滿糟的開始。九年級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呢?
九號、九號、九號……
這是披頭四經典<白碟>(White Album)專輯裡的歌,最後瘋狂混音的那部分。雖然約翰藍儂是很久以前的歌手,在我出生前就掛了,但我就是喜歡他。我喜歡他的小小塗鴉,還有他戴老古董眼鏡的樣子。他很有趣,而且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也喜歡隨手塗鴉,我也戴眼鏡,朋友都覺得我很有趣。我自己也這樣覺得。但是我沒有機會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現在是八點半。如果我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我一定會跳回床上,縮成一團好好睡一覺。約翰藍儂和小野洋子整天躺在床上的時候,不也是成天睡懶覺?他們甚至在床上接受訪問。有夠酷。
嗯,如果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我要睡到中午再起床,然後喝杯熱巧克力,吃個甜甜圈當早餐,再聽聽音樂,隨便畫一些東西。也許看看錄影帶,然後再吃吃東西,出門吃個批薩好了。呃……我想,應該堅持吃沙拉才對。整天躺在床上一定很容易變胖。我才不想變成一隻擱淺的肥鯨魚。
我要吃綠色的蔬菜沙拉,還有綠葡萄。有什麼飲料是綠色的呢?上回梅格妲喝薄荷雞尾酒時我嚐了一口,並沒她說的那麼好喝。我倒覺得有點像在喝牙膏。算了,不管飲料了。
我還要打電話給梅格妲,還有娜黛,然後一直聊天一直聊天,然後……
嗯,聊完天差不多就到傍晚了,該去洗頭洗澡,換上……該穿什麼睡覺呢?反正絕對不會是現在穿的那套泰迪熊睡衣。太男孩子氣了。可是我也不愛那種飄逸的絲質睡衣。想到了,要穿繡著五彩玫瑰的白色長袍,然後每根手指都戴上大大亮亮的戒指,最後像芙烈達卡蘿(Frida Kahola)一樣躺在床上。芙烈達卡蘿也是我的偶像。她是墨西哥藝術家,獨一無二的眉毛、特別的耳環、鮮花髮飾是她的註冊商標。
好,我正打扮得美美的躺在床上,聽見房門被打開的聲音。接著是腳步聲。我的男朋友來找我了……
唯一的問題是,我沒有男朋友。
好吧,我也沒有芙烈達卡蘿的造型,沒有個人專用的電話、電視和錄影機。只要我不在附近,我弟弟旦旦就會在我床上跳來跳去。看,我連自己的床都沒有。不過沒有這些我都還可以忍耐。我唯一的願望就是有個男朋友。
正當我想到要有男朋友的時候,一個金髮棕眼的帥哥向我迎面走來。他正繞過一輛停在人行道上的轎車。他閃到一邊好讓路給我,可是同時我也讓路給他,然後他閃到另一邊,而我也一樣!我們看起來好像在跳兩步舞一樣。
我結結巴巴的說:「喔喔,抱歉!」我想我的臉一定紅得跟關公一樣。
他倒是很冷靜,稍稍抬了抬眉毛,沒說什麼,只是對我微笑。
他對我笑耶!
我還在小鹿亂撞,渾身顫抖時,他已經從我身邊走過了。
我回頭看他,發現他也在回頭看我。真的。說不定……說不定他喜歡我。我在發什麼神經啊!他看起來至少有十八歲。這麼優的男生,怎麼會看上我這個笨手笨腳,連路都走不好的蠢丫頭?
他的眼光並不是往上看,而是向下掃過。天啊!他在看我的腿!天啊,我的裙子該不會真的太短了吧?昨天晚上我自己把它改短。安娜說她會幫我改,但是我知道她只會改個一兩公分。我可是要改成真正的短裙。只可惜我對縫紉不太拿手,裙擺的邊沒縫好,變得有點皺皺的。更慘的是,後來試穿時才醒悟,自己的腿有多粗多難看。
雖然安娜沒說什麼,但我知道她心裡怎麼想。
爸爸就比較直接,他說:「天啊,怎麼那麼短?內褲都快露出來了!」
我嘆口氣回答:「爸,我還以為你跟得上流行。現在大家都穿這種長度的裙子。」
這是真的。梅格妲還穿得更短。但是她的腿長,而且曬得很勻稱。她老是哀哀叫,說自己有蘿蔔腿。她以前學過芭蕾和踢踏舞,現在在學爵士舞。我知道她只是叫好玩而已,一點都不覺得自己的腿難看,不然她怎麼會一有機會就露一下呢?
娜黛的裙子也很短。她的腿很白,所以上學時都會加穿深色絲襪或白色褲襪。娜黛討厭曬太陽。她看起來像一隻蒼白的吸血鬼。她白白瘦瘦的,穿起短裙來很好看。
和兩個比你瘦很多的死黨在一起,真的滿讓人沮喪的,但要是連妳的小媽都比你瘦,那才真讓人沮喪到極點。我的小媽不但瘦,身材還和模特兒一樣。小媽安娜只有二十七歲,而且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小。我們一起出去時,人家都以為我們是姊妹。可是我們長得一點都不像。她又瘦又亮眼,我則是又矮又腫。
其實我不算胖,只是臉比較圓而已。好吧,我承認我全身圓滾滾的。肚子和屁股都又大又圓。胸部也一樣。梅格妲得靠魔術胸罩擠出乳溝,娜黛則是太平公主。
我不介意胸部大,只希望臀部可以小一點。老天,我的背影一定很恐怖,也難怪他會回頭看。
我快步跑過轉角,覺得自己是個大笨蛋。我的腿一直抖,連路都走不穩。兩條腿看起來好像也羞得漲紅了。看看它們,顏色和火腿一樣。我在騙誰啊?我當然很胖。裙腰緊得不得了。暑假時我又變胖了,不用量體重也知道。尤其是最後在小屋度過的三個星期增胖最多。
不公平。別人暑假都出國渡假,快樂得很。梅格妲去西班牙,娜黛去美國,我卻去我家在威爾斯的爛渡假小屋。那裡雨下個不停,潮濕得很。我成天待在屋子裡,如果不陪旦旦玩心臟病、抽鬼牌之類的幼稚遊戲,就只能看收訊不良的攜帶式黑白電視,或是穿著靴子在爛泥巴堆裡散步。無聊到這種地步,也難怪我一直吃東西解悶。
我每天除了吃三餐,還外加至少三十三頓點心。巧克力棒、糖果、爆米花、三角玉米片、洋芋片、冰淇淋。吃、吃、吃,肥肉抖、抖、抖。噁,我走路時膝蓋真的在抖。
我討厭走路。我實在看不出散步有什麼意義--繞來繞去繞個半天,然後又回到原點。我們在威爾斯時老是在散步。
爸爸和安娜總是走在最前面,小旦旦像瘋子一樣邊跳邊走,我則是無精打采的跟在後面,靴子浸在泥巴裡。我邊走邊想,這有什麼好玩的?世界上的渡假小屋那麼多,為什麼我家偏偏要買在威爾斯?為什麼不在西班牙買棟別墅,或是在紐約買層渡假用的公寓?梅格妲和娜黛就好幸運。好吧,梅格妲跟團出國住的是普通飯店,娜黛也只去了奧蘭多的迪士尼樂園,可是我打賭她們每天都看得到燦爛的陽光。
威爾斯老是在下雨,烏雲像被黏在天空上,根本沒有消失的時候。連小屋裡都在下雨。爸爸相信自己可以修好屋頂,結果總是越弄越糟。一排水桶和碗碟從一樓延伸到二樓,白天晚上都聽得到叮叮咚咚的漏水交響曲。
我們照往例參觀無聊的破舊城堡時,我已經受夠了,恨不得立刻從城垛裡解脫。我靠在城堡頂端的石牆邊,心臟還在狂跳(一路走到城堡頂真的很累),想著從上面跳下去會怎麼樣。如果我摔成一團肉醬,會有人在乎嗎?爸爸和安娜緊緊牽著旦旦,但是他們沒理我,就連我倚著牆探頭出去的時候也沒有。
他們牽著旦旦四處晃,咕噥一些外牆和熱油什麼的。他們做得太過火了。想當好爸媽也不用這樣。旦旦連「城堡」這個詞都寫不出來,更別妄想他會懂什麼城堡攻防戰了。我小的時候爸爸就沒對我這麼好。那時候他整天忙來忙去,連渡假的時候都在畫素描。可是我一點都不在意,因為我有媽媽。那時候有。
一想到媽媽,心裡就更難過。大家竟然以為我不記得她。他們瘋了。我記得她好多好多的事情,像是我們一起玩芭比娃娃,一起唱歌,還有她幫我化妝,讓我戴她的珠寶,穿她的高跟鞋和粉紅色真絲小外套。
我好想好想跟爸爸聊聊媽媽的事,可是每次只要我一提到她,爸爸就變得緊張沉默。他會皺眉頭,好像頭很痛一樣。他不想記起媽媽。反正他現在已經有安娜了,而他們兩個也有了旦旦。
我誰都沒有。我開始覺得好悲慘,於是一個人晃到別的地方。我走到城垛的另一邊,發現一座殘破的樓塔。入口被繩索圍住了,旁邊還有一個警告牌。我從繩子底下鑽過去,在黑暗中走上濕漉漉的階梯。走著走著,竟然一腳踩空,跌倒之外還撞到下巴。其實沒那麼痛,但是眼淚卻掉了下來,最後乾脆坐下來啜泣。
過了一會兒,我才發現自己沒帶面紙。眼鏡被眼淚弄得濕濕的,鼻涕也流個不停。我想辦法把眼淚和鼻涕抹掉。雖然石頭台階冷冰冰的,濕氣也滲透了牛仔褲,但我還是坐在那邊。我想我在等爸爸過來找我。我等了又等,終於聽到腳步聲。我坐直仔細聽,那是輕快的腳步聲。爸爸走路沒那麼輕,應該不是他。我還來不及走出去,就有人跌坐到我身上,兩個人齊聲尖叫。
「唉唷!」
「媽啊!」
「抱歉,我沒想到會有人坐在這裡!」
「你還賴在我身上幹嘛!」
「抱歉,抱歉。來,我拉你一把。」
「小心點!」那個人拉得太猛,兩個人差點一起滾下台階。
「糟糕!」
「小心!」
我掙脫他的手,背部緊緊貼著潮濕的牆。那個人也站了起來。四周太暗了,隱隱約約只看得到一個人形。
「妳一個人坐在這裡做什麼?妳沒有受傷吧?」
「之前沒有,但是現在可能有。我快被你壓扁了。」
「抱歉。我好像一直在說『抱歉』。但是蹲在黑黑的地方真的滿危險的。下次從你身上踩過的可能是一大群童子軍,或是一整車穿運動鞋的美國觀光客,或是……或是……我又在碎碎唸了。在黑壓壓的地方真的很難聊天。我們往上走,看看那裡會不會亮一點。」
「你走不上去的。往上階梯看起來已經垮了。」
「好吧,妳說得有道理。我們往下走出去吧。」
我遲疑了一下,很快用手背抹了抹臉。我想在這裡坐下去也沒意義。看樣子爸爸、安娜和旦旦已經忘了我,自己先回小屋去了。他們大概要到三天後才會突然發現我消失,說聲「愛莉呢」,然後聳聳肩,又把我拋到腦後。
那個男生大概以為我是因為害怕才會在原地不動。「妳想的話可以拉我的手,我帶妳走下去。」
我說:「不必了,我應付得來。」
嘴巴上是這樣說,但是向下走時階梯好像變得更滑,旁邊也沒有扶手繩,怪恐怖的。我絆了一下,他拉住我。「小心!」
我說:「我很小心了。」
他說:「我打賭現在有一個管理員在下面等著我們,準備好好唸我們一頓。唉,我就是這樣,每次一看到用繩索圍起來的地方,就忍不住要進去探險,所以身上老是青一塊紫一塊的。家人和朋友發現時就會叫我呆呆丹。我叫丹尼爾,不過他們只有在真的很火大時才會叫我丹尼爾。平常大家都叫我丹。」
他就這樣一路碎碎唸,唸到走出樓塔時才停下來。丹的頭髮又翹又亂,鼻子是小小的獅子鼻,看起來很驢。他皺了皺鼻子,把眼鏡推回原來的位置。
我的鏡片髒髒的。我眨了眨眼睛,努力對焦。
「原來是你啊!」我們同時叫了出來。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Girls﹝1﹞:第一次碰到愛情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90 |
二手中文書 |
$ 148 |
中文書 |
$ 149 |
少兒文學 |
$ 152 |
兒童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Girls﹝1﹞:第一次碰到愛情
這是一本快樂、輕鬆、爆笑的愛情輕小說;節奏明快,妙語連珠,內容與語言風格都非常貼近新世代少女的思想與生活。書中所探討的問題,很多人都會遇上:同儕壓力、單親家庭、男女關係、父母問題……。作者賈桂琳.威爾森非常擅長描寫青少年心理,女生固然感同身受,男生亦可學習從女性觀點看事情。《第一次碰到愛情》是 “Girls”系列四部曲的第一炮,小說內容分為九章,每一章皆和九件有趣的事情串聯起來,如艾莉的九個偶像、學校裡最討厭的九件事、九件糗事等等,讀者可以輕鬆進入坦白、直率又充滿夢想的艾莉的內心世界。
章節試閱
梅格妲說:「感覺很棒吧!」她剛剛又跟我們講她的羅曼史。 娜黛一臉同情的看著我說:「艾莉,等妳有了男朋友就會了解的。」 真是夠了。 我一時脫口而出:「別擔心,我已經有男朋友了。」 娜黛瞪著我。 梅格妲瞪著我。 我像是靈魂出竅,在半空中瞪著自己。 我說了什麼? 我在幹什麼啊? 我怎麼會說出這種話? 可是,已經來不及了……第一章 一個女孩開學第一天,沒趕上校車,只好走路上學。滿糟的開始。九年級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呢?九號、九號、九號……這是披頭四經典<白碟>(White Album)專輯裡的歌...
»看全部
目錄
第一章 一個女孩
第二章 二個好朋友
第三章 三個男朋友
第四章 四口之家
第五章 五個倖存者
第六章 六封信
第七章 七重天
第八章 八點到深夜
第九章 九九九
第二章 二個好朋友
第三章 三個男朋友
第四章 四口之家
第五章 五個倖存者
第六章 六封信
第七章 七重天
第八章 八點到深夜
第九章 九九九
商品資料
- 作者: 賈桂琳‧威爾森
- 出版社: 遊目族 出版日期:2006-03-27 ISBN/ISSN:9577458920
-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144頁
- 類別: 中文書> 少兒親子> 少兒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