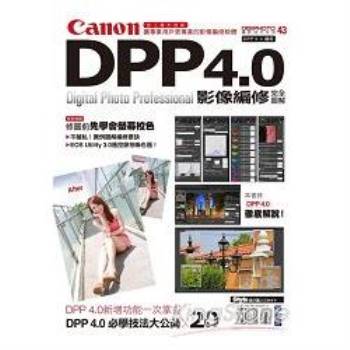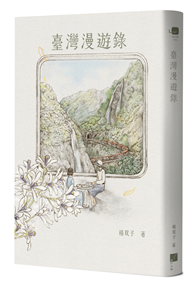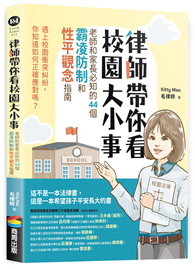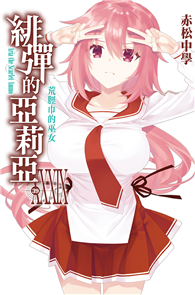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青銅器論文集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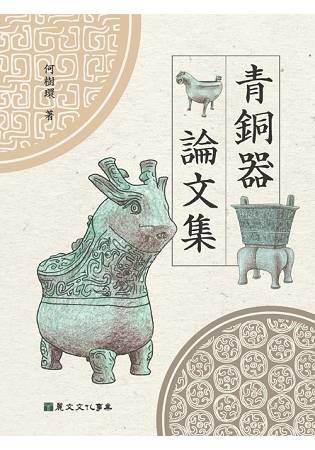 |
青銅器論文集 作者:何樹環 出版社: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02-28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74 |
歷史 |
$ 540 |
中文書 |
$ 540 |
高等教育 |
$ 540 |
科學科普 |
$ 570 |
史地 |
$ 570 |
Social Sciences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青銅器論文集
內容簡介
本書收錄了9篇文章,都是以「兩周青銅器」為範圍所進行的一些探討。雖說範圍是「兩周青銅器」,但所涉及的也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如兵器就全然未被論及,以總的方向在於此,遂題名為《青銅器論文集》。各篇文章內容和具體討論的問題包括︰銘文文字和文句的釋讀、銅器年代排序的討論、銅器銘文間的比對,乃至於器物形制與名稱、器物組合等幾個面向。總的目的則是試圖於銘文字形、文字意義的探索之外,結合二種以上的材料或討論面向,發掘隱藏於青銅器中,遺留的歷史訊息與痕跡。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何樹環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現為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教授中國文字學、古文字學、銅器銘文、訓詁學、中國上古史等課程。長期來以銅器、銘文,及二者與歷史間的對比與綜合為研究時關注的主軸。已出版之專書有《西周土地所有權研究》、《西周對外經略研究》、《西周錫命銘文新研》;論文集有《青銅器與西周史論集》,及會議、期刊論文近三十篇。
何樹環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現為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教授中國文字學、古文字學、銅器銘文、訓詁學、中國上古史等課程。長期來以銅器、銘文,及二者與歷史間的對比與綜合為研究時關注的主軸。已出版之專書有《西周土地所有權研究》、《西周對外經略研究》、《西周錫命銘文新研》;論文集有《青銅器與西周史論集》,及會議、期刊論文近三十篇。
目錄
師兌二器排序問題檢討
《金文人名彙編》及《修訂本》增補正訛——西周之部(一至二劃)
西周銅器所見成國相關人名集釋——附許國
讀西周銘文小劄(二則)
商周異器同銘銅器之銘文類例探析及相關問題探析
西周晚期與春秋時期銅器稱名之時空差異
楚國銅器研讀劄記——繁鼎之相關問題
東周鼎制新探──東周墓葬的歷時觀察
銅器稱名及其與墓葬器物組合相連結所建構的歷史片段
《金文人名彙編》及《修訂本》增補正訛——西周之部(一至二劃)
西周銅器所見成國相關人名集釋——附許國
讀西周銘文小劄(二則)
商周異器同銘銅器之銘文類例探析及相關問題探析
西周晚期與春秋時期銅器稱名之時空差異
楚國銅器研讀劄記——繁鼎之相關問題
東周鼎制新探──東周墓葬的歷時觀察
銅器稱名及其與墓葬器物組合相連結所建構的歷史片段
序
自序
這本小冊子裏面收錄了9 篇文章,都是以「兩周青銅器」為範圍所進行的一些探討。雖說範圍是「兩周青銅器」,但所涉及的也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如兵器就全然未被論及。內容和具體討論的問題雖未能遍及兩周青銅器的方方面面,但總的方向仍在於此,遂題名為《青銅器論文集》。非敢冒用此一總名,取其近似且不相違離故也。
所收錄的 9 篇文章以時間先後來看,可分為2 組。一組是2013 年之前因不同機緣曾發表的舊作,共有4 篇;另一組是2013 年8 月之後陸續所寫的5 篇文章。4 篇舊作的主要觀點沒有明顯地改動,此次收錄時做了若干論述和說明上必要的修訂,對先前遺漏的材料,以及後來始見的相關討論也有所補充。至於近3 年由初稿到逐漸修訂成形的5 篇新作中,〈楚器研讀劄記〉修訂4 稿於2015 年的11 月,曾在兩岸中山大學中國文學學術研討會中宣讀過。9 篇文章在這本小冊子的排列,基本就以書寫時間先後為序,其中與金文所見人名有關的兩篇,是以不同方式對此一主題的試寫之作,排在一起,恰與時間原則亦可相符。
依一般性的看法,這 9 篇文章所關注的面向較不集中,包括銘文文字和文句的釋讀、銅器年代排序的討論、銅器銘文間的比對,乃至於器物形制與名稱、器物組合等幾個面向。但我自己並不是這樣看待這9 篇文章的。銘文文字和文句的釋讀,是文字、訓詁的工夫,銅器年代和銘文自身間的連繫,與歷史學關係較密,器物形制與器物組合則是考古學擅長的領域。用現代的眼光來說,上述三者分屬不同學系的專長,但就青銅器的研究而言,個人認為不要過於區別,又或者在研究中能顧及、運用二者以上,會是較好的。古人做學問,除了知識的討論之外,還能形成「氣象」、追求「境界」。「分」對於知識的討論而言,或許還帶有一些不得不,而「氣象」與「境界」絕對不是僅靠「分」就可以企及,這點則是十分確定的。大學以來一直就讀於中文系的我,試著努力補足青銅器研究中,中文系以外的必要性因素,倒有點像是青銅器不斷提醒我:想理解這門學問,還早得很呢!瞧瞧,這也缺,那也漏,哪裏像個「器」?看著這9 篇文章,不禁這樣覺得:蓋房子不能僅靠一根支柱,雖然不知道自己這座屋子最後是否蓋得成,又或者可以蓋多高?成什麼樣?但過程中多立些柱石,即使最終不是高樓廣廈,或許也還能夠不太偏狹,經受得住一些風雨。這9 篇文章做的仍舊是知識層面的工夫,但多補些洞,多立些柱石,多保持一些「合」的連結與可能性,對領會、證得學問的「氣象」與「境界」,應該還是有些助益的。
如果用不太現代的方式來為這本小冊子命名,我想題為《井中記》,這是我在青銅器這個礦井中的挖掘記錄。如果說這份記錄對別人還能有些作用的話,我希望留下的不是「挖到了什麼」,而是「可能可以挖到什麼」。對於一心只想尋得石油的人而言,遇見的任何珍稀礦產都形同廢物。是以「挖到了什麼」不僅已成過往,對後來的挖掘者而言,雖可能有些參考作用,但無可避免地也將造成無形的束縛。相對地,「可能可以挖到什麼」,對已在挖掘和後來想挖掘的人而言,都是「現在進行式」,是帶著未知與不可預期地驚奇與冒險,是可以更隨著個人情性發展與開拓的領域。而這份記錄對我個人所具有的特殊意義,就是提醒著自己:原來我始終還在井裏。
這本小冊子裏面收錄了9 篇文章,都是以「兩周青銅器」為範圍所進行的一些探討。雖說範圍是「兩周青銅器」,但所涉及的也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如兵器就全然未被論及。內容和具體討論的問題雖未能遍及兩周青銅器的方方面面,但總的方向仍在於此,遂題名為《青銅器論文集》。非敢冒用此一總名,取其近似且不相違離故也。
所收錄的 9 篇文章以時間先後來看,可分為2 組。一組是2013 年之前因不同機緣曾發表的舊作,共有4 篇;另一組是2013 年8 月之後陸續所寫的5 篇文章。4 篇舊作的主要觀點沒有明顯地改動,此次收錄時做了若干論述和說明上必要的修訂,對先前遺漏的材料,以及後來始見的相關討論也有所補充。至於近3 年由初稿到逐漸修訂成形的5 篇新作中,〈楚器研讀劄記〉修訂4 稿於2015 年的11 月,曾在兩岸中山大學中國文學學術研討會中宣讀過。9 篇文章在這本小冊子的排列,基本就以書寫時間先後為序,其中與金文所見人名有關的兩篇,是以不同方式對此一主題的試寫之作,排在一起,恰與時間原則亦可相符。
依一般性的看法,這 9 篇文章所關注的面向較不集中,包括銘文文字和文句的釋讀、銅器年代排序的討論、銅器銘文間的比對,乃至於器物形制與名稱、器物組合等幾個面向。但我自己並不是這樣看待這9 篇文章的。銘文文字和文句的釋讀,是文字、訓詁的工夫,銅器年代和銘文自身間的連繫,與歷史學關係較密,器物形制與器物組合則是考古學擅長的領域。用現代的眼光來說,上述三者分屬不同學系的專長,但就青銅器的研究而言,個人認為不要過於區別,又或者在研究中能顧及、運用二者以上,會是較好的。古人做學問,除了知識的討論之外,還能形成「氣象」、追求「境界」。「分」對於知識的討論而言,或許還帶有一些不得不,而「氣象」與「境界」絕對不是僅靠「分」就可以企及,這點則是十分確定的。大學以來一直就讀於中文系的我,試著努力補足青銅器研究中,中文系以外的必要性因素,倒有點像是青銅器不斷提醒我:想理解這門學問,還早得很呢!瞧瞧,這也缺,那也漏,哪裏像個「器」?看著這9 篇文章,不禁這樣覺得:蓋房子不能僅靠一根支柱,雖然不知道自己這座屋子最後是否蓋得成,又或者可以蓋多高?成什麼樣?但過程中多立些柱石,即使最終不是高樓廣廈,或許也還能夠不太偏狹,經受得住一些風雨。這9 篇文章做的仍舊是知識層面的工夫,但多補些洞,多立些柱石,多保持一些「合」的連結與可能性,對領會、證得學問的「氣象」與「境界」,應該還是有些助益的。
如果用不太現代的方式來為這本小冊子命名,我想題為《井中記》,這是我在青銅器這個礦井中的挖掘記錄。如果說這份記錄對別人還能有些作用的話,我希望留下的不是「挖到了什麼」,而是「可能可以挖到什麼」。對於一心只想尋得石油的人而言,遇見的任何珍稀礦產都形同廢物。是以「挖到了什麼」不僅已成過往,對後來的挖掘者而言,雖可能有些參考作用,但無可避免地也將造成無形的束縛。相對地,「可能可以挖到什麼」,對已在挖掘和後來想挖掘的人而言,都是「現在進行式」,是帶著未知與不可預期地驚奇與冒險,是可以更隨著個人情性發展與開拓的領域。而這份記錄對我個人所具有的特殊意義,就是提醒著自己:原來我始終還在井裏。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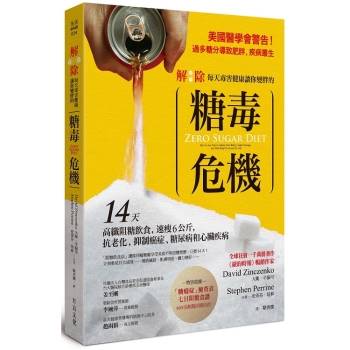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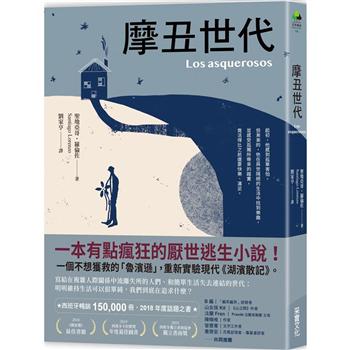
![念君歡卷四] 念君歡卷四]](https://cdn.kingstone.com.tw/book/images/product/20185/2018561884609/2018561884609m.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