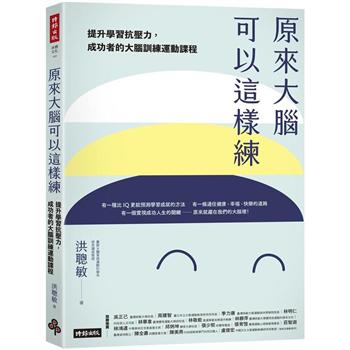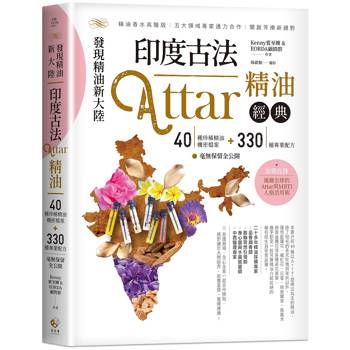藝術家的思維模式
臺灣藝術現代化過程中,思維方式的西方化乃是促使藝術完全進入現代化的關鍵因素。自日據時代開始,臺灣藝術家以西方為師,以尋求西方文化根源的努力,隨著社會現實的改變而調整前進的腳步,初期學習的是技法,中期是理論,最後是思維方式。如今,大家終於了解到,只有技法與理論的模仿,並不足以創作現代藝術,重要的是要了解西方現代人如何想像人與其所處的空間和時間之關係,以及那建構自我成為有意義之個体的全套思維模式。
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在他的名作<詞與物>中稱,在十九世紀中葉之前,一般藝術理論的四個領域: 再現(representation)理論、表達(articulation)理論、指明(designation)理論、衍生(derivation)理論,支撐著藝術家的思維方式。印象派之後,藝術思維的方式被四個理論所取代,它們是人的有限性(finitude)、經驗與先驗(the empirical and the transcendental)的互証、我思與非思(the cogito and the unthought)、起源與歷史等理論。這四種理論構成了現代思想的基本架構,此認識論上的四邊形,雖看似各自獨立,實則相輔相生。
一、 人的有限性
在西方古典時期,當人們在思考人是什麼的時候,人們是以上帝為中心在提問,其真正的意涵是: 「對上帝而言,人是什麼?」。在現代時期,神的地位失落,問題已便成: 「對人類而言,人是什麼?」在現代時期,人的存在意義是以自我為最後的判斷標準,其本質是有限的。
在現代思想中,事物被定位在其各自的內在規律內,而人的存在附屬於事物,人的存在與事物產生直接的聯繫。人的存在既然從屬於物,物是有限的,因而人也是有限的。人如同物一樣,有其歷史的起源與終結; 人因為勞動、生活、說話,因此人的存在必然不是永恒而超越的,他必定從這些與物的關係才能彰顯出來。人的有限之存在由知識的實証性所預報或彰顯。在現代思想中,人不再是獨立於萬物之外超然之存在,人只是生物之一,其生命是有限的,而且不能逃避生老病死的命運。
在藝術再現問題上,二十世紀初以來,現代藝術家熱衷於這樣的提問: 在什麼條件、基礎、界限內,物如何被再現? 物能出現在一個比各種知覺方式都要深遠的地方嗎? 並且,在藝術與物的這一共存中,通過由再現所揭示的,是否正是現代藝術家的有限性。事實上,在西方文化中,藝術家的存在和造型藝術的存在從未能共存與相互連接,它們的不相容乃是現代思想的基本特徵之一。
藝術家的生命若要真實的被再現出來,藝術語言就必須消失,反之,後者的存在,必須以藝術家生命的無止境的消失為代價,情形正如我們在古典繪畫所見到的一樣。在達文西的繪畫中,世界被藝術語言所建構,在蒙娜麗莎的微笑中,達文西的生命永遠在向後撤退,我們無法看清楚藝術家的任何身影。在西方古典藝術中,藝術家的存在和造型語言的存在,的確從未能共存過。
二、 經驗與先驗
現代藝術的基本任務乃試圖要調和上述這個矛盾現象,但其所用的方法是建立在經驗與先驗相互保証上,雖然這種保証永遠存在著認知上的危機。這是因為經驗與先驗的交互保証方式,缺少一種形而上學的基礎。形而上學研究有與存在的問題,但人既是有限的存在,形而上學對人的存在問題就失去其用途。如此便產生了從經驗內容中,尋求先驗真理的答案,而經驗與先驗的交互保証,提供的確實是一種封閉的辯証思想。因此,在辯証作用與一個不具形而上學的本体論相互呼應之下,現代人在思考藝術的本質時,他總是朝著已被自已事先設定好的答案進行。這種思考方式伴隨著雙重現象,既是經驗,又是先驗; 既是實証性的,又是本体的。
現代思想的特徵之一是在分析真理之前,我們先設定某種不能自我明証的判斷標準,此標準反過來成為分析真理的可靠性依據,即判斷標準是先驗的,是由經驗內容所推演出來的,而非已經存在的事實。依此,在論斷真假與其所使用的判斷標準之間,存在著推論上的的迴路,其性質屬於循環邏輯。在現代性的思維方式中,人已成為傅柯所說的,一個奇特的經驗與先驗的對子,而現代人正是以這樣的方式,接受所有知識成為可能的一切。
在現代思想中,人類知識生產決定於其形式,但此形式是經驗的真實內容所彰顯的。知識內容的本身即是人做為反思的範圍,其獲得來自一系列對事物的劃分或分割。經驗世界是人判斷事理的基礎,此基礎所建立起的法則又是判斷的客觀標準。在面對實際的經驗分析時,現代藝術家設法把自然的客觀性與通過感覺所勾勒出來的經驗連接起來,亦即把一種文化的歷史與語言學連接起來。因此,這種思考方式可以說是,藝術家們為了要襯托出個人的經驗與先驗之間的距離,而所做的努力。現代藝術所依賴的造型符號使得經驗與先驗保持分離,但又同時保持相關 這種造型符號在性質上屬於準感覺和準辯証法,其功能在把肉体的經驗和文化的經驗連接起來。
三、 我思與非思
現代藝術家的存在方式總是開放的,它存在於我思的思想活動中,但同時它又從純粹的領悟進到經驗充塞,進到那些避開自身經驗的非思境域。現代形式的先驗反思針對的總是某種有關未知的存在,這種存在是沉默的,但又是藝術家不斷地試圖以可能的造型符號所要貫穿的對象。從這個未知出發,現代藝術家不停地被呼籲要自我認識。
現代人當然也思考,但在目的上已跟過去不同。現代的我思不同於笛卡爾的我思,對笛卡爾來說,我思,才能消除謬誤或幻覺。相反地,在現代我思中,問題是如何分割我思與來自思且根植於非思的一切區分開,卻又要把它們聯繫起來。在人的思考方面,現代人發現一個比會思考的我更難纏的我,那就是不思考的我,即非思。
現代思想詢問的是我思如何能處於非思的形式之中。藝術家既要思考造型藝術的存在,又要思考個人生命的存在。這是現代藝術家不同於古典時期藝術思維之處。在古典時期的藝術再現中,藝術家個人生命是隱蔽的,他的存在屈從於他所使用的造型語言之下,在思考再現物的世界時,藝術家與他的非思,是界限分明的。但在現代藝術裡,藝術家總是在創作之際,思考著要如何連接、表明和釋放那些足以表現他個人的存在之語言或概念,換言之,他試圖將他的我思與非思串聯在一起。既要再現物的表象,又要再現藝術家個人的存在,這便是現代藝術家所面臨的問題。
四、 起源與歷史
在十八世紀,西方藝術家把自然秩序想像成一張圖表,表中存在著由物所聯繫成一個網絡,從這個秩序的一點到另一點,藝術家們就在一種準同一性的內部移動,從這個序列的一端到另一端,藝術家們就受光滑的、相同的層面的引導,把造型語言的起源看作物的表象與物的形狀、色彩、体積和空間的摹本。在這樣一種思想中,年代學的發展處於一張圖表的內部,並且在這張圖表上,年代學的發展只構成一次瀏覽,出發點就既在真實的時間之外,又在其中,這個出發點就是這個最初的摺痕,所有的歷史事件都是通過這個摺痕而得以發生的。
時間是人類所定出的思考模式之一。物並無記憶,但人類有記憶的本能。人類以自身的經驗建立起物的時間表(年代學),此舉乃是為了人自身的利益,為了建構人的記憶之確定性。時間表提供人類思考經驗的過程,但對現代人而言,時間本身並非僅僅是一張平面光滑的圖表而已,它也具有自身的生命,有其起點和終點。事物的起源必得仰賴人的記憶。
但因物的起源在宇宙開始時便已存在,以物為中心點,成為建構起源的工具,尋找人的起源已成為現代人的一大問題,亦即,以時間系列建構一個永遠不存在起源點的起源故事,起源永遠只能在思想中存在。因此,其起源永遠處於不確定的狀態。它的不確定性已成為現代人思考上的焦慮來源。這是因為人必須從生命、自然、歷史等,找到認同。
自從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the Phenomenology of Mind)以來,現代思想已確立起一種藝術與起源的關係,那就是以物為主体時,現代思想努力把藝術的年代學放入物的年代學的內部,以使得藝術的起源有一個日期,存在於物的連續系列中的一個點。以人為主体時,現代人根據人的年代學,有條理地說出人對物的經驗,並由此建構出與時間有關的各種藝術學科知識,如藝術史、美學史、風格史、批評史、理論史等。
因此,對現代藝術思維來說,並不存在著可能的道德,或任何普同的價值標準。自十九世紀中期以來,現代藝術思想的整個特有的存在,已不再是一種理論,而是一種實踐綱領。古代價值標準與宇宙秩序相連接,並且透過對宇宙運行法則的建構,就能從中推演出藝術生產原則,在這普同的藝術價值觀裡,藝術家被要求必須遵守歷史所累積下來的傳統價值標準。相反地,現代價值標準並沒有標舉一種道德觀,正是人的有限性、經驗的先驗法則、隱藏於自身的我思與非思、起源的反思,構成了現代藝術價值的內容和形式。
此四種理論所構成的現代認知,雖開始於西方十九世紀初,但自一九五○年代末,隨著現代思想在臺灣的引進,已經逐漸成為我們的思考方式之一,並已在多數藝術實踐者之中,形成某種牢不可破的思維模式。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西方美學關鍵思維的圖書 |
 |
西方美學關鍵思維 作者:曾長生 出版社: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0-05-0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56頁 / 17 x 23 x 1.28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32 |
美術 |
$ 432 |
藝術設計 |
$ 446 |
中文書 |
$ 446 |
藝術總論 |
$ 456 |
藝術理論 |
$ 456 |
藝術學群 |
$ 456 |
藝術設計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西方美學關鍵思維
臺灣適合閱讀的藝術理論專書不多,且多分散於哲學、文學、文化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美術史與藝術家傳記等論著中。本書即結合了美學、藝術史與創作理論,深入探討西方美術史(從文藝復興時期到後現代)演變的文本中,具代表性的關鍵論述。這本經作者多年時間研讀整理出來的心得,計二十二篇專文,多參考自西文權威著作。每篇並於文前附有提要,文後則列舉討論議題與圖片說明,以供讀者參閱思考。另附有關鍵詞索引,適合大專美術相關科系學生做為藝術理論教材,一般藝術專業人士和美術收藏家也可將之做為補充讀物。
作者簡介:
曾長生
紐約普萊特藝術研究所創作與評論雙碩士(1990年)
臺灣第一位藝術評論博士(2010年)
臺灣美術院院士 (2010年)
中華民國畫學會藝術理論類金爵獎得主 (2018年)
除了藝術家之外,另一個身份是外交官,自 1970 年代便開始長期旅居海外,曾駐留歐洲、南美洲以及北美洲等地。特殊的跨領域背景以及豐富的遊歷經驗,使他早期的創作多圍繞在流浪、歸巢以及環境的變遷等主題上面。南美洲的動物、熱帶雨林以及北美洲的荒原是他的畫面中經常出現的元素,繪畫形式上面則延續了野獸派、立體派、超現實主義以及構成主義,並且巧妙融合了東方、拉丁美洲以及現代前衛藝術的精神,形成曾長生獨樹一格的跨文化個人美學,迄今他已在歐亞及南北美洲舉辦過逾四十次個展,藝術論著近六十種。
章節試閱
藝術家的思維模式
臺灣藝術現代化過程中,思維方式的西方化乃是促使藝術完全進入現代化的關鍵因素。自日據時代開始,臺灣藝術家以西方為師,以尋求西方文化根源的努力,隨著社會現實的改變而調整前進的腳步,初期學習的是技法,中期是理論,最後是思維方式。如今,大家終於了解到,只有技法與理論的模仿,並不足以創作現代藝術,重要的是要了解西方現代人如何想像人與其所處的空間和時間之關係,以及那建構自我成為有意義之個体的全套思維模式。
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在他的名作中稱,在十九世紀中葉之前,一般藝術理論的...
臺灣藝術現代化過程中,思維方式的西方化乃是促使藝術完全進入現代化的關鍵因素。自日據時代開始,臺灣藝術家以西方為師,以尋求西方文化根源的努力,隨著社會現實的改變而調整前進的腳步,初期學習的是技法,中期是理論,最後是思維方式。如今,大家終於了解到,只有技法與理論的模仿,並不足以創作現代藝術,重要的是要了解西方現代人如何想像人與其所處的空間和時間之關係,以及那建構自我成為有意義之個体的全套思維模式。
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在他的名作中稱,在十九世紀中葉之前,一般藝術理論的...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序言
前言—藝術家的思維模式
第一章 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演變—由崇敬米開蘭基羅到肯定威尼斯的審美價值
一、阿伯提的十五世紀佛羅倫斯地區文藝復興理想
二、達文西的繪畫思想充滿了新柏拉圖主義的神祕感
三、米開蘭基羅的理想美造型與杜勒對絕對美的懷疑
四、威尼斯的藝評家贊賞提香的色彩表現
五、折衷主義的出現與瓦薩里的三階段論
六、瓦薩里由崇敬米開蘭基羅到肯定威尼斯的審美價值
第二章 美學家阿伯提的人文素養—兼談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美學
一、阿伯提是人文主義...
前言—藝術家的思維模式
第一章 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演變—由崇敬米開蘭基羅到肯定威尼斯的審美價值
一、阿伯提的十五世紀佛羅倫斯地區文藝復興理想
二、達文西的繪畫思想充滿了新柏拉圖主義的神祕感
三、米開蘭基羅的理想美造型與杜勒對絕對美的懷疑
四、威尼斯的藝評家贊賞提香的色彩表現
五、折衷主義的出現與瓦薩里的三階段論
六、瓦薩里由崇敬米開蘭基羅到肯定威尼斯的審美價值
第二章 美學家阿伯提的人文素養—兼談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美學
一、阿伯提是人文主義...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