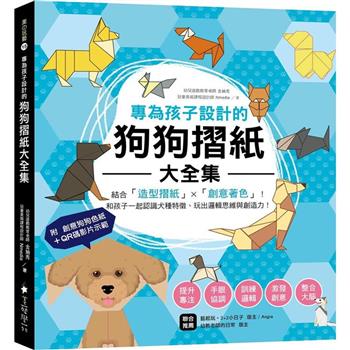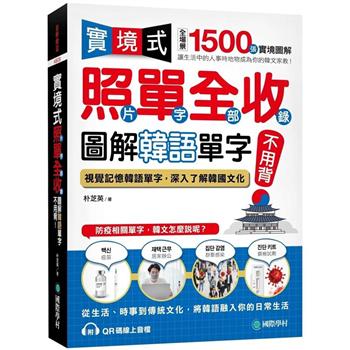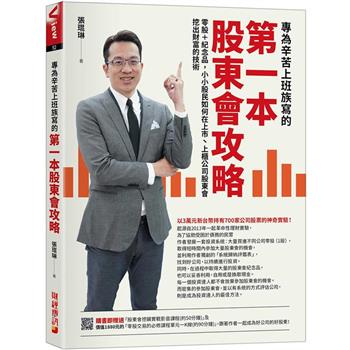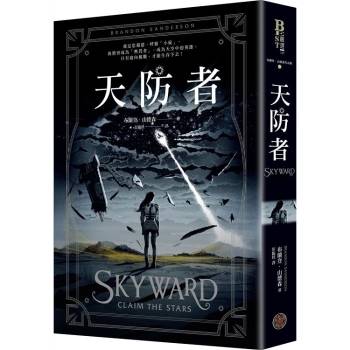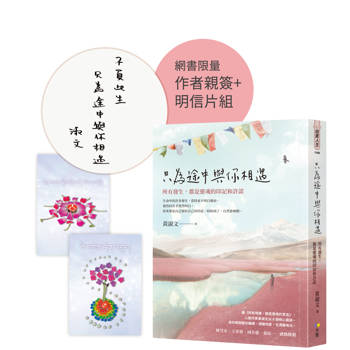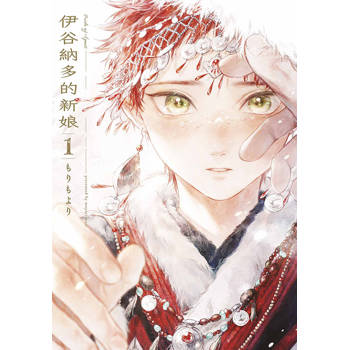第一章 緒論:唐朝對西南的經營—以蜀地為例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蜀地群山環繞,山川形勢險要,北有摩天嶺、米倉山、大巴山等秦巴山脈,西北接岷山,斜向東南伸展,形成蜀地和漢中盆地的天然界線高1,000∼3,000公尺。東部巫山,由長江橫斷產生三峽險峻地勢。南部有大婁山,西接雲貴高原北側邊緣,高1,000∼1,500公尺,山雖不高但坡度陡峭,為川南障壁。西部有大雪山和松潘高原,為青康藏高原東側,高2,000∼4,500公尺,地勢最高。蜀地四周為高山,中部為四川盆地地勢較低,此外,中部有河川由西向東依次為岷水(岷江)、涪水(涪江)、西漢水(嘉陵江)、渠水(巴江),呈向心匯聚水系入長江,三峽為唯一的水道出口。
蜀道的重要性在於唐朝皇帝遇到長安政權危機時,屢次入蜀避難,方得以度過危機,《穀山筆麈》卷12〈形勢〉:
唐都長安,每有盜寇,輒為出奔之舉,恃有蜀也,所以再奔再北而未至亡國,亦幸有蜀也。長安之地,天府四塞,辟如堂之有室,蜀以膏沃之土處其閫閾,辟如室之有奧,風雨晦明有所依而蔽焉。蓋自秦、漢以來,巴、蜀為外府,而唐卒賴以不亡,斯其效矣。
唐朝皇帝選擇蜀地作為庇護所,在於仰賴蜀地的特殊地理形勢與豐富物產資源,使唐朝政權得以延續而不亡。
唐玄宗與僖宗第一次從長安南幸巴蜀,駐蹕地點在劍州成都府,屬劍南道管轄。而唐德宗與僖宗第二次入蜀均南幸梁州(漢中興元府),也是繼唐玄宗後因京師叛亂,利用蜀道南逃途經漢中避難,再成功返回長安繼續執政。唐朝皇帝由京師長安南幸入蜀到成都府避難,沿途需經過京畿道、山南西道,至劍南道。因此,本文所指「蜀地」包含山南西道的漢中郡(後改為興元府)和劍南道的巴蜀。
由於唐玄宗與僖宗第一次入蜀均駐蹕在成都,德宗與僖宗第二次南幸則停留在漢中郡(興元府),成都府隸屬劍南道,漢中郡(興元府)隸屬山南西道,因此,考察山南西道與劍南道的發展狀況,最能反映唐朝皇帝入蜀或南幸時的供備情況。
本文欲探討為何玄宗、德宗、僖宗南逃期間,選擇留駐在漢中郡(興元府)或巴蜀?愚意以為在於「蜀地」具有得天獨厚的雙重優勢,不但有富庶的經濟發展,更有優越的軍事防衛條件,使得玄宗、德宗、僖宗南幸,選擇留駐在漢中與巴蜀避難。
首先,當玄宗、德宗、僖宗因京師變亂臨時出逃到漢中或巴蜀,若無事先累積足夠的經濟條件,如何因應皇帝南幸避難期間所需的糧食與供備?本文欲藉由考察唐初至唐中葉,劍南道與山南西道的經濟發展與水利開發,探究西南「蜀地」的經濟發展狀況與條件。
令人不解的是劍南道具有流民、山獠反亂、吐蕃南詔興起等造成治安問題,及蜀地的逃戶等問題,諸多不利於人口成長的負面因素下,為何劍南道戶口數仍持續增長?劍南道戶口數的增長原因為何?究竟是經濟環境造成人口自然成長,還是因外地人口自行遷入蜀地?或是因唐朝地方官員的積極經營,才克服治安與逃戶問題,使得劍南道戶口數仍持續增長?
其次,唐朝玄宗、德宗、僖宗三位皇帝四度避亂,為何均選擇入蜀地逃難,不選擇其他去處?顯然不是偶然的巧合。「蜀所恃,有險也;蜀所安,無役也。」唐代帝國興衰榮辱與皇帝的政治命運,與「蜀地」的軍事建設息息相關。
關於唐代在全國設置的驛道,以首都長安都亭驛為中心,可分為七條路線:一是營州入安東道,二是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三是夏州塞外通大同雲中道,四是中受降城入回鶻道,五是安西入西域道,六是安南通天竺道,七是廣州通海夷道。這七條幹線中,以往學界運用敦煌吐魯番文書,將研究集中於西北路線的西域道。
但事實上,唐朝有兩條值得重視的交通命脈:一條是往東亞路線的安東道,另一條是往西南路線的蜀道。東亞路線礙於文獻史料,在研究上較困難。拙稿擬關注的「蜀道」指由長安的都亭驛到劍南道益州、姚州的西南線,成為唐代政治經濟軍事命脈的要道,此路線一直延續到明清時期非常重要的「茶馬古道」。「蜀道」為何是唐朝的政治經濟命脈?為什麼是唐玄宗、德宗、僖宗和朝廷官員的逃亡路線?可知劍南道必定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與政治重心。愚意以為安史之亂前,皇帝已積極部署,將節度使、主帥與軍隊、物資運輸緊密結合,為日後入蜀做準備。
唐朝歷代皇帝幾乎都很重視蜀道,唐高祖時修復駱谷道,太宗、玄宗、憲宗、敬宗、文宗、宣宗、僖宗先後在「褒斜散關道」設置館驛,唐玄宗開闢荔枝道,宣宗大中年間重新開闢文川谷道。唐朝玄宗、德宗、僖宗共四次仰賴蜀道出奔逃難,最後都能安然返回首都,蜀道牽動唐帝國的興榮盛衰與政治命運,蜀道在交通運輸上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關於唐代交通研究方面,以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四卷山劍滇黔區)最具代表,該書詳盡考證唐代入蜀交通網,以及繪製唐代蜀道的傳驛路線、館驛與路程。劉希為《隋唐交通》論述隋唐的交通路線,但對於驛道的概念僅記述以長安為中心而已。青山定雄《唐宋時代の交通と地誌地圖の研究》論述唐宋時代的陸路交通,郵驛制度的發達,關津增減與分布,商稅與轉運使,以及製作地誌地圖的研究,並繪製唐代主要交通圖、水路圖與漕運圖。荒川正晴《ユ—ラシアの交通‧交易と唐帝國》研究唐代交通系統,偏重河西以西的交通制度,兼論北庭地區的傳驛制度、長行坊和軍物輸送。上述諸研究,均未探究巴蜀地區的交通路線,拙稿則擬增補這方面的缺漏。
學界對於傳驛制度研究成果頗豐,拙稿論述從《天聖‧廄牧令》探討唐宋監牧制度中畜牧業經營管理,吳淑玲《唐代驛傳與唐詩發展之關係》論述唐代驛傳體系對於驛路詩發展、異地交流、詩歌傳播、詩歌團體形成、詩風變遷影響與角色。拙稿欲以山南西道與劍南道為中心,從交通運輸的角度探討長安到成都的蜀道,對中晚唐政局的獨特性角色。
大陸學界對四川成都專著,段渝等主編《四川通史》(第3冊兩晉南北朝隋唐時期)、謝元魯《成都通史》(卷三 兩晉南北朝隋唐時期)詳論四川政治地位、外族戰爭、人口移民、農商業發展、佛道教興盛、藝術與學術興起,但未突顯出蜀道的交通運輸,對四川發展的重要性。有關巴蜀交通與西南路線,目前最詳盡專論為藍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線史》、《南方絲綢之路》、《交通貿易與西南開發》系列專著。但藍勇研究偏重經濟貿易,如絲綢、鹽棉等商品經濟發展。梁中效〈唐朝皇帝與蜀道〉分析唐朝皇帝重視蜀道的原因、經過與影響,但未論及蜀道在軍事和財政上的交通運輸的重要性。另外,王興鋒〈唐玄宗奔蜀路線考述〉,考察唐玄宗奔蜀在關內道、山南西道、劍南道路線,拙稿擬深入分析論述蜀道在政治、軍事的重要地位。
日本學界有關四川的最新論著,有中林史朗《中國中世四川地方史論集》論述先秦兩漢至魏晉南北朝巴蜀政權與變亂、益州發展。及大川裕子編《中国古代の水利と地域開発》探討古代巴蜀開發、秦川西平原的水利開發、四川盆地丘陵地開發。惜兩部論著僅論及兩晉南北朝巴蜀的發展,本研究欲擴展研究斷代至唐代,透過蜀道的交通運輸,分析唐代對於巴蜀的開發。
針對劍南道研究有多部碩士論文,臺灣學界偏向研究四川、劍南道與中央關係,如賴亮郡《唐代四川與中央關係之研究》、張世偉《唐代劍南道的重要性及其分合與中央關係之研究》、黃俊文《唐代劍南邊防之研究》論述劍南道在邊防的重要性及軍糧調度等問題。吳承翰《五到八世紀財政物流的形成—以軍糧調度為線索》認為總管區內軍糧調度可能形成相對獨立的運作區域,軍糧調度以州為單位,惜未釐清總管與行軍總管的分別,實因未有行軍制度概念5而大陸碩士論文較多針對西川研究,如張熊《唐代西川鎮研究》、向楠《唐代劍南西川節度使的政治地理研究》、呂亮彎《唐代西川政治經濟論述》等。上述惜未論及唐代皇帝對蜀道修築、中央與地方政區的軍事部署,各級官員的統轄與調配,如何奠定蜀道的交通運輸命脈。
本文探討長安與蜀地間,蜀道沿線的傳驛制度結合成綿密的交通運輸網絡,牽涉國家統治運作的環節,扮演上傳下達的樞紐系統。希冀在學界研究基礎上,從蜀道的交通運輸與傳驛制度等面向著手,進一步論述唐代巴蜀驛道在交通運輸中,維繫政權運行的關鍵命脈及其重要的價值地位。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唐朝皇帝入蜀事件研究:兼論蜀道交通的圖書 |
 |
唐朝皇帝入蜀事件研究:兼論蜀道交通 作者:古怡青 出版社: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9-07-25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27 |
中文書 |
$ 428 |
社會人文 |
$ 428 |
中國歷史 |
$ 428 |
科學科普 |
$ 450 |
文史哲學群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唐朝皇帝入蜀事件研究:兼論蜀道交通
唐朝皇帝走不同的陸路或水路的入蜀路線,實具有不同的政治、軍事或經濟考量。從唐朝三位皇帝四次入蜀,所選的蜀道路線,反映出一次比一次驚險與狼狽,中央政府的控制力越來越衰弱。唐朝皇帝因關中事變,四次仰賴蜀道往漢中或成都逃難,最後都能安然返回首都,唐朝遂能維持而不亡,可知「蜀道」是延續唐朝政權的重要傳驛交通路線,唐朝政權興衰與「蜀道」密切相關。
安史之亂後,唐朝皇帝透過有效掌管西北地區的監牧制度,運用西南巴蜀地區在經濟軍事上的優勢,成功以蜀道作為交通運輸的逃難路線,使得唐朝政權得以度過危局。安史之亂後,唐朝國祚仍能延長一百多年,除因社會力仍可支撐外,當與唐朝能夠掌控西北的監牧與西南巴蜀的後方補給,具有莫大的關係。唐僖宗入蜀奔逃,以及黃巢之亂,唐朝已無力挽回危局,因而走向滅亡。
作者簡介:
古怡青
學歷: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
現職:淡江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經歷:國立臺灣大學共同必修「歷史領域」兼任講師
輔仁大學全人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明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著作:《唐代府兵制度興衰研究─從衛士負擔談起》
論文:<從差役看唐朝流刑的配送與執行>
<唐前期西北的交通運輸─以西州為中心>
<唐前期馬政的管理機構─以西州為中心>
<隋代禁衛大將軍的角色及其地位>
<論隋代東宮十率的角色及其地位>
章節試閱
第一章 緒論:唐朝對西南的經營—以蜀地為例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蜀地群山環繞,山川形勢險要,北有摩天嶺、米倉山、大巴山等秦巴山脈,西北接岷山,斜向東南伸展,形成蜀地和漢中盆地的天然界線高1,000∼3,000公尺。東部巫山,由長江橫斷產生三峽險峻地勢。南部有大婁山,西接雲貴高原北側邊緣,高1,000∼1,500公尺,山雖不高但坡度陡峭,為川南障壁。西部有大雪山和松潘高原,為青康藏高原東側,高2,000∼4,500公尺,地勢最高。蜀地四周為高山,中部為四川盆地地勢較低,此外,中部有河川由西向東依次為岷水(岷江)、涪水(涪江)、...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蜀地群山環繞,山川形勢險要,北有摩天嶺、米倉山、大巴山等秦巴山脈,西北接岷山,斜向東南伸展,形成蜀地和漢中盆地的天然界線高1,000∼3,000公尺。東部巫山,由長江橫斷產生三峽險峻地勢。南部有大婁山,西接雲貴高原北側邊緣,高1,000∼1,500公尺,山雖不高但坡度陡峭,為川南障壁。西部有大雪山和松潘高原,為青康藏高原東側,高2,000∼4,500公尺,地勢最高。蜀地四周為高山,中部為四川盆地地勢較低,此外,中部有河川由西向東依次為岷水(岷江)、涪水(涪江)、...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歷史是由時間、空間和人類三大要素構成,「區域研究」是歷史研究的一環,有助於理解歷史的空間性。「區域研究」橫跨政治、社會、經濟、宗教、文化等各領域,在時間縱軸與空間橫軸的座標中,對不同地區進行深入研究。「區域研究」有別於地方史關注地方的特殊性,可反映多層次、較完整的歷史,拓展研究的視
野。
而「區域研究」中有關「自然區域」和「行政區域」兩者互相關係的研究,是目前尚待開拓的課題。「自然區域」牽涉到地理環境,由地貌、氣候、水文、土壤和生活於其中的動植物等因素所組成複雜的關係。「行政區域」是在...
野。
而「區域研究」中有關「自然區域」和「行政區域」兩者互相關係的研究,是目前尚待開拓的課題。「自然區域」牽涉到地理環境,由地貌、氣候、水文、土壤和生活於其中的動植物等因素所組成複雜的關係。「行政區域」是在...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高序
謝誌
導言
第一章 緒論:唐朝對西南的經營—以蜀地為例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第二節 蜀地發展概況
第三節 西南的經濟開發
第四節 蜀地的軍事建設
小結 98
第二章 唐玄宗入蜀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第二節 玄宗入蜀避難時期
第三節 玄宗入蜀的去程
第四節 玄宗返京的回程
小結
第三章 唐德宗南奔漢中
第一節 德宗南奔漢中的去程
第二節 德宗返京的回程
第三節 德宗出行途中糧食供應
小結
目錄
第四章 唐僖宗第一次入蜀
第一節 僖宗第一次入蜀避難時期
第二節 僖宗入蜀的去程...
謝誌
導言
第一章 緒論:唐朝對西南的經營—以蜀地為例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第二節 蜀地發展概況
第三節 西南的經濟開發
第四節 蜀地的軍事建設
小結 98
第二章 唐玄宗入蜀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第二節 玄宗入蜀避難時期
第三節 玄宗入蜀的去程
第四節 玄宗返京的回程
小結
第三章 唐德宗南奔漢中
第一節 德宗南奔漢中的去程
第二節 德宗返京的回程
第三節 德宗出行途中糧食供應
小結
目錄
第四章 唐僖宗第一次入蜀
第一節 僖宗第一次入蜀避難時期
第二節 僖宗入蜀的去程...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