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言
1960年代我正在在撰寫《實踐與行動》(Praxis and Action)一書 時,就深深感覺到有些新思潮正在蘊釀—學術思想的思考模式、強調 重點以及關注對象都逐漸在改變。儘管當代的各種思想取向性格迥異, 而且其間缺乏有效的溝通,但隱約感覺到有些基本主題卻是自黑格爾以 降,在各種思想運動中不斷而且必然出現的。這些思潮都將焦點放在實 踐和行動的核心概念上,以期對於人類處境獲致深刻的理解。於是我開 始檢視實踐和行動的觀念在當代四種思潮—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 實效主義以及分析哲學—中的重要性。不過當時我只有釐清這幾種探 究途徑對於理解人類活動的貢獻而已,而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在總結該項 研究時,宣稱那只是一個開端而已。
當我完成該書手稿時,一場新的論戰正在進行,我在書中所探討 的許多議題,也在這場論戰中,以各種嶄新且無法逆料的形式出現。 1960年代社會政治的騷亂與抗議,所導致的一個後果就是社會科學的 基礎受到一連串抨擊及澈底批判。正當“意識形態的終結”在美國被叫 得震天價響時—當時主流社會科學家都懷著一種自信,認為他們的學 科終究可以建立在穩固的經驗基礎之上了,因而知識的穩定成長乃指日 可待—於是,一場如火如荼的論戰爆發了。
有些學者倡言社會科學的基礎本身就是脆弱的;常常我們以為是客 觀的、科學的知識,其實只不過是一種用來維護現狀的意識形態的偽裝 形式而已;社會科學最顯著的特徵不在於其闡明既存社會政治實在的能 力,而在於它們對現實情況不能提供任何批判性的觀點;以及它們對於 已滲透到人類生活所有層面的社會技術性的控制及操縱,所賦予的一種 虛假正當性。人們逐漸懷疑社會科學中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信念:亦即 相信一旦人類對於社會政治的運作,逐漸獲致系統性的、經驗性的理解 之後,自然會導致明智的決策,改善社會的不平等及不公道,解決社會問題。即使是價值中立及客觀經驗研究的堅決擁護者,也不得不承認他 們的學科有些問題,雖然這些問題經常被歸因於社會科學的年輕及不成熟。
局外人的批評或許可以當作無知、外行,而不加理會。最讓專家困 擾的還是局內人的批評,這些專家都認為社會科學已經獲得大眾承認, 成為真正的科學了。下一代的學者(擁有最精巧之數量化及經驗性的研 究技術)將可以全心全力推動社會科學的發展,使其成為更加成熟的科 學。但是有些局內人卻覺得極端不滿,大肆批評。世界各地學生運動的 領袖,有許多是學習社會科學的學生,他們對於社會的批評和對他們自 己學科的批評是息息相關的。
一些向來被認為是不相干的、垂死的、錯誤的、過時的探究途 徑,突然之間又充滿了活力。從語言哲學的概念分析所得到的一些觀 念,被用來批判社會科學的認識論基礎。科學史及科學哲學晚近的發 展,也威脅到社會科學家一向所抱持的有關科學及理論的看法。“硬心 腸”的經驗主義者一向所敵視的“軟心腸”的現象學及詮釋學也大受歡 迎。許多年輕思想家認為:這兩種探究途徑對於社會關係的理解,比起 以精密嚴謹自豪的經驗研究,更能提供真知灼見。已經被宣布死亡或被 確切駁倒的馬克思主義,又在國際上展現新的活力了。 閱讀社會科學過去十年來的相關文獻,我們獲得的第一印象是雜亂 無章。各種流派互相競逐,最後鹿死誰手尚未可知。關於何者是確定不 移的研究結果、何者為適當的研究程序、何者為重要的問題,或甚至何 者為研究社會政治最有前途的理論途徑等問題,都很少有甚至根本沒有 共識存在—除非是同一個學派的成員。某一個人一提出主張,另一人 就唱反調,互相辯駁,十分熱鬧,這些論調都競相搏取我們的注意。 1960年代如火如荼的論戰,絕不限於社會科學的地位這類狹隘的 學術議題。這些爭執的激烈,反映出人們關心一些較深刻、較廣泛的議 題。當人們感覺到他們正處於危機時期,當基礎似乎動搖了、正統崩潰 了,人們就會創立一個公共空間,在此有關人類處境的一些基本問題將 會重新提出來討論。本書主要的目標在於釐清、探索這些比較基本的議 題。我希望闡明,本來只是有關社會科學的爭論,只限於很小的學術圈 子,現在卻轉移到一些基本問題上,譬如人性、何者構成關於社會政治 知識、此種知識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方式,以及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係為何,以及應該如何等等。
許多社會科學家都相信,在比較平靜的70年代之中,60年代許多 混淆都將很快地過去。一些把社會視為一種複雜的動態均衡,而持“結 構功能模型”的人,或者有些認為新的、更進步的“一般系統”探究, 能使我們理解社會是如何運作的人,都把這段時期視為暫時的緊張壓 力,“調節機制”會再調整過來。他們說,讓這批胡鬧的批評者—這 些人會越來越少—叫囂說這些都是“布爾喬亞的意識形態”。假若我 們是負責、認真、誠實的研究者,則我們的主張必須中庸、實際,但信 念必須堅定,即堅信持續不斷的經驗研究將會增加我們對於社會的科學 理解。而最終這種研究所能獲致之有效的社會改革,將遠比革命者的叫 囂大得多了。
我不否認這是一種普遍的態度,特別是在社會科學家之間,也不否 認有重大的理由去支持這種態度。但我希望能夠去證明對於過去二十年 所發生之現象的這種解釋,基本上是一種曲解。對於過去所發生的,而 現在仍然繼續演變的現象,還有另外一種解釋。如果我們能透視浮辭泛 語—當我們能區辨何者為正確的批評,何者為錯誤的批評;何者為誇 張的批評,何者為中肯的批評時—我們就能覺察到一項正在發展中的 複雜論證的輪廓:一種正在浮現的新感性(new sensibility),目前雖 然還是很脆弱,但終將導致社會政治理論的重建。在此“論證”一詞具 有雙重的意義:在比較古老的用法中,論證指一段情節或一則故事。我 要展示此一情節的輪廓,把它帶到前臺來。而論證比較正規的用法則是 指一種理性論證。我們可以發覺最初似乎是相互獨立的探究路線,卻構 成了一項複雜論證的各個階段,而整個論證的力量比其中任何部分都要大得多了。一套恰當的、廣博的政治社會理論,必須同時是經驗性的、 詮釋性的,以及批判性的。這句話是什麼意思,為什麼必須如此,以及 經驗研究、詮釋以及批評如何辯證地結合在一起等問題,在此一情節開 展的歷程中將可以逐漸明朗。
在本書一開頭,我不打算把我所要證明的清楚論題提出來。我只 提出一個模糊的徵兆,暗示有關行動、社會及理論等的基本議題已經在 論戰之中被提出,而社會科學的批評者和辯護者都只是在各說各話。當 務之急乃重新檢討一個受到嚴厲批判的觀念:即相信社會科學應該是研 究社會現象的自然科學,和目前已確立的自然科學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差 別。某些批評者認為社會科學要模仿自然科學的想法十分膚淺,甚至很 愚蠢。有些批評者以為這個信念係基於一個簡單的或過分簡化的謬誤, 例如:社會科學都是天真素樸的實證主義,然而實證主義已經被駁倒 了,或至少已被澈底修正了,所以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駁斥基於此一錯 誤基礎的社會科學了。另外一些批評者則認為所有社會科學的核心在於 肯定事實與價值的僵硬二分法,而此種僵硬劃分是不可靠的,所以整個 社會科學就崩潰了。在社會科學某些批判性討論中,有一種隱藏的本質 主義。有些批評者—辯護者也是一樣—總以為社會科學運用自然科 學的程序來研究社會政治,只是牽涉到“一個大原則”。只要將此項大 原則加以揭露、駁斥,則整個社會科學就會土崩瓦解,而不必檢討各門 社會科學的煩瑣細節。
由於經常有人倡言社會科學是真正的實證科學,因此在一較精緻的 層次上,反對者就提出種種“不可能性”、“超驗性”或“概念性”的 論證,以證明要建構此種社會科學是不可能的—此種社會科學觀根本 就是概念上的混淆。我不相信任何“不可能性”的論證能夠成立。而且 由於哲學上的理由,我也不相信社會研究的認識論地位可能有這種確定 不移的、先驗的論證。1數百年來,對於社會研究的真正性質,雖然有 人一再地提出超驗性的或不可能性的論證,然而隨即又有反對的論證產 生,證明其無法成立—可見建立一門研究社會中之個人的實證性、經 驗性的自然科學,並沒有什麼不可超越的理論障礙存在。關於社會科學 的一些重要思考已經從這些討論當中浮現出來了,我並不是暗示把社會 研究當作不成熟的或年輕的自然科學的看法沒有問題。但是社會研究是 不是真正的科學,或社會生活的某些特徵是否無法用科學技術來研究等 問題的回答陳述,只是混淆(而非釐清)自然科學與社會研究的異同。
我首先要討論的是,主流社會科學家對於他們的學科的理解。我用主流社會科學家”是指那些認為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差異只是 程度問題的人。他們相信社會科學最大的成就乃寄託在模仿、修改自然 科學中已見成效的研究技術。我們不可把“主流社會科學”想像得比實 際更為一致、更為同質。因為其中不僅對自然科學的本質有重大歧見, 而且對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類似性也莫衷一是。然而,我覺得應 該重視實際在做研究且具有方法論自覺的社會科學家的意見,而不應完 全聽信社會科學哲學家(philosophers of social sciences)的說法。社會 科學哲學經常成為自然科學哲學的童養媳,只是探討一般認識論的爭議,而與社會學科的實際研究毫無關聯。
誠如我將在第一章闡明的,主流社會科學家相信他們的學科是一 門真正的自然科學,只是比較年輕而已。他們這個信念係肇因於他們對 於經驗理論之性質及重要性的理解,因而必須探討何謂經驗理論,經驗 理論與其他類型的理論活動(如所謂的規範理論)如何區別,為何他們 認為經驗理論對於社會科學的科學地位是如此重要。儘管主流社會科學 家之間有歧見,但是他們對於經驗理論之認識論特徵以及邏輯特徵的理 解,卻極為一致。不過對於何者能滿足或甚至接近該種理論的標準卻缺 乏理性共識。
對於社會科學的自然主義觀,只有在提出來加以探討之後,我們方 能評估其優劣、其所見、其所蔽。我將集中於當代直接向這種自然主義 式理解挑戰的思想取向*。每一種取向皆針對社會科學之基礎來批判, 每一種取向皆提出一種它認為更高明的社會政治探究途徑。
第一種思想取向係基於分析哲學,特別是維根斯坦和奧斯丁(J. L. Austin)所倡導的“語言轉向”。社會科學並非兩人的主要興趣,甚至 對於他們的研究與社會理論究竟有何關聯的問題,也不是他們的興趣所 在。但受兩人影響的許多思想家卻辯稱:以往社會科學家對於行動之性 質、描述及說明的主張,已經受到來自語言分析對於語言現象(特別是 行動的語言)的新見解的挑戰了。他們辯稱人類行動的描述和解釋要完 全遵循經驗性自然科學的規格,根本是錯誤的見解,而且是觀念上的混淆。
(* 譯註:即分析哲學、現象學及批判理論,分別在本書第二、三、四章中檢視。)
再者,最近分析哲學者的一個最重要、爭議最厲害、高潮迭起的 領域,就是科學史和科學哲學。在過去短短幾年之中,我們對“科學形 象”(image of science)的了解,已歷經了一次實質革命—至少和實 證主義者及邏輯經驗論者倡導的所謂正統見解比較起來確實如此。科學 史和科學哲學大部分著作是以自然科學為對象,但對社會科學顯然有重 大的影響。對社會科學作一種自然主義式的理解,有賴於對自然科學的 主要特徵(特別是理論所扮演的角色)有清楚的掌握。由於一種嶄新的 後經驗主義的科學觀,已經改變了我們對於自然科學的理解,從而影 響到對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異同的評判。對於最近之社會科學觀的 影響,也許還沒有一部作品比庫恩(Thomas Kuhn)的《科學革命的結 構》更大了,儘管他很少論及社會科學。他的影響很紛歧,也很奇怪。 或許問題出在一些政治及社會學者對庫恩著作的引用方式,他的著作甚 至被引用來支持互相衝突、矛盾的論調。
第二個向社會科學的自然主義觀挑戰的,來自於現象學。當代現象 學創始者胡塞爾(Edmund Husserl)的研究,雖然是從檢討邏輯及數學 開始的,但他把現象學方法應用到全部的人類經驗。在社會科學當中, 他對心理學的興趣最為直接。他有鑑於傳統心理學的缺失,因而要求把 心理學放在一個堅實的現象學基礎之上。在他的哲學發展中,互為主體 性(intersubjectivity)成為他的現象學的中心旨趣了。 但是真正去探求現象學對於社會研究的複雜含義的,則是受到胡 塞爾影響的一些學者。舒茲(Alfred Schutz)原來關注韋伯的理解社會 學,後來在胡塞爾以及柏格森(Bergson)的作品中,找到釐清社會科 學之現象學基礎所需要的思想工具。法國哲學家如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和呂格爾(Paul Ricoeur),從胡塞爾獲得一些觀念, 卻將注意力轉移到現象學如何能夠幫助我們理解社會實在。最近若干思 想家—最著名者莫過於義大利哲學家帕西(Enzo Paci)—嘗試綜 合胡塞爾和馬克思二者的思想。現象學原來對社會科學中經驗研究的影 響極微小,但在過去二十年間,對於經驗研究(特別是在社會學裡頭) 已經發生了重大影響。在美國和英國,現象學派的社會學者及庶民方法 學者(ethnomethodologists)逐漸形成一股潮流,他們經常從胡塞爾和 舒茲的思想中獲得靈感。
對於經驗理論及自然主義的社會科學觀的第三個挑戰,來自法蘭克 福學派的批判理論。“法蘭克福學派”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始聞名於世, 它包括一群與社會研究所有關的思想家,該研究所係於1923年在德國 法蘭克福成立。此一學派大部分成員,包括核心人物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阿多諾(Adorno)及馬庫色(Marcuse)等等,都受到 黑格爾、馬克思的強烈影響。在他們被逐出德國的時期—正值該所最 具創造力的時期—他們集體建立起社會批判理論的基礎。這種理論一 方面有別於布爾喬亞社會科學,另一方面也和教條式的史達林派馬克思 主義不同。社會研究所成立的宗旨之一乃從事經驗研究,在其避居美國 期間,係以權威人格及大眾社會的研究聞名於世。但是其成員對於英國 經驗主義以及美國實效主義的傳統深表懷疑而且極為輕視。 社會研究所於1950年遷回德國之後,最為傑出而且引起最多爭議 的思想家就是哈伯馬斯(Jurgen Habermas)。哈伯馬斯與老一輩的法 蘭克福理論家不同,他對社會科學、分析性的科學哲學、語言哲學以及 理論語言學等的晚近發展都有精深理解。哈伯馬斯重新檢視批判理論的 基礎,並尋求發展出一套廣博的社會理論,將經驗主義、現象學、詮釋 學以及馬克思-黑格爾等的研究主題,作一種辯證式的綜合。哈伯馬斯 和舒茲以及許多維根斯坦之後的分析哲學者一樣,對於主流社會科學公 然加以抨擊,對於我們理解社會實在之際所涉及的一些核心的認識論議 題,也加以探討。他已經著手從事在自然主義式的社會科學觀之外,另 闢蹊徑了。
因為上述三種取向都根源於哲學運動,這些哲學運動已經形塑了現 代意識,又因為三種取向都對於主導我們這個時代的科學主義,加以揭 露—一種可能導致理論上及實踐上不良後果的科學主義—因此我決 定詳加檢視。但是我並不想撰寫一部概論書,也不想站在不偏不倚的裁 判者立場,評判各方的優劣。我的主要目標是要發展出一個觀點,以便 綜合各種思想取向的精華,而棄其糟粕。
我越審視這堆龐雜材料,就發現有越多的材料可以安排到這裡面 來。於是乎,我們所面對的不再是一大堆從不相關的觀點擷取而來的要 點和論證。當我發現在這些材料中,儘管有緊張及衝突,卻遠比我當初 所預料的更為連貫時,我覺得大為興奮。
例如:在探討分析哲學者對於社會科學的一些批判時,我就問他們 對於社會知識有何不同的見解。這些批評者所津津樂道的一些主題,仍 是解釋社會學和現象學傳統的核心問題,因此我就很自然地探討現象學 對於社會實在的見解是否提供了一套比較清楚的闡釋。尤有進者,儘管 “硬心腸”的經驗主義者、分析哲學者與現象學者之間有重大歧見,但 他們其實共同秉持某些基本假定。他們倡導一種理論觀以及理論家的角 色,這種理論家近乎超然無私之觀察者的理想,去說明、理解、解釋, 甚至僅僅描述實際情況。但是這種理論和理論家的觀念,潛藏著困難和 未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及其枝節就是社會批判理論的源泉了。 在從事此一研究時,我想起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中的一段名 言。在《精神現象學》導言中,黑格爾描述科學與自然意識彼此最初如 何看待對方。從其中之一方的觀點來看,對方似乎都是顛倒錯亂的。黑 格爾警告我們:
因為要拋棄或駁斥一種不是真理的知識,說它是對事物的一種庸俗 見解,則不能全憑保證,保證自己是一種完全不同的知識,至於那 種庸俗見解在自己看來一文不值等等;也不能全憑揣想,說在這種 不真的知識本身存在著較佳知識的徵兆。如果只是作斷言,那麼科 學等於聲明它自己的價值及力量全在於它的存在,但不真的知識恰 恰也是訴諸它的存在,而斷言科學在它看來一文不值。一項枯燥貧 乏的保證,只是跟另一項保證具有同樣多的價值而已。2 我雖然摒棄黑格爾的主張,謂有或可能有一種最終的完善科學,但我們 可以從上述引文中獲得一項與本研究相關的、極為重要的教訓。在有 關社會科學之地位的爭論中,特別是基於不同哲學觀點者之間,我們似 乎遇到“一項枯燥貧乏的保證”,此保證的價值“和另一項保證的價值完全相等”。從爭論各方的言行來看,似乎自己的觀點才是唯一正確的 觀點,別的觀點都“不足道”。假若我們想要避免這種知識上的懷疑 主義,必須非常實在地檢視某一種主張—黑格爾稱之為某種意識形 式—設身處地來加以理解,發現它的弱點和內在矛盾,這樣就能引 導到更恰當、更廣博的理解。這就是黑格爾所謂從確信不疑到真理的辯 證運動。真理有待發現—黑格爾所探討的每一種意識形式中正確的成 分;任務是抽出這種“真理”,因而必須揭露這些意識形式之中錯誤的 及抽象的成分,然後超越這些意識形式,而達到一種更為恰當的理解。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社會政治理論的重構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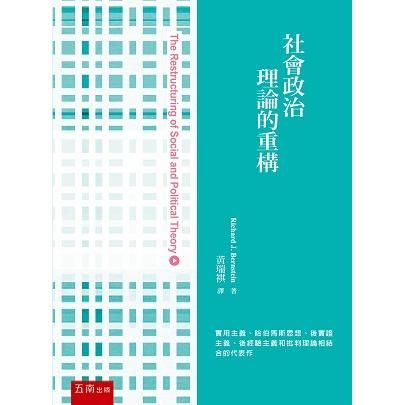 |
社會政治理論的重構 作者:Richard J. Bernstein 出版社:五南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16 |
社會人文 |
$ 360 |
Others |
$ 372 |
中文書 |
$ 372 |
政治 |
$ 380 |
政治學理論/經典著作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社會政治理論的重構
本書特色:實用主義、哈貝馬斯思想、後實證主義、後經驗主義和批判理論相結合的代表作。
本書對社會學理論、科學哲學、分析哲學、語言哲學、現象學、社會批判理論及哈伯馬斯的思想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對當代社會政治理論的主要流派中最重要、代表性的思想家進行了詳細而精當的分析。它所呈現的各理論流派並不是互不聯繫的,呈現的方式也不是平鋪直敘的個別介紹,而是排列成一個辯證的順序,有優劣、高下之分,其根據主要是「知識論一科學哲學一方法論」這一軸線。本書是實用主義、哈貝馬斯思想、後實證主義、後經驗主義和批判理論相結合的代表作。
作者簡介:
[美]R.伯恩斯坦Richard J. Bernstein
理查德•J.伯恩斯坦(1932—)1958年獲得耶魯大學博士學位,然後留校任教。曾為美國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哲學系講座教授。伯恩斯坦主要研究實用主義、社會政治哲學、批判理論等。著有《實踐與行動》(1971)、《超越客觀主義和相對主義》(1983)、《漢娜•阿倫特與猶太問題》。
譯者簡介:
黃瑞祺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博士,主要從事歐美社會政治理論、全球化、生態等研究。著有《批判社會學》、《社會理論與社會世界》、《馬克思主義與社會科學方法論集》、Recent Interpretations of Karl Marx’s Social Theory等;主編《當代社會學》、《溝通、批判和實踐──哈伯馬斯八十論集》、《再見福柯︰福柯晚期思想研究》等。
章節試閱
導 言
1960年代我正在在撰寫《實踐與行動》(Praxis and Action)一書 時,就深深感覺到有些新思潮正在蘊釀—學術思想的思考模式、強調 重點以及關注對象都逐漸在改變。儘管當代的各種思想取向性格迥異, 而且其間缺乏有效的溝通,但隱約感覺到有些基本主題卻是自黑格爾以 降,在各種思想運動中不斷而且必然出現的。這些思潮都將焦點放在實 踐和行動的核心概念上,以期對於人類處境獲致深刻的理解。於是我開 始檢視實踐和行動的觀念在當代四種思潮—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 實效主義以及分析哲學—中的重要性。不過當時我只有釐清這幾種...
1960年代我正在在撰寫《實踐與行動》(Praxis and Action)一書 時,就深深感覺到有些新思潮正在蘊釀—學術思想的思考模式、強調 重點以及關注對象都逐漸在改變。儘管當代的各種思想取向性格迥異, 而且其間缺乏有效的溝通,但隱約感覺到有些基本主題卻是自黑格爾以 降,在各種思想運動中不斷而且必然出現的。這些思潮都將焦點放在實 踐和行動的核心概念上,以期對於人類處境獲致深刻的理解。於是我開 始檢視實踐和行動的觀念在當代四種思潮—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 實效主義以及分析哲學—中的重要性。不過當時我只有釐清這幾種...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序言
《社會政治理論的重建》一書已出版了三十餘年,從那時起,在所有社會科學以及在我們對社會政治理論的理解中發生了劇烈變遷。不過,我仍然相信在這本書中所發展的論旨──一個適當的社會政治理論必須是經驗性的、解釋性的、批判性的──已經被證實了。這並不是三種不同類型的理論,而是社會政治理論的功能的三個面向。為了能領會我在這本書中所說的,我們需要重建其〔社會政治理論〕歷史脈絡與智識脈絡。二戰後社會科學有驚人成長──特別是美國的社會科學。許多重要社會科學家把社會科學看作是行為科學──人類行為的科學。他們的行...
《社會政治理論的重建》一書已出版了三十餘年,從那時起,在所有社會科學以及在我們對社會政治理論的理解中發生了劇烈變遷。不過,我仍然相信在這本書中所發展的論旨──一個適當的社會政治理論必須是經驗性的、解釋性的、批判性的──已經被證實了。這並不是三種不同類型的理論,而是社會政治理論的功能的三個面向。為了能領會我在這本書中所說的,我們需要重建其〔社會政治理論〕歷史脈絡與智識脈絡。二戰後社會科學有驚人成長──特別是美國的社會科學。許多重要社會科學家把社會科學看作是行為科學──人類行為的科學。他們的行...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序言
致謝
導言
第一章 經驗理論
第二章 語言、分析及理論
第三章 社會現象學
第四章 社會批判理論
結論:社會政治理論的重構
參考書目
譯後記
致謝
導言
第一章 經驗理論
第二章 語言、分析及理論
第三章 社會現象學
第四章 社會批判理論
結論:社會政治理論的重構
參考書目
譯後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