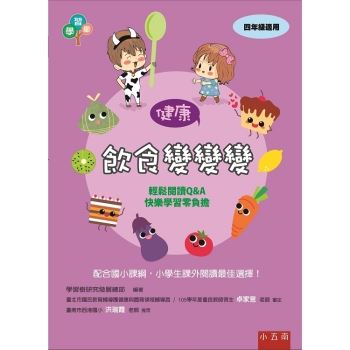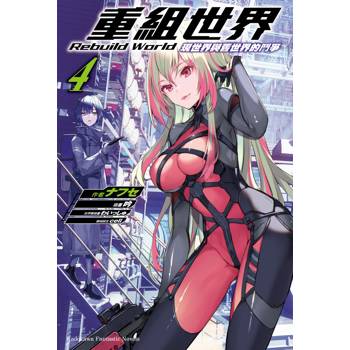今日的「政治」一詞,說是從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而來,一點也不為過!
本書將讓我們找到面對「政治」的新可能性,不能僅要求在民主生活中各種「權利」應獲得什麼保障,而是要從「義務」的觀點來想想我們如何可以貢獻於所處的政治共同體,因為亞里斯多德一直視政治是個人存有的不可缺部分,且是最重要的部分。
在本書中,亞里斯多德分析最佳政體所依據的核心觀念乃是「裨益」(good,本書譯為善)與「德行」(virtue)。什麼樣的生活可以為人帶來「裨益」,因而獲致幸福?而要什麼樣的「德行」才可以讓人獲致如此的「裨益」?「裨益」有三類:外在於人的;身體的;靈魂的。第一類例如財富;第二類如健康長壽等;而第三類則是亞里斯多德認為最重要、也是最高等級的「裨益」,那就是某種有益於靈魂、可讓靈魂狀態提升之物,例如德性(靈魂之滋養品)與智慧(使靈魂理性和諧)等。若以此觀點來看,對個人言最好的生活也就是對政治體最好的生活,反之亦然。然只有一種政治體制可以達成這個目的:那就是民治政治(democracy),在其中,因為公民們同時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因此每一個人都能獲致自由,發揮其能力,鍛鍊其智性與成就其德行,最後成為一個充分實現人之所以為人的潛能的人。
作者簡介:
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西元前384-西元前322年)
希臘哲學家和科學家。其父曾是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大帝的祖父的御醫,他是柏拉圖的學生,後來在柏拉圖阿卡德摩學園任教二十年,於柏拉圖去世後離開雅典。西元前342年返回馬其頓擔任年僅13歲的亞歷山大的老師,影響了亞歷山大大帝對科學和知識的重視。西元前335年亞歷山大去世後,於雅典開辦自己的萊西姆學院,於此期間,他邊講課邊撰寫了多部哲學著作。由於亞氏與其弟子常漫步於庭院有頂蓋的走廊討論問題,因此有「逍遙學派」之稱。其作品多以講課的筆記為基礎,甚至是他學生的課堂筆記。西元前342年,雅典人開始反對馬其頓的統治,由於他和亞歷山大的關係,被指控不敬神而不得不至卡爾基避難,一年之後病逝。他的哲學開創了之後的科學方法,也是集大成者,被稱為古代最博學的人,對後來的西方科學和哲學的影響十分巨大。著作豐富,知名作品有:《工具篇》、《論靈魂》、《物理學》、《形上學》、《尼科馬可倫理學》、《政治學》和《修辭學》等。
譯者簡介:
蕭育和
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人員,研究專長為當代政治哲學及當代歐陸政治思想。
章節試閱
卷一:家計的理論
第一章(1252a1-1252a23)
城邦(polis)是共同體(community)的一種。凡人類所做所為,其目的都不外乎為了某種善,共同體組成的目的也是為某種善。如果所有共同體的目的,都在於某種善,那麼就可以斷定,包羅囊括一切其他共同體的城邦(亦可稱之為政治共同體),是所有共同體中最高一級,跟其他的共同體比起來,它的權威最高,所求之善,也是最高。
有人認為,治邦者(statesman)、君王、家主、奴隸主,其實是同一件事。所不同者,只在於臣服的人數多寡而已。例如,奴隸主統治寥寥幾個奴隸;若受治的人再多一些,就成了家計(household)的經營管理者;受治的人再更多一些,就成了治邦者或君王,彷彿大的家計跟小的城邦之間沒有差別。而治邦者跟君王的差別,又只在於一人之治則為君王,而依政治性的法則,由公民輪流統治,既治人又受治於人,則為治邦者。
如果依據過去一直以來指導我們的方法,對這個問題稍作考慮,就很清楚:上述的說法是有謬誤的。政治學跟其他學科分支一樣,其方法都是把合成物拆解成再無法拆解的元素,也就是全體中最小的部分。是以,我們必須要先看的是城邦組成的各種元素。為此,我們得先看看,那些不同的統治形式之間,相異何在?以及這樣做是否對這整體論題,能夠有體系性的立論。
第二章(1252a24-1253a38)
無論研究國家或其他問題,如果先考察其開端與演進,就能有清楚的認識。首先,必然有一種缺一不可的結合,這也就是男女之間的結合。有了這樣的結合,種族就可以連綿不斷地延續下去。這樣的結果,並非刻意的算計或選擇,其實不過跟其他動植物的自然動機類似,也就是留下自己的血脈而已。接著,必然有一種雙方為求彼此保全,統治者與受治者自然的結合。有洞燭機先心智能力的,自然而然就是主人;而為此遠見而以身體出力的,則成了受治的一方,自然而然也就成了奴隸。因此,可以說主人與奴隸之間有著同樣的利益。可是,女性與奴隸自然大有分別,不能併為一談。自然不像德爾菲的鐵匠,會設計出多功能的刀(Delphian knife) ,一定讓所有造物都各有其用途,而只為單一用途而非多重用途所造的器具,才為上乘的器具。然而,在蠻族中,對女性與奴隸是沒有區別的,因為他們之間並無自然而生的統治者:可以說,他們是男女皆奴的奴隸社會,這是為什麼會有詩人這麼說:
當由希臘人來統治蠻族 。
彷彿蠻人與奴隸天生沒有差別一般。從男女與主奴這兩種基本結合中,首先出現的是家計,赫西俄德(Hesiod)有云:
首為家屋、為妻孥、為耕牛。
這樣的說法確實精確。耕牛可以說就是貧民的奴隸。而家計正是為了滿足日常生活的需求,自然而生。查隆達斯(Charondas)將家計成員稱之為「一起吃飯的伴侶」;或者,克里特島的埃庇米尼得斯(Epimenides)也有「一起圍坐在爐火邊的伴侶」這樣頗為切實的比喻。當若干家計單位,為了日常所需之供給之外的目的而結合起來時,就成了聚落(village)。最自然的聚落,其實不過就是同一個家計單位開枝散葉,所以,有些人稱聚落成員是「同乳所哺」「子息綿延」。這是為什麼希臘諸邦,在彼此結合之前,都跟現今的蠻族一樣,由君王君臨統治。所有的家計單位都由年長者統治,從而,在家計組成的聚落中,王權的治理形式就依同樣的血脈原則而盛行。正如荷馬(Homer)所說:
人皆為其妻孥,立下律法 。
他們在遠古時期散居各地。這也是為什麼人們會說諸神中有王,因為在遠古時期,他們或者自己就是王,或者被王所治。他們用自己的生活樣態,來想像諸神及其生活樣態。而當聚落日多,結合在單一個完整的共同體,其規模大到足以或近乎自足時,始於生活所必需目的,繼之為了更好的良善生活,城邦於是就出現了。
城邦一旦肇建成立,就無法再加以廢除。如果說過去的共同體形式,都是出於自然而成,那麼城邦的肇建,必然也出於自然,可以說城邦是所有共同體的終點。我們說一個事物的自然本質,所說的就是它的發展終點。當事物完全發展而達到某個狀態,我們就可以說這就是它的自然本質。無論是人、馬、或者家計單位都是一樣。所以很清楚,城邦的肇建,乃是出於自然。除此之外,任何一個事物最初的原因與最終的結果,都是最為完善的,所以,能夠自給自足者,就既是最終點,也是最為完善。
因此可以證明,城邦的肇建,是自然的產物;而人也是本於自然,而成政治動物(political animal)。要是有出於自然本性而非偶然遭遇,而不需要城邦者,要麼不是惡徒,要麼就是超人。也就是詩人荷馬(Homer)痛斥為「無部落之屬,無律法所規,又無家可歸」的人。這樣的人生性嗜血,天地不容,說是棋盤上的孤子,一點也不為過。
顯而易見,跟蜂群或其他群居動物比起來,人更是一種政治動物。人是唯一一種天賦具有言說(speech)能力的動物,自然造物的事功,不會虛擲徒勞。我們用聲音,來表達痛苦與歡愉,這樣的本能,其他動物一樣也有,可是其知覺程度,只能達於感受與傳達苦樂。但是,言說的能力,是用以闡明利與弊,因此而能有是非曲直之分(the just and the unjust)。人的獨特之處,在於只有他們才有類似善與惡,是非曲直諸如此類的認識。具有這樣感知能力的造物,就創造出了家計與城邦。
城邦的肇建,就其本性(by nature)是先於家計與個體。他們之間的關係,就像是人整副身體與肢體之間的關係。如果身體毀損,那麼手足就無法存在。除非我們搬弄文字遊戲說這是「石頭手」,否則一旦身體毀損,手足肢體也難說完好。世上一切事物都是以其功能與能力來加以界定,如果手足失去了它固有的特質,就無法再將之視為手足,除非指的是另一個同音但意思完全不同的東西。
城邦是自然的造物,而且先於個體。證據是,一個人離群索居,就無法自給自足,這就像是人手足肢體與整副身體之間的關係一樣。如果有人無法在共同體中生存,或者自認可以自給自足毋須共同體,就不會是城邦的一分子,這樣的人如果不是野獸,不然就是神靈。自然賦予人結成共同體的本能,因此,說肇建城邦的人,功績無可限量,一點也不為過。人如果能達到完善的境地,就可以說是動物中最為優良者,但若是除去律法與正義(justice),則反成最為惡劣者。畢竟,配有武裝的不義,更為危險。而人天生俱有為智識慎慮與德行優異的武裝,可以為了最惡劣的目的,而加以運用。這是為什麼,人一旦失德,就會變成充滿無盡慾望與貪婪,最為邪惡殘暴的造物。正義是城邦中人際之間的紐帶,用以斷定是非曲直,而這就是政治共同體秩序的原則。
第三章(1253b1-1253b22)
由於城邦是由家計單位組成,所以在討論城邦之前,最好先討論家計管理。家計管理的各個部分,相應於組成家計的個人。一個完整的家計單位,包含了奴隸與自由人。我們對一切事物的研究,應該要從最簡單的元素開始,這是基本常識。而家計單位最首要與最簡單的部分是主奴關係、配偶關係(人與其妻的結合尚未有適切命名),以及家父長與子嗣的關係(也同樣未有適切命名)。而家計單位尚有另一元素,也就是所謂「理財致富的技藝」(art of getting wealth),有些人認為,此一技藝與家計管理並無分別;另一些人則認為,此為家計管理的主要部分。理財致富的技藝其本質為何,我們也必須加以討論。
首先要討論的是主奴關係。既要看其對實際生活的需求,也要對比當下的現狀,看看能否得出更為完備的理論。有論者認為,主人的統治是一門學問,所以一個家計單位的管理,對奴隸的駕馭,乃至於政治與君王的統治,都是同一回事,就像我們開頭所說的那樣。但也有人認定,主人對奴隸的統治違背自然,因此自由人與奴隸之別,不過約定成俗(by convention),而非自然所成,所以必定與自然扞格,從而並非正義,這是另一種說法。
第四章(1253b23-1254a16)
家產(peoperty)是家計的一部分,所以獲取財產的技藝,也是家計經營技藝的一部分。要是生活所必需品不能俱全,則無法享受舒適的生活,甚至於無以維生。技藝一定有一個確切的範圍,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家計管理也是如此。在各式各樣的工具中,可以分成兩類:一是具有生命者;另一則是不具生命者。以航行的技藝來說,船舵是無生命的工具,而瞭望者,則是有生命的工具。在一切的技藝中,可供人役使者(servant),都可以說是工具之一。所有物(possession)是人維持生活的工具,而在家計的經營管理上,奴隸是有生命的所有物,家產就是這些大量工具的集成,而可供人役使者,就是使用工具的工具。如果所有工具,都像是戴達洛斯(Daedalus)所雕的塑像,或者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的三足寶座那樣,能有預知人意,自動完成工作的能力,就像詩人所說:自行參與諸神的集會。要是織梭能自動織布,琴弦能自己彈動,毋須人動手,那麼,匠人就不需可供役使者,主人也同樣不需奴隸。
而通常稱之為工具者,大概指為生產製作(production; poiesis)的工具而言,而家產乃是為活動實踐(action; praxis)的工具。以織梭為例,其功用,不只是供人運用而已,也有賴它製成其他物品,這就是生產製作的工具。而至於衣服或床第,則除了供人使用以外,別無其他產出,而這也就是活動實踐的工具。接著,雖然生產製作與活動實踐,都有賴於工具,但它們的作用方式有所區別,所以其所用的工具,也必然有所區別。人的生活,是關於活動實踐的事,而不是生產製作的事,所以奴隸是在活動實踐場域中供役使者。
此外,當我們論及「所有物」的界定時,就好像論及某個物的部分,這個部分所指的不是只有這個部分而已,也有它完全屬於另一個某物的意義。所以當說到主人,他不附屬於奴隸,單純就只是奴隸的主人;但說到奴隸,則不只是主人的奴隸,而是還有完全附屬於主人的意義在其中。據此,我們就可以理解奴隸的本質與作用。如果一個人自然而然附屬於他人,就自然而然地成為奴隸。作為奴隸,也就是作為所有物,也就可以界定成能夠與其所有者分離,成為活動實踐所用的工具。
卷一:家計的理論
第一章(1252a1-1252a23)
城邦(polis)是共同體(community)的一種。凡人類所做所為,其目的都不外乎為了某種善,共同體組成的目的也是為某種善。如果所有共同體的目的,都在於某種善,那麼就可以斷定,包羅囊括一切其他共同體的城邦(亦可稱之為政治共同體),是所有共同體中最高一級,跟其他的共同體比起來,它的權威最高,所求之善,也是最高。
有人認為,治邦者(statesman)、君王、家主、奴隸主,其實是同一件事。所不同者,只在於臣服的人數多寡而已。例如,奴隸主統治寥寥幾個奴隸;若受治的人再多一些,就...
推薦序
人類文明中出現政治與權力關係該有幾萬年了吧?而開始使用文字不過幾千年,歷史上第一本以政治為名的書出現大概就是這本書了(約西元前四世紀)。不過應該這樣說,在西方「政治」(politics)這個字本來就是從本書的書名(politika)而來──它意指「城邦的事務」(affairs of the Polis),而不是西方文化早已先有我們今日所認知的「政治學」這個詞意後,本書乃以之為名。
既然對希臘人言,「政治」之本意為「城邦事務之管理」,我們在讀此書時首先要有的觀念就是:他們所謂的「政治」是在「熟人」(或即使沒那麼熟,也是今日我們所稱的「鄉親」)之間,大家彼此有明顯的「歸屬感」與「地域共同感」。在今日廣土眾民的民族國家中生活的我們,很難體會「人際間的熟稔關係」會是聚首會商公共事務的先決條件。也就是說,從「歸屬感」而來的「參與感」是政治的起始,也是終點──政治始於城邦的共同生活所需,終於城邦的幸福繁榮。每個人離不開城邦,每個人因此離不開「政治」(城邦公共事務)。
很顯然地,這並不是我們今日的生活方式與對政治的看法。所以,我們可從這本書中學到什麼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找到面對「政治」的新可能性──重新地思考人與「政治」的關係,因為亞里斯多德一直視政治是個人存有的不可缺部分,且是最重要的部分。也許現代人能從這本書中得到的「震撼」,就是民主不能只從「權利」的角度思考:我們不能僅要求在民主生活中各種「權利」應獲得什麼保障,而是要從「義務」的觀點來想想我們如何可以貢獻於所處的政治共同體。後者即是亞里斯多德所強調的「政治人」、「人是營政治生活的動物」(homo politicus)之概念,它意指我們要帶著人的本性中的「主體性」與「歸屬感」來參與政治生活,而政治生活最終也讓我們天性圓滿、實現生命意義。也正是這樣的態度,可用來矯正今日自由主義民主之下普遍產生的兩大弊病:「自私」與「政治冷漠」。(多數學者都同意,我們讀亞里斯多德《政治學》時要一併讀其《尼柯馬基倫理學》,因這兩本書合起來可構成他較完整的公民素養與公共生活觀。)
這本書在歷史上一直享盛名嗎?並不是的,它曾經與古典時期其他若干希臘羅馬經典一般,在歐洲消失近千年,其觀念也不為中世紀的人所認同。這當然是由於書中的人本思想與基督教不合,遭到排擠之故。這本書是亞里斯多德親手撰著發表的嗎?不是,據信這乃是他授課演講時所準備的筆記,身後由他人編輯遺稿而成,並編排上書名,且書中各卷次序未必符合亞氏原先的講授次序。再者,現在這本書與成書時的版本一樣嗎?可能已有差距!當時以古典希臘文手抄傳寫,但是傳寫過程中必有脫漏失真處,且原稿已不復存,歐洲所僅存的希臘文版本都屬之後的傳抄,且可能互相有異;中世紀時本書大抵已在歐洲失傳,流落到伊斯蘭世界以阿拉伯文保存,後再傳回歐洲(十二世紀時有所謂的亞里斯多德思想復興)譯回為拉丁文版本,這個來源對現今我們考據希臘文正確版本當然也有影響。但無論如何,亞氏的重要政治觀念的確是保存下來了。
亞氏思想重現歐洲後,當時的人如何地接納呢?基本上有兩種不同態度,一是完全採納他的「異教」(pagan)世界觀而將理性分別於信仰之外,這是以馬希留(Marsilius of Padua)的「繼受伊斯蘭式詮釋」(Latin Averroism)為代表,而漸漸演變為意大利文藝復興的公民人本主義(civic humanism)與馬基維利主義,它們對不良政體的革命與打造重建,深受亞氏《政治學》之啟發。另一則是教會的經院哲學家們以想要調和信仰與理性的立場閱讀,其中又以聖湯馬斯的「雙重秩序」(duplex ordo)觀點為代表,它著重於重拾「政治場域」(the realm of the political)的重要性。但無論如何,在近代兩者已合流,鎔鑄成為歐洲各個國家的民族共和主義思潮:或在「天啟」與「公民興國」之間穿梭,或猶如光譜般因時因地而各有不同著重。美利堅合眾國的建立與法國大革命,都是璀璨的例子。
在本書中,亞里斯多德分析最佳政體所依據的核心觀念乃是「裨益」(good,本書譯為善)與「德行」(virtue)。什麼樣的生活可以為人帶來「裨益」,因而獲致幸福?而要什麼樣的「德行」才可以讓人獲致如此的「裨益」?「裨益」有三類:外在於人的;身體的;靈魂的。第一類例如財富;第二類如健康長壽等;而第三類則是亞里斯多德認為最重要、也是最高等級的「裨益」,那就是某種有益於靈魂、可讓靈魂狀態提升之物,例如德性(靈魂之滋養品)與智慧(使靈魂理性和諧)等。若以此觀點來看,對個人言最好的生活也就是對政治體最好的生活,反之亦然。然只有一種政治體制可以達成這個目的:那就是民治政治(democracy),在其中,因為公民們同時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因此每一個人都能獲致自由,發揮其能力,鍛鍊其智性與成就其德行,最後成為一個充分實現人之所以為人的潛能的人。
亞里斯多德《政治學》共分八卷,其實可以分開獨立來讀,理由已如上述:這八卷乃是後人就遺稿撮集而成,編排之次序也不盡理想。其中卷二、卷三與卷七最具理論意涵。卷二透過「回顧理想城邦」來對已出現的理論或現實做評論,包括對他老師柏拉圖設計的不同模式城邦,與諸如斯巴達、克里特與迦太基等實際政體的討論。卷三則是對我們今日奉為圭臬的(雅典式)城邦政治之基本概念的鋪陳解析,此部分對後世政治理論影響最大。卷七則是對於理想城邦的政治生活做出宏觀、形而上精神性的探析與形而下實際建制上的擘畫。
但是在卷一進入有關「家庭」、「家計單位」(household)的討論前,卻出現了瞭解亞氏所有對於政治的思考最緊要關鍵的一些話語:
城邦是「共同體」(koinonia,人類社群之意)的一種。凡人類
所作所為,其目的都不外乎為了某種「善」(good,或可譯為裨益),
則共同體組成的目的也是為某種善。如果所有共同體的目的,都在
於某種善,那麼就可以斷定,包羅囊括一切其它共同體的城邦
(亦可稱之為政治共同體),是所有共同體中最高一級,跟其它
的共同體比起來,它的權威最高,所求之善,也是最高。
此段話已標舉出政治學的標的與重要性。這個經典的定義足以讓他成為「政治學之父」。他繼而解釋為什麼城邦會出現?「當聚落日多,結合在單一個完整的共同體,其規模大到足以或近乎自足時,始於生活所必需目的,繼之為了更好的良善生活,城邦於是就出現了。」從這之中,我們知道他認為城邦乃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共同體(希臘人視之如「小宇宙」(micro-cosmos)),物質上可滿足經濟生活所需,精神上則可帶來良善生活之可能。這也就符合前述所謂城邦為「最高之善」。由於人有趨向於善的本能,所以城邦的肇建,「乃是出於自然」。城邦因於人本性之所趨,這是亞氏政治思想的起點。人不但有這種自然的本能會去肇建城邦,也是在自然界生物中獨有一種能力,可以經營城邦生活者,這就是亞氏那句千古名言「人是營政治生活的動物」之來由。
人有什麼樣異於其他動物的能力可行政治生活?那就是「理性」,其見諸於「思辨」,且表達於「言說」。「言說的能力,是用以闡明利與弊,因此而能有是非曲直之分(the just and the unjust)。人的獨特之處,在於只有他們才有類似善與惡,是非曲直等諸如此類的認識。具有這樣感知能力的造物,就創造出了家計與城邦。」亞氏對人的本質有一種看法,近似於歌德在《浮士德》所言,就是人乃是能力極高、令神明也讚嘆的一種生物,但可以大好或大壞:「人如果能達到完善的境地,就可以說是動物中最為優良者,但是若除去律法與正義,則反成為最惡劣者。……人一旦失德,就會變成充滿無盡慾望與貪婪,是最為邪惡殘暴的造物。」由此可知良好政治的重要,城邦的存在就是為了讓人「成德」,維繫群體生活的「正義」,讓人的一生富於意義。對亞氏而言,城邦是「自然的」,「先於個體而存在的」,人類的起點(生於斯、長於斯)與終點(發揮潛能、完成人生意義)。
然而歸結言之,我們今日生活在濃厚自由主義氣息之下,未必願意以如此立場看待政治生活與國家,或許也會深深覺得,以亞里斯多德的城邦政治思想所引領建構的古典共和主義太過於高調令人窒息。但是這種對人的生命意義必然「寄託於公領域」之看法,的確讓我們這些「自由主義時代之子民」耳目一新,腦中不時會浮現古典「政治人」的影像。也許在潛移默化中,我們仍會不自覺地在某些面向上(不只是政治)朝向心中的城邦緩緩前進。
人類文明中出現政治與權力關係該有幾萬年了吧?而開始使用文字不過幾千年,歷史上第一本以政治為名的書出現大概就是這本書了(約西元前四世紀)。不過應該這樣說,在西方「政治」(politics)這個字本來就是從本書的書名(politika)而來──它意指「城邦的事務」(affairs of the Polis),而不是西方文化早已先有我們今日所認知的「政治學」這個詞意後,本書乃以之為名。
既然對希臘人言,「政治」之本意為「城邦事務之管理」,我們在讀此書時首先要有的觀念就是:他們所謂的「政治」是在「熟人」(或即使沒那麼熟,也是今日我們所稱的...
目錄
卷一:家計的理論
卷二:回顧理想城邦
卷三:邦民身分與城邦體制
卷四:現行的政治體制及其各種形式
卷五:政治體制變革與動亂的緣由
卷六:建構穩定民治與寡頭政體的方法
卷七:政治的理念與教化原則
卷八:青少年的教養
卷一:家計的理論
卷二:回顧理想城邦
卷三:邦民身分與城邦體制
卷四:現行的政治體制及其各種形式
卷五:政治體制變革與動亂的緣由
卷六:建構穩定民治與寡頭政體的方法
卷七:政治的理念與教化原則
卷八:青少年的教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