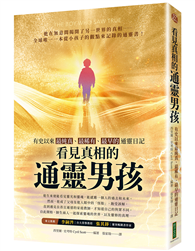流放整整十一載,皇長子賀泰佝僂了腰背,
如百姓一般低首編蓆,節衣縮食。
他性格軟弱,幸好幾個兒子撐起一家。
見過三郎賀融的,每個人都覺得可惜。
幼年落馬,害死嫡出弟弟也落下足疾,致生母為父親所惡;
隔一年謀逆案發,母親又遭陷入罪慘被賜死,一家貶庶流放。
房州人盡皆知,為生命安全計,遠離賀家為上,
不然哪天坐連遭禍,恐怕就連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苦難使一家團結、兄弟和樂,
失去過,方懂珍惜得來不易。
賀融一計成功,天子終於憶起他們,
京城來使卻同時帶來了和親的陰霾——
本書特色
夢溪石,《成化十四年》作者最新歷史權謀作品,精彩呈現!
苦難使一家團結,失去過方懂珍惜。
即使貶落塵泥,困不住龍游九天!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麟趾 一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10 |
二手中文書 |
$ 237 |
大眾文學 |
$ 237 |
古代小說 |
$ 255 |
古代小說 |
$ 270 |
中文書 |
$ 270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圖書名稱:麟趾 一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