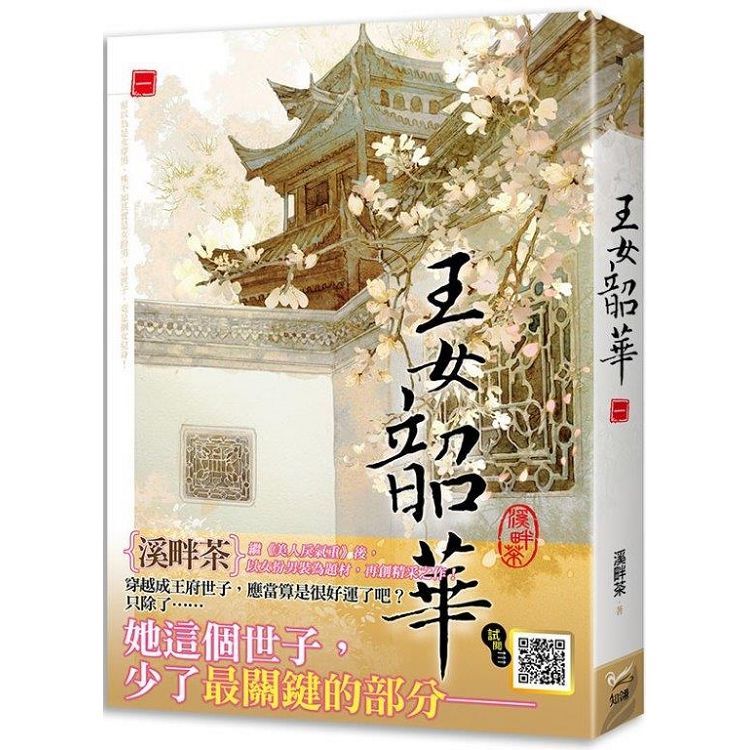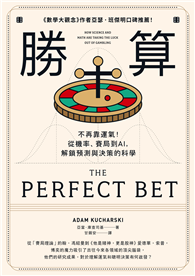第一章
傍晚。
暮色裡,一片片飛雪打著旋兒,輕盈揚落下來,地上,樹上,行人的頭上,或茅草或青瓦或琉璃堆砌的屋頂上,很快皆染上了一層濕意,那濕意層層累積,緩緩覆白。
廣闊莊穆的滇寧王府靜靜地矗立在這片冬日的初雪中,門楣前懸掛的宮燈在雪花飛融中散發著瑩瑩溫暖的光,朱紅獸頭正門緊閉,只有西側角門還半開著,青衣小帽的幾個門房小廝們縮在階邊角落裡,跺腳哈手地取暖。
天色已晚,又落了雪,這個時辰王府所占的長街前已無行人往來,靜謐中只見飄雪如絮。然而那西側角門並無關閉之意,小廝們也不進到裡面的倒座房小間去躲雪,似仍在等候著什麼。
萬物顏色漸改,又過一刻,終於有一行馬隊自長街盡頭而來,馬蹄聲得得敲在鋪設齊整的青石板道上,小廝們聽得動靜,一下子像都拋卻了寒冷,忙紛紛伸長脖子去望。
只見馬隊為首的是一匹通體雪白的駿馬,那馬和中原常見的高頭大馬不同,卻是矮墩墩的,但牠身姿健美流暢之勢並不遜色,而且踏步十分穩健,只是因那小短腿,對比之下腦袋就顯得大大的,迎面奔來時很有幾分憨態可掬之態,與馬身上駕馭的少年相映成趣。
這少年也是個矮短身材,看年紀不過十一二歲,裹著件朱紅氅衣,足蹬鹿皮小靴,生著一張圓乎乎的臉,因為風雪所侵,露出來的臉頰凍得紅通通的,眼睛也在飄雪裡瞇著,但仍看得出眉目明秀,肌膚底子白皙,有江南山水之清逸,與他身後那些紅銅色肌肉勃發的本地漢子們大為不同。
小廝們見到這隊人,還隔著老遠就忙都奔了出來,待頭前的少年馳到近前,馬速慢下來,立刻牽馬的牽馬,扶人的扶人,訓練有素又殷勤萬分,其實少年騎的馬乃是本地特產的滇馬,腿短而耐力長,以少年本人的身高也可以輕鬆躍下,但他很顯然是個脾氣不錯的人,由著小廝們獻了殷勤,再從腰間扯下一個荷包來,隨手丟出去,然後自己捂著冰涼的臉哈了口氣道:「我也不知多少,拿去分了罷,公平些,可不許再打起來啊,不然我可不敢賞你們了。」
扶著他的小廝年紀長些,看著像是個小頭目,忙笑成了一朵花,嘿嘿道:「那回那兩個小子不懂事,給世子爺添堵了,這得了賞多開心的事,偏給臉不要臉,硬鬧起來,如今已經不在門上了,我跟林二管家稟報了,發了他們去掃兩個月馬廄,長長記性!」
少年正是這一代滇寧王的長子沐元瑜,這點門房上小廝為打賞掐架的事當然不在他的心上,他不過是順口點一句,得了回話,也就隨意點點頭,抬步便往角門裡去了。
護衛他一起出門的隨從們跟在後面,進門後熟門熟路地往另一個方向散去。
那小廝則有眼色,把得的荷包先塞給了旁人,追上來,彎腰繼續陪著沐元瑜,一邊往裡走一邊道:「丁香姐姐在門房裡等著世子呢,您出門的時候這天看著好好的,下午了忽然陰下來落起雪來,不知您什麼時候能從武定回來,那邊能備上蓑衣不能——唉,看您這衣裳,指定是一路淋了回來。」
在這塊天高皇帝遠,上位者的權力很多時候可以代替律法的地界上,沐元瑜這樣脾性溫和的少主人很為罕見,所以連門房上的小廝們都敢多嘴跟他絮叨兩句,沐元瑜也習慣了,不多搭話,只是點個頭,表示有在聽,那小廝就樂不得了。
到了門裡,顛顛地搶上兩步去敲倒座房小間的門:「丁香姐姐,快出來了,世子爺回來了!」
那門原是半掩著,聽得叫喚,一個身量高挑的少女忙走了出來,她穿件藕荷色短襖,水色長裙,嫋嫋婷婷,人如其名,真如一枝丁香花般露了面。
她手裡拿著把油傘,一見沐元瑜站在雪裡,忙把傘撐開了遮到他頭頂上,又伸手去拂他身上的落雪,心疼地嗔道:「哥兒看下了雪,不拘哪裡躲一躲,遣個人回來報個信便是了,偏頂了雪回來,看這小臉凍的,娘娘見了可不得心疼壞了。」
這是滇寧王妃身邊的二等大丫頭,所以對他的稱呼不同,透著親暱,沐元瑜待她也透出了尊重來,仰臉含笑回道:「怕母妃等著著急,再者,姐姐那邊的好消息,我也想親口告訴母妃一聲。」
滇寧王妃育有一子一女,沐元瑜之上,還有個相差了足足十五歲的嫡長姐,閨名芷媛,封號廣南縣主。
廣南縣主於十一年前出嫁,嫁與了雲南都司都指揮使家的長子展維棟。
展維棟今年剛至而立,現任都司下轄武定所試千戶,只要不出差錯,明年就可以把頭上這個「試」字去掉,轉為正式的正五品武官了——其實以展維棟本身積攢的軍功,論功敘職,並不必走試職一關,早可以直升千戶,只是他父親展指揮使教子嚴厲,為怕有父蔭徇私而使他人眼熱不服之嫌,硬是壓著兒子升得慢了些。
這卻也無妨,展維棟親爹是統管雲南一應武事的掌印老大,岳父是國朝迄今為止僅餘的異姓郡王,與他的同僚們比,他此時的升職快慢根本無關緊要,升得緩一些,在基層將基礎打牢反而更好。
廣南縣主出嫁後,接連得了兩個千金,隨後便因生產太頻,有些傷了身子,一直調養到今年年初,終於再度有孕,這兩日就是穩婆推算好的預產期了,不想倒是神準,沐元瑜一早去,晚上回來就得了好消息。
小廝退了出去,丁香撐著傘,伴著他繼續往裡走,聞言眼神一亮:「縣主那裡?」
沐元瑜腳步輕快:「母子平安。」
「呦,這可好,娘娘懸了這麼久心,這下終於可以放下來了!」
沐元瑜笑著點頭:「正是。丁香姐姐,我先去給父王請安,妳知道父王現在書房還是清婉院那邊?」
提到這一點,丁香原本飛揚高興的語調馬上降了兩度下來,有點慢吞吞地道:「……清婉院。」
沐元瑜的眼睛還是笑咪咪地彎著,道:「那我們過去罷。」
丁香答應著,小心地投下目光望了他的側臉一眼,心中不免嘆氣:這樣好的小世子,性格寬和大方,處事舉止有度,文武色色用心去學,比外面那些土司家無法無天的少爺們不知出息上多少倍,怎麼王爺就偏偏——
唉。
再多抱不平,也不是她一個女婢可以輕易出口的,丁香只能默默地撐著傘,陪著他一路行到了清婉院前。
整座王府的建築都以闊大威嚴為主,盡顯王家氣象,獨有這處不同,粉牆漏窗,花光柳影,諸般布置擺設娟秀細緻得如同自千里之外的某處江南園林中挪移而來般。
迎出來的女婢亦是身量嬌小,相貌嬌美,福了身柔聲道:「請世子稍待,婢子這便通傳。」
她婀娜轉身去了,丁香對著她的背影撇了撇嘴——她本身氣質幽雅,其實不太適合這種動作,她出口的話就更有反差了:「矮子矮,一肚子拐。」
沐元瑜噗哧笑了。
他母妃身邊的好幾個丫頭都很妙。
迎出來的那女婢是清婉院的主人柳夫人身邊的大丫頭,與丁香其實沒有什麼實際仇怨,但不巧那女婢名叫結香,與丁香恰撞了一個字,這名字倒不是柳夫人起的,而是出自滇寧王爺的意思——以此留念他和柳夫人在一叢結香花旁結緣之事,這等順風揚十里的酸文假醋聽到王妃一脈耳裡如何是滋味,丁香為此看結香就不那麼順眼起來,但弄到現在話都不曾搭上,就對她橫挑眉毛豎挑眼要背後說起壞話來,則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世子。」
結香很快出來了,面上有著歉意,道,「王爺已經歇下,說知道了,天色已晚,請世子去見王妃娘娘罷,娘娘一定掛念著。」
這意思就是不打算讓沐元瑜入內請安了。
沐元瑜早已習慣這般待遇,面色不變,在傘下垂手聽完,回道:「是。有一事請上覆父王,長姐於今日午時二刻生下一子,重五斤二兩,母子均安。」
結香愣了愣,忙笑道:「那可恭喜縣主了,請世子稍候,婢子這便去稟告王爺。」
「不必了。」沐元瑜叫住她,「父王既然已經歇下,我就明日再來請安罷。」
結香微有猶豫:「世子——不等一等?也許王爺想要知道縣主的細況,其實方才我們夫人也勸了兩句的——」
沐元瑜笑著搖搖頭:「不打攪父王了。」
他態度坦定,反是丁香冒火地盯她一眼,掀唇低聲道:「呸,要妳來賣這個好!」
這就是丁香何以厭惡結香的另一重重要原因了,沐元瑜來給滇寧王請安,十回總有六七回見不著,而這出來應話的十回有九回是結香——她是柳夫人身邊攬總的大丫頭,旁人一般也不配來給這對王府中最尊貴的父子傳話。
要論理,這其實怨不著結香,滇寧王要不要見兒子,哪是她一個丫頭說了算的,但每回都是她出來當這個攔駕的惡人,丁香看她自然有遷怒了。
丁香聲音極低,但緊挨著她的沐元瑜還是聽見了,拉了她一把:「丁香姐姐,我有些冷了,我們走罷。」
聽他喊冷,丁香顧不得置氣了,忙道:「好。」
沐元瑜轉身離去。
◎
清婉院,西次間裡。
窗下的紫檀雕螭紋羅漢床上鋪著猩猩紅織錦毛氈,身著家常烏絨道袍的滇寧王姿勢放鬆地坐著,一手擱在中間的小几上,微瞇著眼,半斜著身。
床邊立著一位麗人,穿妃色對襟長襖,挽著簡單髮髻,髻上只插著一根珠釵,她抬著手,輕輕替滇寧王捶著肩頭,隨著她一下一下的動作,那珠釵釵頭上鑲嵌的明珠跟著微微晃顫,床腳擺一架宮燈,燈光珠光交相映襯,映得麗人無比清婉動人。
這麗人便是自進王府一直盛寵不衰的柳夫人了,隨著結香掀開錦簾,再度進來稟報廣南縣主之事,她停下了手裡的動作,著意望了一眼滇寧王的表情。
只見他眼睛睜開,眉頭向上一聳,嘴角跟著舒展開來。
這是個顯而易見的喜悅神色,柳夫人柔聲細氣地向結香道:「有這樣好的消息,怎麼不早說來?世子呢,還不快請進來,說一說究竟,女人生產,可是件極不容易的事,不知縣主遇著什麼凶險沒有。」
她一邊說一邊留心著滇寧王,見他雖未首肯,但未反駁,這便是默認了,柳夫人不著痕跡地鬆了口氣,轉望向結香,目中含了催促之意。
結香看得懂主人的眼色,但卻沒法依言出去,只能輕聲道:「世子聽說王爺已經歇下,便退走了……」
滇寧王的嘴角垂下,才生出的喜意褪了個乾淨。
柳夫人張了張嘴,想說什麼打個轉圜,卻又不好說——這個辰分,將將到用晚膳時,離滇寧王慣常安歇的時候還早得很,滇寧王先前那麼說不過是個不想見兒子的託辭,這也不是頭一回了,父子兩邊心中都有數,但趕上今天這種情形,世子帶了好消息回來,明明是有機會進來請安的,卻還是毫不猶豫地掉頭便走了——
雖說是滇寧王自己的意思,可在他的角度看來,恐怕仍會覺得被兒子掃了面子。
他此刻身上散發出的冷意便是明證。
屋裡陷入沉默,結香感覺到氣氛不對,有點不安,張嘴想說「世子還沒有走遠,不如請他回來」,話未出口,柳夫人察覺到了,搶先一步道:「外邊晚膳讓人擺了沒有?」
結香硬把話吞了回去,轉道:「——已經吩咐人去了廚房,應當快回來了。」
柳夫人點點頭,轉回去柔聲向滇寧王道:「王爺,妾身先出去看一看,若好了,請王爺移駕用膳。」
滇寧王垂著眼,無可無不可地「哼」了一聲。
柳夫人腳步輕盈地帶著結香出去。
厚厚的錦簾一放下,柳夫人面上柔和溫婉的表情就盡皆轉成了無奈。
結香尚有兩分不解,把聲音壓得低低地道:「夫人,為何不讓我請世子回來?有縣主的好消息在,難得王爺心情好,世子豈不領夫人的情……」
柳夫人搖搖頭:「世子若沒走罷了,走都走了,再叫回來,不是那個味了。」
結香聞言有點領悟,但她年歲尚輕,上位成為柳夫人的心腹年份不是很長,還沒有摸到這座滇寧王府尊榮之下掩蓋的暗流,那不解更多地仍舊留存著,嘀咕道:「嫡嫡親的父子,王爺膝下又只得這一根獨苗,連個偏心的地兒都沒有,如何還有這許多計較。」
柳夫人幽幽嘆了口氣:「你問我,我也不知該問誰……」
她是江南姑蘇人氏,天生一種婉柔態度,面上輕愁一籠,結香同為女子都禁不住心疼起來,跟在柳夫人身後往門邊走了兩步,勸道:「罷了,以後夫人別管那些事了,管來管去都是白效力,既沒個作用,也沒人領夫人的情——方才我出去,跟世子來的是王妃身邊的丁香,我請世子等一等,她還衝我說怪話,難道我不是好心不成。」
柳夫人聽了倒不生氣,寬容地道:「她是王妃身邊的人,瞧妳自然不大順眼,妳忍一忍便是,世子總是沒說什麼罷?」
結香點頭:「世子還是一樣客氣,只是他要肯等一等就好了。」
柳夫人素手挑開一線簾隔,望著廊外細密小雪,嘴裡輕輕地道:「妳不懂——王爺不想見世子,但真見不到,又要不高興;最好是他不要見,但世子孺慕懇切,一心巴著他求著他,就要承歡膝下,他才覺得暢意。世子又不是奴婢之流,平白無故為什麼要受這個排揎?他可以低這個頭,也可以不低,王爺拿他又有什麼辦法。」
結香似懂非懂:「夫人說的也是,確實並沒見世子犯什麼錯,不知王爺為何如此。不過,既然這樣,夫人又何必還幫他們穿針引線,替人緩頰。」
柳夫人唇邊飛過一抹輕飄笑意:「王爺和世子怎麼樣,是他們父子的事,我做什麼,是我的事。」
結香知道自己跟的主子外表柔弱,實則內裡是個有主意的人,便收了抱怨,轉而附和著道:「夫人大度,好在夫人這一片心不算全白拋費了去,世子見了夫人總是格外有禮的,西院那裡,世子可不大願意去搭理。」
她說的西院是滇寧王的另一位夫人所居之地,那位夫人姓孟,在王府的資歷比柳夫人深得多,住的院子也好,僅次於滇寧王妃所居的榮正堂。
當年柳夫人進府後,滇寧王得她如獲至寶,看偌大王府剩下的空餘院落皆不入眼,便打上了讓孟夫人讓賢的主意,孟夫人雖為妾室,好歹也是有封號的,且為滇寧王生養了兩個女兒,娘家父親不大不小還任著個官兒,哪裡丟得起這個臉面,便鬧起來不依。
柳夫人才進府,不想與前輩爭風,主動勸說著滇寧王退了一步,滇寧王倒是聽了她的勸,但卻更心疼她懂事知禮,於是沒再去讓孟夫人遷居,卻另選了一處地方,把屋舍全部扒掉重建。
滇寧王這一脈本為中原漢人遷居而來,不過幾輩人在南疆繁衍生息下來,難免有被當地同化之處,建築裝飾風格也有些受到影響,與中原生出了差異來,滇寧王為了解愛妾的思鄉之情,卻是不惜靡費,不遠千里從柳夫人的故土江南運來了工匠及許多材料,耗費了極大功夫,最終造就出這一座玲瓏雅致的清婉院。
隨著清婉院的落成,柳夫人的盛寵踏踏實實地坐實了下來,與此同時,跟孟夫人那邊的怨結也是乾脆俐落地打了個死扣。
聽見結香提起這一點,柳夫人的笑意深了些,嘴裡卻道:「別胡說,我並不求壓倒別人,只望著世子別聽了小人讒言,誤會了我就好了。」
結香很明白她的言下之意,滇寧王已是快知天命的年歲了,柳夫人卻將才三十,老夫少妾,兩邊年紀差了這麼多,滇寧王的身子骨又不算十分硬朗——因前些年遇刺遭了場大罪,雖王府不缺神醫靈藥,慢慢養治了回來,到底虧空了些元氣。柳夫人眼下風光無匹,可將來晚景如何,滇寧王恐怕管不到她,倒是著落在那位小世子身上更多一些。
明白歸明白,結香還是忍不住嘆了口氣:「夫人要是能自己生養個小主子就好了,貼心貼肺的,再不用這樣委屈。」
「……」
柳夫人眼中閃過極其複雜難辨的光芒,是結香無論如何也看不懂的,不過因柳夫人很快低下頭去,她根本也沒機會捕捉到,她只見到柳夫人往自己平坦的小腹看了一眼,然後道:「我如何不想,只是我已經這個年紀——」
她搖了搖頭:「罷啦,總算世子溫和知禮,不是殘暴之人。」
雖如此說,對於專寵十來年卻膝下猶虛這件事,柳夫人心底到底不是不遺憾的,再抬起頭來時,面上笑意便惘然散去了。
結香一時多嘴勾起主子憾事來,說完就後悔了,好在見到迴廊裡幾個著一般樣式比甲的丫頭們過來,手裡捧盤提盒,是自小廚房取了晚膳來,便忙轉移了話題道:「夫人,晚膳好了,您往裡面站站,這裡在風口上,一會簾子打起來,仔細受了寒。」
滇寧王還在裡間,柳夫人也不想在這時陷入憂悒,便點點頭,順著離開了簾隔邊,蓮步輕移,往裡面走去了。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王女韶華(一)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205 |
大眾文學 |
$ 205 |
穿越文 |
$ 221 |
穿越文 |
$ 234 |
中文書 |
$ 234 |
華文羅曼史 |
$ 234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王女韶華(一)
她在這具身子五歲時穿了過來,
自此成了滇寧王府唯一的世子沐元瑜。
可,原以為是女穿男,殊不知其實是女扮男,
這世子,竟是個女兒身!
而這一切的原因,源自她爹──滇寧王。
身為本朝唯一的異姓郡王,為了爵位的承襲,
滇寧王鋌而走險,將女兒當成長子養育,
甚至大膽地向朝廷請封為世子。
從此,她的性別祕密成了關乎性命的大事,
不過既來之則安之,
沐元瑜仍舊放寬心地當起了這個要命的世子。
可隨著她越發長大,父親卻待她日益冷淡,
她這個工於心計的父親,是否……又在盤算著些什麼?
商品特色
溪畔茶 繼《美人戾氣重》後,以女扮男裝為題材,再創精采之作!
穿越成王府世子,應當算是很好運了吧?
只除了……
她這個世子,少了最關鍵的部分──
作者簡介:
溪畔茶
長在淡水湖邊的無聊夢想家,碼字娛己也娛人,一本一腳印,慢吞吞造夢中,希望可以一直給大家寫出好看溫暖的故事,陪我的小天使們走四時風景,過悠長人生。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傍晚。
暮色裡,一片片飛雪打著旋兒,輕盈揚落下來,地上,樹上,行人的頭上,或茅草或青瓦或琉璃堆砌的屋頂上,很快皆染上了一層濕意,那濕意層層累積,緩緩覆白。
廣闊莊穆的滇寧王府靜靜地矗立在這片冬日的初雪中,門楣前懸掛的宮燈在雪花飛融中散發著瑩瑩溫暖的光,朱紅獸頭正門緊閉,只有西側角門還半開著,青衣小帽的幾個門房小廝們縮在階邊角落裡,跺腳哈手地取暖。
天色已晚,又落了雪,這個時辰王府所占的長街前已無行人往來,靜謐中只見飄雪如絮。然而那西側角門並無關閉之意,小廝們也不進到裡面的倒座房小間去躲雪...
傍晚。
暮色裡,一片片飛雪打著旋兒,輕盈揚落下來,地上,樹上,行人的頭上,或茅草或青瓦或琉璃堆砌的屋頂上,很快皆染上了一層濕意,那濕意層層累積,緩緩覆白。
廣闊莊穆的滇寧王府靜靜地矗立在這片冬日的初雪中,門楣前懸掛的宮燈在雪花飛融中散發著瑩瑩溫暖的光,朱紅獸頭正門緊閉,只有西側角門還半開著,青衣小帽的幾個門房小廝們縮在階邊角落裡,跺腳哈手地取暖。
天色已晚,又落了雪,這個時辰王府所占的長街前已無行人往來,靜謐中只見飄雪如絮。然而那西側角門並無關閉之意,小廝們也不進到裡面的倒座房小間去躲雪...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