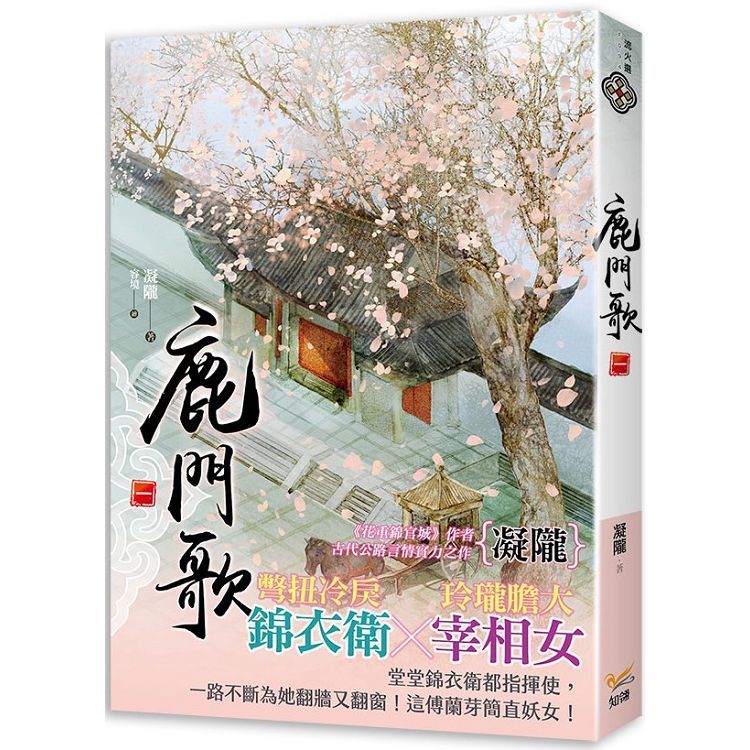在雲南昏沉整月,傅蘭芽剛覺出不對,下一刻錦衣衛便破門而入、奉旨抄家,
自此,她方知父親罹罪下獄,而淪為罪眷的她即將被押赴上京。
間不容髮的一瞬,她當機立斷殺僕藏物,
自認萬無一失,卻瞞不過那個冷戾精明的男人——
打從看見傅蘭芽伊始,平煜就沒被她的傾城姿色迷惑,
這一切都要感謝她父親傅冰,若不是當年發配宣府充軍三年,
他也不會遭俘而被……
冤有頭債有主,平煜沒興趣刁難女人,卻並不代表他跟傅家的仇兩清,
只要這傅家女別老是乖張的陽奉陰違,在他利用完她之前,
倒是可以勉為其難的留著她……
本書特色
《花重錦官城》作者凝隴古代公路言情實力之作
彆扭冷戾錦衣衛✕玲瓏膽大宰相女
堂堂錦衣衛都指揮使,
一路不斷為她翻牆又翻窗!這傅蘭芽簡直妖女!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鹿門歌 一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92 |
二手中文書 |
$ 205 |
中文書 |
$ 205 |
言情小說 |
$ 205 |
古代小說 |
$ 221 |
古代小說 |
$ 234 |
華文羅曼史 |
$ 234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鹿門歌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