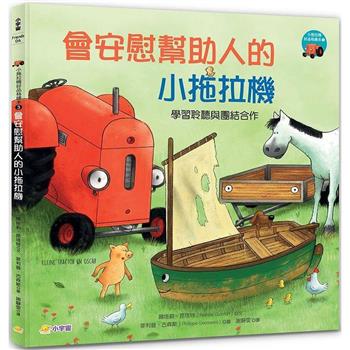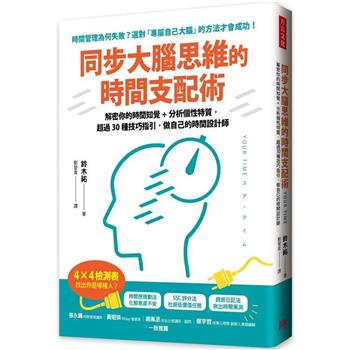楔子
林愫出生那晚,老林在產房門前枯坐。兒媳婦凌晨破水,足足哀號一天一夜,第二夜子時剛到,掙扎著產下一女嬰。
那產婆看到是女兒,血淋淋的胎盤都來不及處理,一團血肉掛在兒媳身下,抱著女嬰跌跌撞撞跑了出來,一把把孩子送到老林懷裡,慘叫一聲:「女孩兒!」
老林溝壑縱橫的臉上露出一抹古怪的苦笑。
「果然,躲不過妳。」
天煞孤星,極陰之身,該來總還是會來。
那晚農曆七月半。遺腹子林愫呱呱墜地,父親在母親孕期意外身亡,母親生產當夜血崩而逝,就連當日接生她的產婆,都纏綿病榻兩年多,死了。
只有老林,枯木一般的老林,將她從襁褓嬰童拉扯大。
「這都是命。」這話老林不知說過多少遍。
「我天煞之身,上剋父母,下剋妻兒。卻命中註定要帶出一個地煞。」老林長嘆。
「待妳成人,我也就能被妳剋死啦。」
老林以畫獸首為生。每年中元節和元宵夜,陝西本地風俗,社火社從一個村子舞到另一個村子,伴隨著秦腔的嘶啞震天吼。老林畫的獸首,就在那秦腔嘶吼中壓軸出場,幾位雜技手圍著那一人高一人寬的巨大怪物頭點起熊熊烈火。老林筆下獸首此時彷彿活了過來,瞳仁烏黑,鼻孔透亮,襯著老林那張枯木般的臉,常有小兒受驚啼哭。鄉間小兒淘氣,婦人皆以老林嚇唬:「再哭,再哭讓老林抓你去餵獸首哩。」每每奏效。
林愫從小跟著他,走遍陝西鄉間社火。林愫十六歲那年,老林沉默了許多。中元夜社火前,他精挑細選,拿出最滿意的那一副,仔仔細細上了色,摩挲了許久,又扭頭對林愫說:「我帶了妳來,要遭天譴。如今妳要成人,我也該走了。這萬般皆是緣,妳不必難過。」
林愫不以為意。老林幾乎次次都要胡言亂語一番。從來沒成真。何況她才十六,離十八歲成人明明還有兩年。
可他這次真的出了事。
那圍繞著獸首面具的熊熊烈火,不知怎麼燒到了老林的身上,將他燃成一具掙扎的怪獸。林愫看著那火中揮舞的肢體,那熊熊烈焰包裹住的人形,淚流滿面。
老林頭七夜,她掙扎著從老林靈前醒來,發現自己來了癸水。
原來,成人是指,成了女人。
第一章
那天是再普通不過的一個星期四的早上,宋書明開一罐北冰洋,照舊把認屍啟事網打開,漫不經心刷著。
每日如此,從不間斷,已三年有餘。
這世界上絕大多數人並不知道,這樣一個看起來就像是釣魚網址的網站,其實是很多人的命根子。他們中的大多數,就像宋書明這樣,日復一日刷開這個網站的更新,期待著奇蹟的發生。
宋書明滑動滑鼠,眼睛緊盯螢幕,最新發布的一條認屍啟事,吸引了他的注意:「城西分局發現一具女屍,身高一六○至一六五公分,體態中等,全身赤裸,頭部及四肢缺失。另該屍體已做DNA鑑定,請各地失蹤人員家屬,如有蛛絲馬跡請迅速聯繫我局。」
他睫毛微微一顫,似是深淵中看到了點點星光。可他又已經習慣,於絕望中有了期盼,又在希冀中歸於失落,一顆心似是烈油烹過般千瘡百孔,又總也控制不住自己在灰燼裡生出勇氣,開始新一輪的找尋。
宋書明默默穿上外套,開車前去。那條路他已走過近百次,閉著眼都知道在哪裡轉彎。到了地方,他輕輕敲了兩下門。門很快吱呀一聲開了,許大生站在門後,對他笑了笑,說:「來了?」
宋書明點點頭,問他:「阿卡呢?來過了嗎?」
許大生搖搖頭,「奇怪了,他這次,沒有來。」
宋書明腳步一頓,「可能有事情耽擱了。」心裡卻打定主意,之後要問問。
兩人走到停屍房,許大生輕輕掀開屍體身上蓋布,說:「我知道你等你妹妹已經很多年了,但是這次,我真的希望不是。」
饒是已有了充分心理準備,又曾有那麼多年辦案經驗,宋書明仍忍不住後退兩步,胸口陣陣翻湧,險些扭頭就吐。他咬緊牙關,生生忍住,不願在許大生面前丟了前刑警的顏面。等緩過一口勁來,才再扭頭仔仔細細翻看。
這具女屍,頭顱和四肢都被鈍器割斷,胸口和下身被砍得七零八落,整塊屍身被泡出了巨人觀(巨人觀:一種人死後,屍體發生高度腐敗和膨脹的現象。),勉強才能辨認出人形。許大生嘆口氣,拍拍宋書明的肩膀,說:「太殘忍了,這可是人彘!聽說撈屍那天出動了半個刑警支隊,消防人員用繩子綁住屍身往上撈,腐爛的屍塊竟大塊大塊往下掉,引來護城河紅鯉魚紛紛湧上啄食屍塊。許多沒見過世面的年輕幹警都吐得一塌糊塗。」
宋書明微微頷首,問:「案子有進展嗎?」
許大生搖頭,「沒有。排查監視耗時太長,幾個同事連番加班,卻沒有提取到什麼有用的線索。剩下的頭顱和四肢,蛙人下水幾天,都絲毫不見蹤跡。」說完很是可惜的看著宋書明,「宋隊,說真的,離了你之後分局少了一大主力,老李跟我說過很多次想你回去,你有沒有考慮過……」
話音未落,就被宋書明打斷:「大生,不要再提這件事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妹妹是怎麼失蹤的。」
許大生卻不肯放棄,仍勸他:「書晴已經失蹤三年多了,生活總要繼續啊。」
宋書明神色堅定,「不找到她,我哪裡還配有什麼生活。」
許大生嘆氣,不再勸他,只將他送出去。
宋書明開車走了十幾分鐘,拿起電話打給阿卡。
響過幾聲才接通,宋書明關切問道:「阿卡,最近新出了一具女屍,你知道嗎?」
電話裡阿卡的聲音很是疲憊:「宋警官,不用了。我已經找到我姐姐了。」
宋書明和阿卡,一個是北京大漢,一個是福建小夥。一個是刑警大學畢業的前警察,一個是初中輟學的打工仔,八竿子打不到一起去。兩人能認識,還是因為經常在許大生那裡撞見。
宋書明不見了親生妹妹宋書晴三年多,劉阿卡失蹤了親生姐姐劉阿采快三年,兩個人生活背景成長軌跡不盡相同,卻都有那一股子不撞南牆不回頭的倔勁頭。尋親尋到最後,總免不了經常來停屍房,認一認那些無人認領的屍體。兩人遇見幾次,聊了幾句,知道彼此境遇相近,很是惺惺相惜了一陣。
此番宋書明聽說阿卡竟然找到姐姐,替他開心之餘不免十分激動,連聲詢問:「怎麼回事?」
阿卡卻不願多說,諱莫如深的樣子。被宋書明問得急了,只拋下一句話來:「宋隊長,展覽路二條三里,四樓五○六,你要想找你妹妹,知情人住在那裡。」
訊息給得沒頭沒尾,宋書明卻毫不猶豫,開了車去展覽路二條。
這一片區他並不熟悉,繞遠了路,開到已是傍晚。連問了好幾個人,卻都不知道所謂展覽路二條在哪裡。本來已經打算放棄,轉過彎打算買瓶水,隨口問了問福利社的老頭,看著也有七十多歲,耳聾眼背,找錢的手哆哆嗦嗦,認了半天沒認出錢。宋書明大手一揮不要零錢了,鬼使神差問了一句「展覽路二條在哪裡」。哪知那老頭竟知道,嘶啞著嗓子說:「展覽路二條,就是老冶金所家屬區。」
宋書明沿著坑窪不平的水泥路往前走,這一片周圍全部被拆遷走後建了新的開發區,只零散分布了幾塊不知什麼原因遺留下的老筒子樓(筒子樓:一種住房類型,一條長走廊兩側各有一排小坪數房間。)。上個世紀五○年代的樓裡,住的基本都是上了年紀無力搬走的老人,水管破舊,電閘常跳,社區年久失修,壓根談不上什麼居住環境。他眼力不錯,進了棟樓,又拿手機照著昏暗的樓梯爬了四樓,樓梯間角落裡密密散布的黑點都是老鼠遺留下的痕跡。宋書明暗暗皺眉,對住在這裡的人又多了幾分沒來由的懷疑。
五○六室在筒子樓最裡面,整條走廊陰冷安靜,門前連盞燈都沒有,掉漆的大鐵門鏽跡斑斑,很難想像有人居住。宋書明幾乎已經不抱什麼希望敲了敲門,卻聽吱呀一聲,門開了。
出乎他意料之外,竟然是個二十歲左右的小女生,身材單薄乾瘦,穿著一件灰撲撲的舊帽T,五官疏淡,年齡雖不大,神色卻死氣沉沉,很不起眼的樣子。
「什麼事?」她問。聲音低沉沙啞,並不十分好聽。
宋書明皺了眉頭,問:「我是阿卡介紹來的。聽說,妳幫他找到了姐姐?」
小女生面色波瀾不驚,讓開門口自顧自往裡走,邊走邊說:「一次八十,不還價。」
宋書明一愣,以為阿卡把自己介紹給了暗娼,猶豫一番站在門口徘徊不前,小心翼翼說:「我是來找人的,不是來做生意。」
小女生似是反應過來,大怒,眼睛瞪得圓滾滾,衝宋書明大吼一聲:「我會問米!」
宋書明回了家,坐在桌前生了一肚子悶氣。萬萬沒想到費了一番周折,阿卡竟然找回一個神婆來。而這神婆女孩名叫林愫,竟然是北方師範大學中文系的大一學生,今年剛剛十九歲,父母雙亡,由爺爺帶大,爺爺去世之後自己孤身生活,直到考上大學。他一開始還不知「問米」是怎麼回事,再多問幾句,才知有些地方流傳在糯米裡插根筷子,請鬼上身回答一些問題。多是想念故人的家人,慰藉心靈的封建迷信罷了。等搞清楚了這個,他立時坐不住了,當即起身告辭,失望的神色掩都掩不住。
臨行前,宋書明滿肚子好奇,終是忍不住問她:「妳為什麼不住在學生宿舍,要在這麼一個破舊社區租房子住?」
林愫瞥了他一眼,面無表情說:「我不愛乾淨。」
宋書明氣結,再不說話,揮揮袖子轉身就走。
回到家中,宋書明原本打算將這事拋在腦後,但夜深人靜躺在床上,卻遲遲不能入睡,像鐵板上的蝦子翻來覆去,他為人本分老實,又仍有警察的正義感作祟,滿心都在憂慮阿卡如果相信了騙子的鬼話散盡積蓄豈不可惜。想了又想,他乾脆爬起身披上衣服,開車直奔阿卡租住的社區。
他上次去,還是大半年前。宋書明到停屍房認屍,恰好又遇到阿卡。阿卡轉了三趟公車,又騎了二十分鐘的共用單車,輾轉三個多小時才來到停屍房。那次的無名女屍看樣子像是精神有問題的流浪妹,黑黑胖胖,宋書明一看就知道不是妹妹宋書晴,也覺得年齡對不上阿卡的姐姐劉阿采。可是他就是不肯放棄,堅持還要再留一次血,方便驗證DNA。
許大生溫言勸了他很久,說阿卡你已經留了好幾次血了,你的樣本我們庫裡有。對上了,一定會找你呢。
他倔著一張臉,一口福建普通話:「血不新鮮了,測不準怎麼辦?」
宋書明嘆口氣,扳著阿卡的肩膀帶他出去。他開車送阿卡回家,才知道他蝸居在城南紅門路一處建材市場的群租房裡面。十幾個人一間房,上下鋪,冬天沒暖氣夏天沒空調,一個月只要六百塊。省下的錢,這些年來全用在東奔西走找姐姐上。
宋書明胸口難受。原以為這世間自己苦痛已是不公,睜眼一看,卻發現芸芸眾生總會有人比你更慘。
最起碼他宋書明,衣食無憂。
他知阿卡攢錢不易,不願看他浪費血汗錢,這次才專門開車去找阿卡,想好好開解他一番。到了紅門路,他找一家小餐館,打電話叫阿卡下來聊聊。
阿卡沉默片刻才應聲。十幾分鐘後出現在宋書明的面前,開口就說:「宋警官,我這半年,去了一趟西安。」
老林去世之後給林愫留下兩萬多存款,她全拿來辦了喪事。買了塊上好的杉木棺材,挑了塊原上背靠秦嶺的風水寶地,風風光光替老林落葬。等喪事辦完,九月開學,就要交學雜費了。
林愫一個初中畢業生,什麼謀生技能都沒有。老林從來不許她上手畫獸首,說她煞氣太重,小地方社火壓不住。她會的手藝,就只有一門祖傳的問米。
老林帶她這許多年,早將技藝手把手傾囊相授。可他自己從沒替人收錢做過,也從未允許林愫試過。她問起來,老林皺著眉頭拿煙袋敲她的頭,「鄰里鄉親的,手藝說出來變了味,妳將來還怎麼嫁人?」
林愫眼熱,想自己試,老林又攔她:「妳煞氣這麼重,我老了,還想多活幾年呢。」
是以她紙上功夫不錯,卻從沒實戰過。
這如今打算把這事做成生意,倒還有些心裡沒底。
林愫收拾好裝備,上薦福寺門前的小商品批發市場,找白大嫂。
白大嫂就是當初接生她的產婆白大娘的兒媳婦。白大娘死後,白大嫂一個人拉扯兒子長大,很是受了老林的照顧。她兒子比林愫大快十歲,初中畢業南下打工,經常寄錢回來。
白大嫂自己在薦福寺前面的小商品市場那裡支個卦攤,城管管得不嚴的時候就賣賣籤香符文問卜,城管管得嚴了就把東西一捲,攤子一收,袖著兩隻手給人看相,靠著一張巧舌如簧的嘴騙些大爺大媽的買菜錢。
林愫來找白大嫂,想求她替她說門生意。剛巧那晚城管不在,白大嫂於是幫她支了張小桌子給人算命,放上零零碎碎自己攤子上的小東西,看起來還很有點樣子。
林愫坐在那裡,周遭都是幾十歲的老婆子,只她一個小女生,很是有幾分臊得慌。初開始面薄臉生,很不好意思高聲攬客。後來日子久了,不但能面不改色招攬生意,還能牙尖嘴利討價還價。
今年六月,聯考結束,林愫趁著暑假漫長,每晚都去薦福寺擺她的小卦攤,就在這裡,遇見了南下尋親的阿卡。
那晚阿卡穿著件破舊的紅T恤,挨著那些算卦的攤子一家家問價錢,還跟老婆子們講價,惹得好幾個老婆子出來唾他:「算命還討價還價,不誠心的呦!」
林愫一抬眼,紅著一張臉的阿卡剛好瞅到她。
阿卡過來問:「算命多少錢?」
林愫:「八十。」
阿卡:「三十。」
林愫:「五十。」
阿卡:「三十。」
林愫:「行。」
阿卡想算的是他失蹤兩年多的姐姐劉阿采的下落。
阿采十五歲跟著同鄉南下打工,一開始在玩具廠的流水線幹拼裝,每天要站十幾個小時,很辛苦,沒幾個年輕女孩子熬得住。剛開始的兩年,阿采斷斷續續寄錢回來,不多,很微薄。
阿卡省吃儉用不敢多花,每天盼星星盼月亮等姐姐回家。待到第三年春節返鄉,阿采卻一副衣錦還鄉榮歸故里的樣子,穿著簇新的名牌衣服,挎了個亮晶晶的黑漆皮包,一進門就塞給弟弟一個厚厚的信封,說是兩萬塊錢。
阿卡嚇了一跳,把那厚厚一沓子錢攥在手裡,緊張得掌心都在冒汗。阿采喜氣洋洋告訴他說她交了男朋友,來年國慶就要結婚,還可以在東莞買下一套小房子。明年阿卡初中畢業,不要再繼續讀了,她來接他去東莞,跟著她一起做生意。
阿卡也很興奮,卻沒想元宵節還沒過完,村裡就有風言風語傳來,說阿采在東莞做的不是正當生意,下了海,做了「雞」。
傳這話的自然是鄰居那些眼熱的年輕媳婦,生了女兒的都守在村子裡,直到生下了兒子才能有機會跟著丈夫出去打工,看阿采年紀輕輕賺了大錢,自然疑心她賺的不是乾淨錢。
阿采卻不似一般下了海的女孩那樣心虛,梗著脖子打上人家家裡去,叉著腰罵,一副理直氣壯的樣子。
「不下蛋的母雞,沒得敗壞老娘名聲,老娘明年就要嫁人的來!」
她自幼雙親俱喪,早早立身拉扯弟弟,一身剽悍性格,這麼光明正大一喊破,旁人倒也摸不清楚她在廣東到底做些什麼。
阿卡倒也關起門來問她。他們姐弟自幼親厚,阿采也不瞞他:「做生意。幫人牽線搭橋咯。」
又掩了口神神祕祕:「卡仔千萬記得收聲不要亂講。阿姐這條路,日進斗金的呀。」
他這一下更害怕了,生怕姐姐犯了事被抓了起來,又著急著慌問她,姐夫是做什麼的。
阿采噗哧一笑,還拿弟弟當小孩,輕抱住他,微微搖晃,哄他:「阿姐萬沒有做傷天害理的事情,刑警也不會抓我。你姐夫做的正經事,開公司的,還出過國讀大學,嫁了他,我們姐弟就有好日子。」
阿卡半信半疑。實在怨不得他不信,自家人自家最清楚,劉阿采自幼就算不得美女,連路人長相說起來都很勉強。一張黃面皮,歪鼻大口,粗眉小眼,何況姐姐小學勉強畢了業,初中都沒有讀,怎麼能短短時間內輕鬆攢下十幾萬來,還能在東莞買房子。
他日夜憂心等著姐姐捎信,好南下找她。
可姐姐阿采,再也沒有捎來過隻言片語。
阿卡從春節等到了五一,從五一等到中秋,從中秋又等到國慶,直到村裡流言蜚語逼得他走投無路,乾脆揣著姐姐給他的那兩萬塊錢,自己買了張票去東莞。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白夜問米(上)的圖書 |
 |
白夜問米(上) 作者:touchinghk 出版社:知翎文化 出版日期:2020-03-05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92 |
二手中文書 |
$ 221 |
小說/文學 |
$ 234 |
靈異/推理 |
$ 234 |
中文書 |
$ 234 |
推理/驚悚小說 |
$ 234 |
文學作品 |
$ 234 |
Literature & Fiction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白夜問米(上)
自妹妹失蹤,父母傷心而亡,宋書明的人生就此暫停,
不當警察改做偵探,日日查著認屍啟事,進出停屍間,
即使他仍抱著一絲希望,妹妹書晴仍活著……
經由同為失蹤者家屬的朋友介紹,他找上了林愫幫忙,
卻沒想到這個大一小女生原來是個……神婆?
「一次八十,不還價。」
林愫自問很有良心,只想靠問米小技能卜卜卦找找人,
賺點大學學費生活費,不坑人的。
可眼前這位偵探大哥居然先是以為她在賣身,
又質疑她的「專業」,拉她去看無頭人彘女屍當測試。
幸好從小有祖父老林把詭事異術當床邊故事,
拿鎮鬼法器當玩具,假旅遊真除妖,讓她練得些本事。
但殭屍注魂、屍油花露、陰山血玉、人皮羅剎……
怎會這些被耳提面命要避開的邪術,
眼看就要被她遇了個遍……
商品特色
她只是個想賺點生活費的女大生,誰知──
問米卜卦卻問到邪術精怪盡出?!
無頭人彘、殭屍殺人、以屍油為食的鼇蟒,殺人全族的血玉……
不過是幫忙曾任警察的偵探大哥找妹妹,結果看她都找出了啥?
作者簡介:
touchinghk
曾在世界多個國家地區漂泊多年,現與家人居住北京。喜歡突如其來的轉折和意想不到的結局。著有《白夜問米》《雲中有鬼》《鳳靈》《洗白之路》等作品,並在晉江文學城連載。
章節試閱
楔子
林愫出生那晚,老林在產房門前枯坐。兒媳婦凌晨破水,足足哀號一天一夜,第二夜子時剛到,掙扎著產下一女嬰。
那產婆看到是女兒,血淋淋的胎盤都來不及處理,一團血肉掛在兒媳身下,抱著女嬰跌跌撞撞跑了出來,一把把孩子送到老林懷裡,慘叫一聲:「女孩兒!」
老林溝壑縱橫的臉上露出一抹古怪的苦笑。
「果然,躲不過妳。」
天煞孤星,極陰之身,該來總還是會來。
那晚農曆七月半。遺腹子林愫呱呱墜地,父親在母親孕期意外身亡,母親生產當夜血崩而逝,就連當日接生她的產婆,都纏綿病榻兩年多,死了。
只有老林,枯木一般的...
林愫出生那晚,老林在產房門前枯坐。兒媳婦凌晨破水,足足哀號一天一夜,第二夜子時剛到,掙扎著產下一女嬰。
那產婆看到是女兒,血淋淋的胎盤都來不及處理,一團血肉掛在兒媳身下,抱著女嬰跌跌撞撞跑了出來,一把把孩子送到老林懷裡,慘叫一聲:「女孩兒!」
老林溝壑縱橫的臉上露出一抹古怪的苦笑。
「果然,躲不過妳。」
天煞孤星,極陰之身,該來總還是會來。
那晚農曆七月半。遺腹子林愫呱呱墜地,父親在母親孕期意外身亡,母親生產當夜血崩而逝,就連當日接生她的產婆,都纏綿病榻兩年多,死了。
只有老林,枯木一般的...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