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郭媛根本就沒去管郭凌,只逕自向那花架子旁走了兩步,抬手便揪下一把葉子來,拿在手裡胡亂撕扯著,眉眼間一派森寒:「包玉春那廝,真真是滑頭得緊,我幾回進宮,卻一次都沒找見過他的人。」
這話顯然是說給攜芳聽的,攜芳聞言,蹙眉想了想,便低聲回道:「那依縣主看來,婢子要不要再請乾娘進一趟宮?」
「用不著了。」郭媛陰著臉說道,一把就將扯碎的葉片扔了出去,散得滿地都是:「包玉春定然不曾得手,若不然他肯定一早就蹦出來跟我請賞了,還能憋到現在?」
越往下說,她便似是越恨,眼中的怨毒幾乎能射穿那厚厚的濃蔭,切齒道:「這陳三,怎麼就如此難纏?我原想著叫包玉春藉搜身之機,記下她身上的記號,不拘是美人痣還是胎記,只消記下了一樣兒,再把這事兒往那下三濫的地方一傳。到時候,這位陳三姑娘的名號,可就要傳遍下九流了。」
她的面上露出了陰冷而又得意的笑容,旋即卻又沉下了臉,恨恨道:「可恨!當真可恨!這陳三竟還能滑脫了去,到如今包玉春更是連面兒都不敢露。早知如此,我還不如把那銀子餵了狗呢!」
攜芳覷著她的面色,小心翼翼地道:「縣主要不要換個法子……」
「罷了。」郭媛打斷了她的話,面色雖然陰沉,但眼神卻顯得很冷靜:「我已經出過三回手了,回回都被那陳三識破,如今宜靜不宜動,不然又是一場是非。」
說罷此語,她心底又是一陣怒恨交加。
可恨陳瀅,幾次三番與她過不去,上回武陵春宴之時,更是大大地下了她的臉。
她可不想再被人指指點點地當笑話看了。
郭媛的面色又往下沉了沉。
若非司徒皇后特意把她召進宮中,又親命著福清公主與她同吃同住,好歹圓過了場面,她在武陵春宴上丟的那些面子,只怕到現在還撿不回來。
「等過了這陣風頭,我再找個機會狠狠治一治陳三。」郭媛低聲語道,面色十分陰沉。
攜芳情不自禁地打了個寒顫,往後退了小半步,垂頭不語。
在花架下又站了數息,郭媛身上的氣勢方才一鬆,意興闌珊地道:「罷了,回去吧,也別叫母親等得太久。」
攜芳輕聲應是,提聲喚來一眾小丫鬟,眾人便又圍隨著郭媛,回到了小花廳。
回去時,那戲文正到好處,咿咿呀呀的曲聲和在風裡,唱的卻是:「嫋春風遊絲嬌軟,飄朱欄飛絮如煙,恁是那錦瑟流年暗偷換,奴呀奴,且自憂憐。」
這幾句戲文,被那伶人唱得格外綿軟悠長,臺下的長公主已是聽得癡了,就連郭媛回來都沒發現。
郭媛素知她愛聽戲,便也不去擾她,自坐了下來,轉首四顧,這才發覺,花廳裡似是比方才空了好些,許多人都不見了,而那些仍舊在座的夫人們,縱然還在聽著戲,但卻一個個的面色各異,似是心神不屬。
郭媛不由暗自奇怪,又見那一曲已然唱罷,便往長公主身邊湊了湊,輕聲地問:「母親,怎麼這一轉眼的人就不見了好些?女兒出去的這一會兒,出了什麼事兒麼?」
長公主往四下裡看了看,不在意地一笑:「聽說是劉家的姑娘落了水,劉夫人並妳祖母她們都過去了。」說罷她便又笑著輕撫郭媛的髮絲,柔聲道:「還是我們阿嬌聰慧乖巧,早早地便陪在母親身邊,母親也省了心。」
郭媛聞言,面上帶笑,眉心卻是蹙了蹙,沒說話,只繼續安坐著陪長公主聽戲不提。
且說劉夫人並程氏,此時已然趕到了水邊,眼瞧著劉霜兀自正坐在那石凳子上哭,身上縱披著衣裳,但裙子卻是濕得透了,盡皆黏在身上,髮鬢也散亂不堪。
那劉夫人自來是個沒主見的,見狀立時就慌了神,又見女兒形容可憐,眼圈兒也跟著一紅。
程氏在旁見了,卻是在心裡念了句佛。
劉霜除了身上髒了些、衣裳濕了些,人卻是好好地,也沒斷胳膊少腿,程氏自是放下了一顆心,又見郭冰與郭凝安排得很妥當,那春凳子也抬了來,她的心便更是落回了肚裡。
王氏姐妹正立在人群外瞧著,因見劉夫人一臉心疼地抱著劉霜,王敏芝的心下頗為感慨,回頭正要說話,忽然發現,陳瀅居然不見了。
「咦,阿瀅人呢?哪裡去了?」她往左右看了看,便問一旁的王敏蓁。
王敏蓁沒說話,只伸手往人群中央一指。
王敏芝凝目看去,不由張大了眼睛。
不知何時,陳瀅居然擠進了人群中心,正彎著腰站在劉霜腳旁,盯著她的一隻腳看得出神。
「她怎麼過去了?」王敏芝大是不解,輕聲問道。
王敏蓁搖了搖頭,神情卻是十分淡定:「想來她有她的道理,我們在這裡看著便是。」
王敏芝立時點頭:「大姐姐說的是,若是有什麼能幫得上的,咱們也幫一把。」
姐妹二人悄聲說著話,那廂陳瀅卻已是又往前移了兩步,一雙眼睛仍舊盯著劉霜的腳,就像是那上頭有什麼東西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郭冰早就瞧見她了,只礙於人多不好說話,此刻見她居然越靠越近,不由便擰著眉頭道:「陳三姑娘怎麼過來了?有事麼?」
沒事就走遠點,別跑來礙眼。
這是她的未盡之意,雖未言明,陳瀅卻聽懂了。
她看了看郭冰,一抬手,卻是指向了劉霜的左腳,神情很是鄭重地道:「郭大姑娘,妳瞧見了麼,劉姑娘的鞋子上有東西。」
這話一出,包括劉夫人在內的一眾人等,便皆將視線轉向了劉霜的鞋,果見那鞋子上有幾縷細細的黑色的東西,似是水草。
貴女們穿的繡鞋上通常都要繡花兒的,那鞋面自然就不夠平整,就算偶爾勾著些什麼東西,也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兒。
「不過幾根水草罷了,陳三姑娘不會連水草都沒見過吧?」郭冰有些不耐煩地道,深覺陳瀅就像是專門生下來剋她們興濟伯府的,方才在亭中之時,她便給了人好大一個沒臉,如今又來了。
郭冰的話對陳瀅卻是沒有半分影響。
她像是沒聽見一般,提起裙襬,竟在劉霜的腳邊蹲了下來,仔細地看了那水草好一會,方抬頭轉向了旁邊的興濟伯夫人程氏,認真地道:「郭夫人,這不是水草,這是人的頭髮。」
此言一出,方才還亂糟糟的人群,漸漸地便安靜了下來。
參加此次壽宴的人中,有不少也曾赴過之前的武陵春宴,如今聽得陳瀅所言,諸人便又想起前事,不由得心下都在打鼓。
這莫非又是出了事兒?
抑或是說,這位陳三姑娘,又要進行她那種古怪的查證法子了麼?
「我仔細瞧過了,不會錯的。」陳瀅繼續說道,並不因周遭氛圍的改變而有異動,仍舊一臉地平靜:「且我還能夠肯定,這頭髮不是劉姑娘的,也不是那幾個會水的健婦的。這頭髮在水裡浸泡的時間,至少超過兩個月。」
這話一出,程氏身上的汗毛立時就豎了起來,旁觀的眾人亦是頭皮發緊。
這種頭髮之類的東西,很容易讓人有不好的聯想,有幾個膽小的姑娘,這時候臉兒都白了。
「妳……妳胡說什麼?這……這分明就是水草!」說話的是劉夫人,語聲微有些顫抖:「我女兒的身上,哪裡……哪裡來的頭髮?」
她一面否定了陳瀅的說辭,一面便伸出手去,似欲摘取那幾根所謂的水草。
可不知為什麼,她的手卻停在了半空,遲遲不曾落下,臉色也開始發白。
那幾縷黑色的長絲,初看時的確像是水草,可是仔細看去,便能瞧見那顏色是純正的黑,而不是水草那種黑中泛綠的顏色。
確實很像是人的頭髮。
劉氏的面色越發慘白,劉霜也停止了哭泣。
這可憐的姑娘像是一時失去了反應,只呆呆地看著鞋面上那幾縷長長而彎曲的黑絲,嘴唇微顫。
「妳這孩子,說的什麼話兒?」程氏終於開了口。
她竭力維持著鎮定,強撐出一張笑臉來,嗔怪地看向了陳瀅:「妳沒見過,不知道,那就是一種水草。這水裡種著蓮花兒呢,淤泥甚厚,水草自然也多些。」
她一面說,一面便環視四周,笑著解釋地道:「我們府裡的碧荷開得這麼好,都是這些水草的功勞,若不然,大家也沒的花兒好賞了。」
「很抱歉,郭夫人,我並不贊同妳的觀點。」陳瀅完全沒給程氏面子,說話間便站了起來,「刷」地從袖中掏出了一塊金光燦燦、寫著「神探」二字的金牌,高舉過頂。
此舉大出眾人意外,所有人都怔怔地看著她,程氏更是一臉呆滯。
陳瀅高舉金牌,環視四周,語聲清晰而肯定:「聖上御賜金牌在此。我陳氏三女,以御賜神探之名,在此聲明,這水底下,有死屍。」
「轟」地一聲,水邊立時炸開了鍋。
死屍?
興濟伯府的碧荷塘裡,居然埋著屍首?且那屍首的頭髮,還纏在了一位貴女的鞋子上?
劉家母女齊齊白了臉,劉夫人搖搖欲墜,劉霜更是神經質地尖叫起來,一面拚命將身子朝後閃,似是要躲開那鞋子上的頭髮。
陳瀅忙伸手按住她,向她擰了擰嘴角,露出了一個自認為最和善的笑:「別怕,我替妳把這些死人頭髮給弄下來。」
她不笑還好,這一笑,劉霜立馬兩眼一翻,朝後便倒,竟是生生被陳瀅給嚇暈了。
場中再度炸起一陣驚呼,好些人甚至認為那死人的頭髮自己動了起來,直嚇得面白唇青、連聲驚叫。
那一刻,那些過往聽來的、看來的志怪傳說,盡皆冒了出來,越想越叫人害怕,岸邊登時一片大亂,受了驚嚇的姑娘太太們有往回跑的,也有尖叫著就是挪不動腳的,嚇哭了的更是不在少數。還有人見劉霜暈過去了,想要趕過來瞧的,一時間人擠人、人碰人,直是亂成了一鍋粥。
郭冰再也忍不下去了,猛地回身看向了陳瀅,張目怒道:「妳有什麼毛……」
「大姐姐,噤聲!」郭凝及時制止了她,一面便將視線轉向了陳瀅高舉的那隻手。
那面御賜的金牌,在午後的烈陽下熠熠生光,幾乎能晃花人的眼。
在這電光石火間,郭冰陡然記起,這位陳三姑娘,乃是元嘉帝親口應下「便宜行事」的「神探」。
連陛下都這樣說了,即便請長公主出面,想必也震不住這位御賜的「神探」。
剎時間,郭冰面色鐵青,視線飄向人群之外,便看見了並肩而立的王氏姐妹。
一塊御賜金牌,再加上一個王家,興濟伯府今日可算是倒了血楣,竟把這兩尊神給請了過來,如今就是要趕她們走,那也是不成的了。
與郭冰同樣面色難看的,還有程氏。
她回首看了看小花廳的方向,思忖片刻,召手喚過一個管事媽媽,低低地吩咐了她幾句,那媽媽便匆匆去了。
程氏擰著眉頭,重又回身看向陳瀅。
此時,陳瀅正戴著古代版自製手套,小心地從劉霜的鞋面兒上摘取那幾根髮絲。
劉霜暈了過去,這也算是給了陳瀅一點便利,能夠毫無阻礙地收集證據。
至於劉夫人,她此刻已是嚇得六神無主,只曉得抱著女兒哭,哪裡還顧得上陳瀅?
將那幾根頭髮取下來之後,陳瀅便迎著光細細端詳。
鑒於這個時代男女皆留長髮的風俗,她暫且還不能從這幾根頭髮上推測屍體的性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具屍首一定還在水中,因為在頭髮的根部,陳瀅發現了幾粒細小的絮狀物,有點像是皮膚組織。
陳瀅習慣性地擰了擰嘴角。
一般說來,屍體腐爛的速度依次為:空氣一、水中二、地底八。
也就是說,暴露在空氣中的屍體,其腐爛的速度是最快的,次之為水中,最慢的則是地底。
當然,這也不能一概而論。如果是在極深的水底,比如接近零度的深海,屍體反倒會停止腐爛,得以較好地保存。在現代時,失事的庫爾斯克號潛艇在沉入水中一年之後,還曾搜出過幾名船員的完整遺體。
根據從偵探先生那裡學來的些許法醫學知識,陳瀅可以粗略推斷出,這具屍體落水的時間,差不多在兩、三個月前。
這其實也是需要據水中情況而定的。通常條件下,屍體在死水中腐爛的速度會更快些,而劉霜落水的地方是一片活水,因而陳瀅才有了如上判斷。
正在她盯著那頭髮思索之時,耳邊忽地傳來了一個蒼老的語聲:「三丫頭,妳這是在做什麼呢?」
竟是許老夫人的聲音!
陳瀅心下微驚,抬頭望去,果見許老夫人正扶著許氏的手,身邊跟著花容失色的沈氏並柳氏,正站在不遠處看著她。
她們怎麼過來了?
心念電轉間,陳瀅飛快地看向旁邊的程氏。
原以為來的會是長公主,不想程氏卻是劍走偏鋒,居然把許老夫人給請來了。
不以勢壓人,卻以輩分及孝道說話,程氏這一招兒,倒也算得精明。
不過,她顯然誤會了陳瀅,以為陳瀅這是藉機生事,純粹就是跟興濟伯府過不去。
想來,在這位伯夫人眼中,人命一點也不重要,伯府的臉面才更為要緊。
思及此,陳瀅的嘴角,便又擰向了那個奇怪的角度。
她的想法,與程氏剛好相反。
她向著許老夫人微微躬身,人卻仍舊停在原處,平靜地道:「回祖母的話,孫女謹遵天子之命,遇案查案,便宜行事。」
「原來如此。」許老夫人點點頭,沉吟了片刻,驀地轉身吩咐:「留幾個人下來幫著三丫頭,別叫她找不著人手使動。」語罷,老人家施施然轉向程氏,投去微含歉意的一笑:「這丫頭胡鬧慣了,只是陛下有言在先,老身……委實不好多管。」
居然乾脆俐落地就把陳瀅給留下了?!
程氏驚訝地張大了眼睛,正想要說些什麼,卻不妨那頭跑來個管事媽媽,一臉惶惶地道:「稟……稟告夫人,京府衙門的老爺……老爺們,穿著官服來的,說是要……登門查案子。」
「妳說什麼?京府衙門?查案子?」程氏登時面色大變,再顧不上許老夫人,蒼白著臉焦灼地看著那管事媽媽,說話聲兒都有點岔了調兒:「他們怎麼會來?府裡出事兒了?難不成世子爺他又……」
說到這裡,她忽然就噤了聲,一臉忌憚地看了看遠處的王家姐妹,眼底深處,飛快地劃過了一絲怨憤。
「沒……不關世子爺的事兒……」那管事媽媽見她明顯是想歪了,忙忙搖頭,說著便偷眼覷了陳瀅一眼,壓低了聲音回道:「回夫人,就是這河裡的……屍首……府衙的人……不知怎麼的,全都知道了。」
原來是這麼回事兒。
程氏大鬆了一口氣,再一琢磨,又險些氣個倒仰。
這位陳三姑娘倒真是好本事,不聲不響地,也不跟伯府打個招呼,居然直接就把盛京府衙的人給召了來。
且不論這水底下有沒有屍首,伯府這回真是丟了個大臉。
程氏越想越是氣恨。
成國公府這是存了心要把壽宴給弄得不歡而散,把他們興濟伯府的臉面往地上踩啊!
「妳這……」程氏拿手指著陳瀅,手指頭抖個不息,只說了兩個字,就再也接續不下去了。
縱使在娘家練就了一身嫻熟的罵人本領,但此時此刻,她卻根本罵不出口。
就衝著人家手上的御賜金牌,她也沒那個膽子敢口吐汙言。
可要是不罵,程氏這心裡又窩火得緊,只覺得窩囊透頂,好好地辦個壽宴,竟給攪得這麼一團糟。
「郭夫人還請不要誤會,我並無他意,只是想要查明真相罷了。」陳瀅向她解釋了一句。
陳瀅確實不是故意針對誰家的。即便這是在皇宮之中,只要出現屍首,她也一樣要查。
這本是她的肺腑之言,然聽在程氏耳中,卻是格外刺耳。
只是此時此刻,就算她有千百句罵人的話要說,可惜竟是發作不得,只能苦笑著收回了手,搖搖頭:「三丫頭說笑了。」語罷又將眼風往那湖上一掃,淡聲道:「三丫頭口口聲聲兒說這湖底有死屍,這萬一妳說錯了,又當如何?」
「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湖底有死屍。」陳瀅垂下頭來整理著手中的死者髮絲,神情篤定。
程氏聞言,心頭又是一陣地堵,旋即又有點心驚肉跳。
到底她也是一府主母,府裡的事兒她比誰都清楚,這湖裡到底有沒有屍首,這還真是……
她搖搖頭,禁止自己再繼續往下想。
為今之計,還是要先把事情糊弄過去再說。此外,該提醒的人也該提前知會一聲,也免得事到臨頭亂了陣腳。
她這裡正自沉吟著,那管事媽媽卻是挨近了些,以極輕的聲音繼續說道:「伯爺正在前頭與府衙的老爺們說話呢,只那些老爺們來的人數不少,伯爺怕招呼不過來,便遣了大管事送賀客們先離開。伯爺便遣奴婢來問一聲兒,夫人看看,要不要請長公主殿下出來說句話兒?」
程氏皺著眉頭,藏在袖中的手緊緊攥著,尖利的指甲觸著掌心,有輕微的刺痛。
說不得,還是要請她那個尊貴的兒媳露個臉。
她暗自咬了咬牙,正要提聲喚人,忽聽一人語道:「母親,使不得。」
她怔了怔,轉首便見大女兒郭冰不知何時走了過來,一面走一面給她使眼色。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出閨閣記(二)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出閨閣記(二)
陳瀅隨許老夫人等家中長輩前往興濟伯府參加壽宴,
卻因一場湖中泛舟的意外,牽扯出兩條命案來。
眾女眷驚惶不安,唯有拿著皇帝御賜「神探」金牌的陳瀅,
一個箭步往前探看,趁此良機一展推理長才!
只是前來處理的不只有府衙的人,
還來了一個她意想不到的人──代表刑部前來的裴恕。
且兩人意外的想法合拍,思慮接近,
是陳瀅以女子之身,在這個思想落後的古代,
難得可以合作的對象。
可身在內宅,又出了幾次風頭,
難免便要成為人所看不順眼的目標。
一只紙人的嫁禍,意外被陳瀅提前揭破,
她原想趁此機會和許老夫人談條件,避到莊子裡去,
卻不想久不理事的母親李氏竟在此時挺身而出,
準備帶她與兄長陳浚,一起前往山東拜訪舅舅與外祖母。
若能趁此機會看看大好山河,才是不枉此生!
商品特色
《庶庶得正》作者姚霽珊,又一部古裝推理宅鬥作品。
御賜金牌在此!
陳氏三女,以御賜神探之名,
奉君命在此查案!
作者簡介:
姚霽珊,金陵人士,坐望六朝煙水間,汲泉煮字、搗文成衣,文字細膩優美,擅寫景抒情,散文及小說見諸各雜誌報刊,曾出版作品《至媚紅顏》、《一花盛開一世界,一生相思為一人》、《世間女子最相思》、《願你已放下、常駐光陰中》,現為閱文集團簽約寫手,著有長篇小說《庶庶得正》、《折錦春》等。
章節試閱
第一章
郭媛根本就沒去管郭凌,只逕自向那花架子旁走了兩步,抬手便揪下一把葉子來,拿在手裡胡亂撕扯著,眉眼間一派森寒:「包玉春那廝,真真是滑頭得緊,我幾回進宮,卻一次都沒找見過他的人。」
這話顯然是說給攜芳聽的,攜芳聞言,蹙眉想了想,便低聲回道:「那依縣主看來,婢子要不要再請乾娘進一趟宮?」
「用不著了。」郭媛陰著臉說道,一把就將扯碎的葉片扔了出去,散得滿地都是:「包玉春定然不曾得手,若不然他肯定一早就蹦出來跟我請賞了,還能憋到現在?」
越往下說,她便似是越恨,眼中的怨毒幾乎能射穿那厚厚的濃蔭,切...
郭媛根本就沒去管郭凌,只逕自向那花架子旁走了兩步,抬手便揪下一把葉子來,拿在手裡胡亂撕扯著,眉眼間一派森寒:「包玉春那廝,真真是滑頭得緊,我幾回進宮,卻一次都沒找見過他的人。」
這話顯然是說給攜芳聽的,攜芳聞言,蹙眉想了想,便低聲回道:「那依縣主看來,婢子要不要再請乾娘進一趟宮?」
「用不著了。」郭媛陰著臉說道,一把就將扯碎的葉片扔了出去,散得滿地都是:「包玉春定然不曾得手,若不然他肯定一早就蹦出來跟我請賞了,還能憋到現在?」
越往下說,她便似是越恨,眼中的怨毒幾乎能射穿那厚厚的濃蔭,切...
顯示全部內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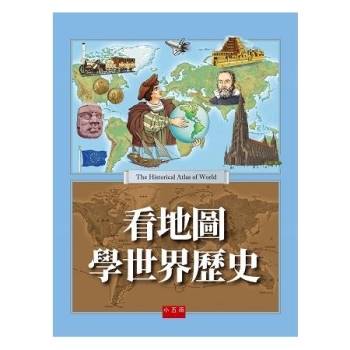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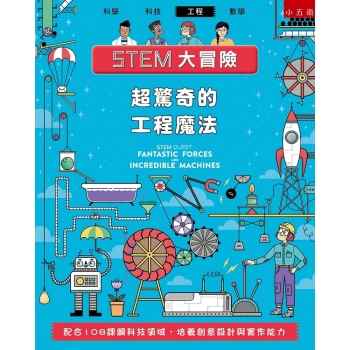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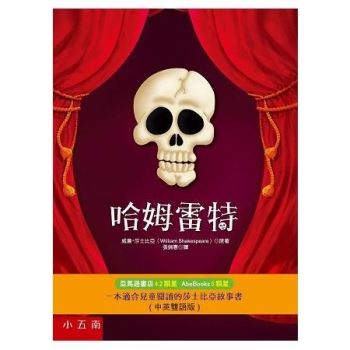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