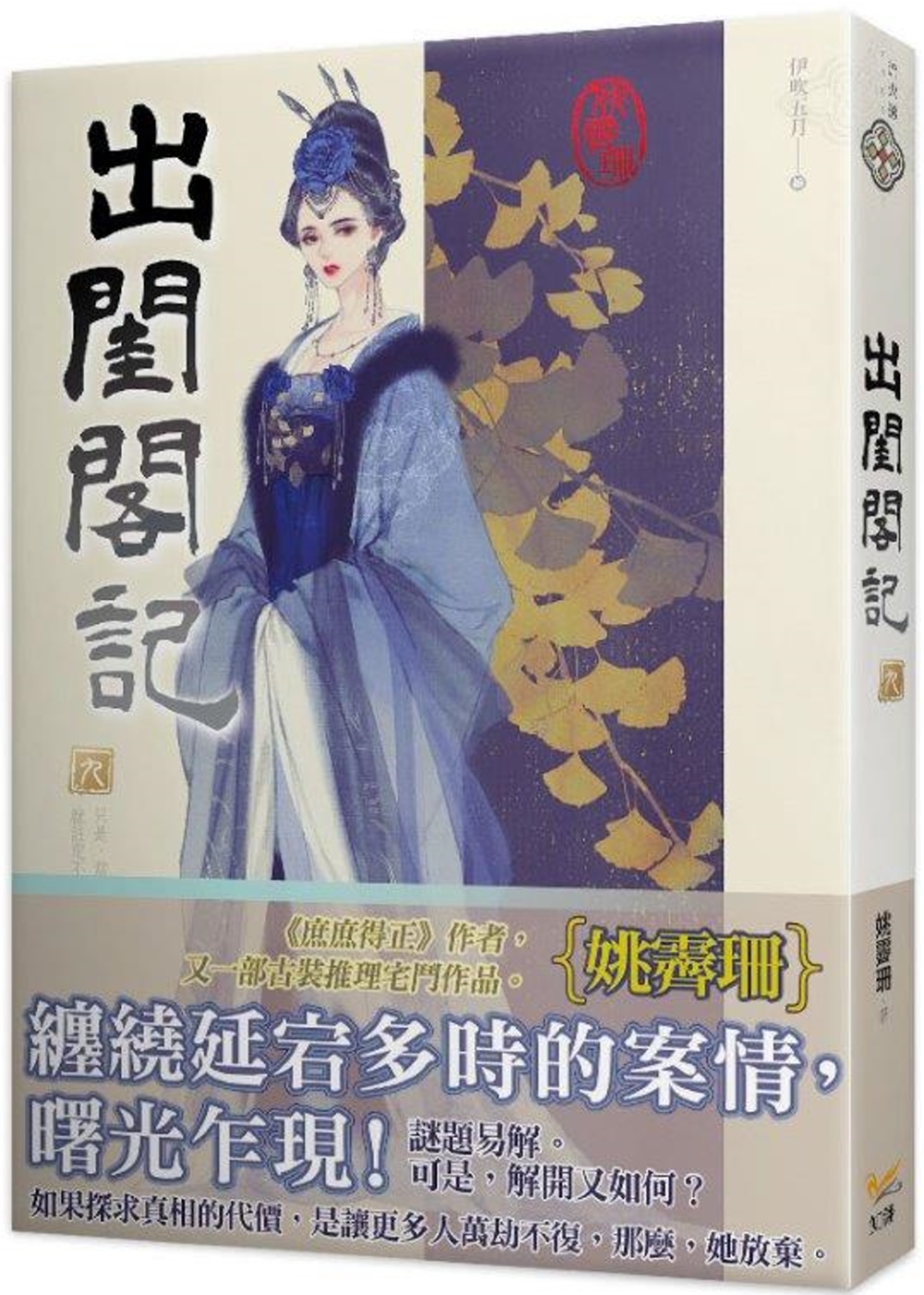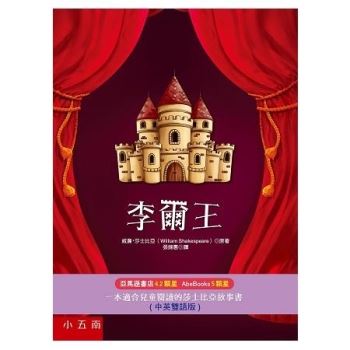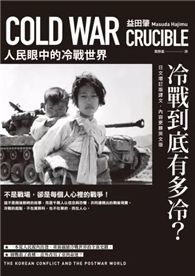第一章
裴恕脖根兒都紅了,好似那心尖尖也被這纖指撩著,跳得擂鼓也似,嗓子眼兒幾乎冒煙。
可偏偏地,那冒出來的煙卻又甜得很,彷彿那飄進傘下的細雨,也是糖水兒化出來的。
他紅著臉往四下瞧,又侷促、又歡喜、又有幾分不安。
見他已然不好意思到了極致,陳瀅亦覺心虛。
在男女之事上,她的經驗比他多了太多,總這樣戲弄他,似乎也不太好。再者說,當導師縱然有趣,只學生面皮太薄,卻也教她心軟,不忍繼續。
所以,她打算適可而止。
她故意抬頭,看向傘外灰暗的天空,給出空間,由他自己轉過來。
雨下得不疾不緩,青布傘面兒上餘音輕透,如一曲清弦,分明空漠離塵,然入耳時,卻又因了雨打疏葉、水過橫枝,而有了別一番纏綿。
陳瀅略有些出神。
算算日子,他們趕回京時,李氏怕就要往濟南來了。
雖李氏從不曾言明,可陳瀅卻知道,李氏離京,有一多半兒,是為了陳劭。
她在有意地避開他。
居家時,分院而住;如今,乾脆避回娘家。
這非是她對陳劭無情。
正相反,真正的無情,是漠然冷淡,是縱使人在眼前、四目相顧,亦可視之如無物。
而李氏卻不同,她必須以空間的隔絕,達到「眼不見、心不煩」的目的。
她對陳劭,其實尚有餘情未了。
陳瀅不免有些唏噓。
哪怕嘴上說得再狠、再絕情,人心卻不會作偽,那些出自於本能的舉動,往往比言語更能照見真心。
她無聲地嘆了口氣,心中念頭百轉,腳下亦無意識地遵循方才的步幅,往前行去。
可就在此時,她與裴恕握在一處的手,倏地被他一扯。
她以為裴恕有話要說,忙自傘外收回視線。
然才一轉首,她的眼前,便現出一張放大的臉。
確切地說,是半張面頰。
裴恕正側對著她俯身,也不說話,那半個紅通通的面頰,離陳瀅僅一寸之距。
「阿恕,你怎麼了?」陳瀅簡直詫異。
好端端地,裴恕把臉湊過來做甚?
她不問還好,這一問,裴恕的大紅臉上,登時冒出幾粒汗珠。
可他仍舊不語,也可能是害羞得說不出話來,遂只能以動作表明態度。
於是,陳瀅便瞧見,那半張大紅臉,以極其緩慢的速度,一點一點地往她面前湊,隨後,精確地停在了半寸這麼個妙到毫巔的位置,方才停下,彷彿在等待著什麼。
陳瀅怔住了。
隨後,下意識便要向後退,以拉開間距。
然,此念方生,她忽如醍醐灌頂,陡然間明白了過來,一時直是啼笑皆非。
而再過一秒,這啼笑皆非,便也只剩下了笑。
原來,裴恕挨得這般近,是有著很恰切、很正當的理由的。
她忍笑湊上去,在那張大臉上用力親了一下,笑道:「是我的錯兒,沒想起來用這個表示感謝。」
語罷,又「啵、啵、啵」連親三記,笑著再續:「我自罰三親,以表誠意。」
裴恕頂著滴汗的紅臉直身,笑得眉眼都快挪位了。
從來只聽過自罰三杯,這自罰三親,他可是頭一回聽說。
媳婦兒真好,為了親他,連名目都想得如此周全。
裴恕樂滋滋地咧嘴。
被心愛的姑娘連著親了四口,真是再沒有比這更高興的事兒了。
他決定不洗臉了。
而後,他又決定還禮。
總不能白白叫人親了不是?
想他小侯爺縱橫四海,那可是很懂禮數的,若總這麼只取不予,成何體統?
心中是這般想的,他口中亦說了出來。
當然,有鑑於他此時的心跳、呼吸以及腦中思緒之混亂,他說出來的話,亦不能夠稱之為連貫。
「那個……那什麼……」他抬起空著的手擦汗,那汗卻越擦越多,如同他越來越結巴的語聲:「……阿瀅親都親……親了,我也得那什麼……所謂來而不往非禮也,我也得……聊表寸心。」
一壁說話,他一壁轉身,面朝著陳瀅站定,只是,視線卻不敢往下落,只得遠遠拋去前方,像對著漫天雨絲說話。
陳瀅笑看著他,深覺孺子可教。
這麼快就曉得回禮,可見小侯爺其實很聰明,身為導師,她還是欣慰的。
她唇角微翹,仰首、閉眼、踮腳,等待著他的唇落下。
最先落下的,是他的手臂。
很堅實、很有力的手臂,攬住了她的腰。
然後……陳瀅的腳就離了地。
並且,越離越高、越離越高。
待那高度達到陳瀅認為裴恕絕不可能吻上她時,她才終於覺出不對。
再一睜眼,卻見裴恕正咧著大嘴,那一口白牙,就在陳瀅的腰際。
他居然單手把她抱起來了!
饒是陳瀅有著舉世最聰明的腦瓜子,此際身在半空,還是有點發懵。
不是說還禮嗎?
她親了他一下,則他的還禮,不應該是親回來?
怎麼變成舉高高了?
她是不是在做夢?
然而,裴恕接下來的話語,卻讓陳瀅清醒地意識到,她沒做夢,這就是活生生的現實。
她確實被舉高高了。
還是單手舉的。
「我早就想這麼抱妳了。」裴恕笑得眼睛瞇成縫兒,攬在陳瀅腰際的手臂堅實如鐵,竟還有餘力抱著她上下掂幾掂:「上回妳抱我的時候,我就想著,也得好好抱妳一回。」
許是佳人在懷,他心情大好,說話竟也比方才流暢了些,唯獨那臉還很紅。
陳瀅怔望他幾秒,忍不住放聲大笑起來。
得學生如此,實乃人生一大樂事。
她決定不去糾正他了。
她倒要瞧瞧,這個情場經驗為負數的傢伙,還能整出什麼花樣兒來。
而看著陳瀅的笑臉,聽著她那如清溪躍動的笑聲,裴恕完全沒覺出半點不妥,反以為,此舉大大取悅了心上人。
他的白牙越發閃亮起來。
他決定以後沒事就舉個高兒,也好叫他的阿瀅歡歡喜喜地,就像他每天都歡喜一樣。
有鑑於兩個人想法出奇地一致,於是,這次浪漫的雨中漫步,便在這既甜蜜、又怪異的氛圍中落了幕。
其後的一路,裴恕用行動表明,他是言出必行的真漢子。
逮著空兒他就要這麼抱一回。
而陳瀅居然很賞臉,偶爾高興了,還會再親他幾下。
如此古怪的親暱模式,放眼整個大楚,恐怕也唯有陳瀅這個怪人,才會以如此方式回應。
若郎廷玉不曾力挽狂瀾的話,沒準兒裴恕能把這個保留項目,一直延續到洞房花燭夜。
好在,有「玉面飛熊」暗中指導,沒過多久,小侯爺終是幡然悔悟,也終於知曉,回禮不是這麼個回法。
而逐漸摸到竅門兒後,裴恕這個生瓜蛋子,終是懂得反客為主,由被動而主動,再由主動到殺得陳瀅丟盔卸甲,此皆後話,在此不提。
七月十七,回到京城的次日,暮煙秋雨又黃昏。
一身男式庶服、簡單易容過的陳瀅、裴恕等一行人,前往馬猴兒他們的住處問話。
老常將這群小青皮安置在了北城,那地方魚龍混雜、幫派雲集,充斥著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還有著以私自搭建的棚舍、木屋以及簡陋瓦房所構築而成的、如蛛網般九曲十八彎的地形,藏人極易,而尋人卻極難。
老常行事之老成,由此可見一斑。
「再往前走幾步就到了,陳大……陳爺。」趙仵作點頭哈腰地向陳瀅道。
說起來,這地方還是他介紹給老常的。他本就是土生土長的京城人,幹的又是仵作這行,北城這一帶他常來,久而久之,也就摸清了裡頭的門道,因聽說老常要找個不引人注意的住處,便向他推薦了這裡。
而今日引路,亦是因了趙仵作這地頭蛇的身分。
陳瀅轉首顧視,見他穿著一身灰夾短衫,亂糟糟的頭髮拿根布帶子綁著,矮小的身形,輔以精瘦的臉,瞧來倒像隻老鼠,雜在這嘈切的坊市間,竟是意外和諧。
她向趙仵作笑了笑,正待言聲,一旁的裴恕已然搶先開口:「好生帶路,少廢話!」
這一喝,氣勢迫人,趙仵作登時縮縮脖子,麻溜兒在前帶路,再不敢多說半個字。
他識得裴恕。
前番喬小弟殺人案時,就是裴恕領著一批皇城禁軍接替了他們,那張叫人膽寒的臉,即便隔了年許時光,亦叫人記憶猶新。
見裴恕滿身殺意,陳瀅輕碰了下他的衣袖,示意他放鬆。
今日來此,裴恕並不在陳瀅的計畫中。
她原打算單獨前往,然裴恕卻執意相從,只道城北混亂,不宜於女子獨行,即便易容改裝,亦有危險。
而今所見,正如裴恕之言,這地方的確很亂,就是個貧民窟,僅這一路行來,便遇見好幾個眼神不善、腰藏武器之人,更有幫眾子弟大搖大擺招搖過市,若陳瀅獨自前來,雖安全上不至於有問題,但很可能會碰上麻煩。
而她最希望避免的,正是麻煩。
「謝謝你與我同來。」陳瀅扯動裴恕衣袖,以口形比出這句話。
裴恕身上氣息一緩,亦向她笑了笑。
他也易了容,面上黏了片假鬚,著一身鷹背灰勁裝,戴著斗笠往那兒那麼一站,儼然便是江湖客、遊俠兒,那滿身匪氣天然便具偽裝作用,與這地界兒極為相合。
唯一的異類,大約便是陳瀅。
縱使她扮作小廝模樣,戴斗笠披針蓑,只是,她行止間那種冷靜淡然的味道,委實與身分相異。
所幸裴恕帶了幾名裴家軍,一個個提刀仗劍、凶狠剽悍,人數又頗多,便有那混混青皮,也斷不會沒長眼跑來惹事,路人更是有多遠躲多遠。是故,陳瀅這些許不同,也就不那麼引人注意了。
轉過兩條小街,便是一條窄巷,巷中破瓦房林立,間錯出無數岔路,卻是個四通八達的所在。
「就在這裡。」趙仵作恭恭敬敬地道,搶上前幾步,立在一所小院兒門前,拉起殘舊木門上鏽蝕的鐵環,輕叩了幾下。
「誰啊?」門裡傳來粗嘎的少年聲線,正是馬猴兒的聲音。
「我是你大爺。」趙仵作回以約好的切口,特意將聲音揚得很高:「你幾個叔伯來看你們了,快開門。」
「來了來了!」隨著話音,急促的腳步聲響起,旋即木扉開啟,馬猴兒的破鑼嗓子一下子湧了出來:「三叔你們怎麼才來啊,我都等你們好多天了,兄弟幾個都快沒吃的了……」
他熟練地嚎著對好的暗號兒,一面將眾人讓進院中,又機警探頭四顧。
時近黃昏,雨勢漸成,冷風捲起一幕幕水線,拋灑於瓦簷和地面,濺起大片碎珠,偶爾風疾,那雨便往人身上撲,順著蓑衣斗笠的縫隙鑽進去,不少人衣衫已然濕了。
這樣的時日,舉凡口中有食、身上有衣、溫飽可自顧的人家,是斷不會想著出門兒的,窩在乾燥溫暖的家裡,哪怕粗茶淡飯,亦比在外奔波強。
見巷中並無人跡,馬猴兒忙將門關牢。
而待木扉一合,那幾個裴家軍立時有序分散開來,將院子前後守住。
「守好,勿叫人靠近。」裴恕沉聲喝道。
眾兵卒齊齊應諾,雖聲音壓得極低,氣勢卻極盛,那屋中幾個小青皮已經看傻了。
此時,馬猴兒也終是認出易裝的陳瀅,忙快步上前見禮:「陳校長好。」
「進屋說話。」陳瀅輕聲道。
這院子左右皆有人家,防備些總不為過。
一行人進得屋中,另幾個少年在馬猴兒的督促下,盡皆過來見禮。
許是裴恕在側之故,小青皮們見禮後,便齊刷刷在東牆下站成一溜兒,束手束腳地,十分侷促。
陳瀅知道他們是被這群鐵血軍人給嚇住了,便溫言道:「我就是過來問幾個問題的,你們不必緊張。」又環顧四周,問:「湯秀才上吊那天,是誰負責盯他的梢的?」
「是豬頭。」馬猴兒飛快地道,伸手指向一個腦袋大、身骨兒細、眉眼透著精明的少年。
那渾號豬頭的少年下意識地一縮,旋即又挺了挺腰桿,強做出一副膽大的模樣來,道:「那天正……正是小的盯著湯秀才的。」
說完了,他便又往後退了兩步,似是要藉著人群把自己隱去,時不時偷看裴恕一眼,蒼白的臉上,浮起濃濃畏懼。
若單看樣貌,裴恕絕對稱不上凶惡,至少比豬頭所知的濟南城「鐵刀門」門主差上許多,且那門主的身板兒也遠比裴恕壯,手裡的刀子更是亮得怕人。
可偏偏地,豬頭就是怕。
雖面貌不算打眼,可面前男子五官冷厲、神情淡漠,只隨隨便便站在那裡,不必亮刀子、也不必亮身板兒,周身便散發出一股子冷氣,凍得人腳底打晃兒,恨不能趕快跑遠才好。
「好了,那就豬頭和小猴兒留下吧。」陳瀅此時笑道,又走過去拍拍馬猴兒的腦袋:「辛苦你們了。」
馬猴兒與她相熟些,加之見多識廣,此際倒未顯得害怕,唯神情有些沮喪,垮著臉、塌著肩,小聲兒道:「陳校長,小的把差事辦砸了。」
他低了頭,語中滿是懊惱與悔恨:「都怨小的沒把人盯牢,不知怎麼的他居然就死了,要不是那木器行的夥計上門兒送貨,叫破了這事兒,小的怕還要在外頭白盯著呢。」
他越說聲音越小,心底裡極為自責。
湯秀才雖是上吊死的,那也是他們沒提前發現苗頭,竟不知他要尋死。身為這群人的頭兒,馬猴兒自覺罪責重大。
他記得葉統領說過,如果一隊人犯了錯,那頭兒就得擔下來,這叫「擔當」。如今湯秀才既死,則他就得擔下這盯梢不力的錯兒來,不能怪別人。
「你們已經盡力了,做這些也委實為難你們。」陳瀅和聲道。
一群沒接受過專業訓練的半大小子,千里迢迢跟著湯秀才進京,這一路都沒把人跟丟,且還將其近期動向摸得一清二楚,這已然是超水準發揮了,她對他們,並無苛責之意。
見陳瀅始終態度柔和,馬猴兒多少放下些心來,摸著後腦勺兒道:「校長不怪罪小的就好。」
陳瀅擺擺手,拉他與豬頭分別坐了,略過這話題,當先便問豬頭道:「湯秀才上吊那天都做了些什麼,你仔細說給我聽聽。」
「好生說,莫要有遺漏。」裴恕在旁補充道。
很沉的聲音,聽在陳瀅耳中,是醇酒低弦,然豬頭聽了,心底更慌。
這黑臉大漢本就怪嚇人的,如今這話聽來越發像是威脅,由不得他不緊張。
「是……是,陳校長。」豬頭乾嚥了口唾沫道,喉嚨又澀又癢,舌頭也不大利索了:「俺……我……我就是那天盯著湯秀才來著,俺……」
「你慢慢說,別怕。」陳瀅柔聲道,自袖中取出個小紙包兒來,打開了,卻原來裡頭裝著幾粒松子糖:「吃塊糖,甜食有助於平穩心情。」
豬頭半懂不懂地聽著,心思壓根兒就被那糖給引過去了,伸手欲取,又縮回,怯怯地看了裴恕一眼。
「吃吧吃吧,陳校長人可好了。」馬猴兒到底見過些世面,雖也覺著裴恕嚇人,卻沒那麼害怕,拿了塊糖塞進豬頭嘴裡。
陳瀅便將整包糖都遞了過去,溫笑道:「都拿著罷,我還帶了好些吃的,等一會說完了話再給你們。」
豬頭將糖塊兒含在嘴裡,那甜絲絲、冰冰涼的口感,立時便攫去他全部的注意力。他瞇眼感受著,倒真把裴恕給忘了。
馬猴兒見他只顧著吃,便虎下臉,胳膊肘用力捅了捅他:「快說,陳校長還等著呢。」
豬頭這才回過神來,一面吸溜吸溜地吃糖,一面便道:「那天快中晌的時候,湯秀才出門兒,小的悄悄跟在他後頭,一直跟到城南銅鑼巷,那巷子裡有家熱湯麵館兒,湯秀才有時候會過去吃湯麵。」
「他去的時間有規律麼?」陳瀅插口問道,怕他聽不懂,又解釋道:「我的意思是,他一般隔幾天去一次?」
豬頭呆了呆,馬猴兒倒是答得很快:「小的記得湯秀才去的日子不定,有時候隔兩、三天,有時候隔個五、六天。」
「你確定麼?」陳瀅略有些懷疑。
不是她不相信馬猴兒,委實是覺著,以這小傢伙識得的那幾個字,怕是無法記下如此繁複的訊息。
馬猴兒便笑嘻嘻地道:「小的記著這事兒呢。葉統領給了小的幾張黃曆紙,小的每天都在上頭做記號兒來著。」
「黃曆紙?」陳瀅怔了怔,旋即心頭一喜,忙問:「是女校特製的那種黃曆麼?」
馬猴兒立時點頭:「回陳校長,就是那種黃曆紙,葉統領給了小的半年的黃曆,又教小的識數兒和認字兒,小的就在上頭畫記號記事兒。」
陳瀅欣然頷首:「這法子很好,你很聰明。」
馬猴兒所說的黃曆紙,其實是女校特製的月曆,一個月一張,與現代的桌曆相仿。
原先,陳瀅將之作記事用,後眾人見其簡便,便也都跟著學,一來二去,簡易版月曆就此在女校流行開來,葉青那裡也有幾份。
「葉統領告訴小的說,好記性不如爛筆頭兒,記在紙上比記在腦子裡更穩當,小的便照做啦。」馬猴兒比劃著道,又張大眼睛問:「小的這就把那黃曆紙拿來給您瞧瞧?」
「好,快拿來給我看看。」陳瀅笑道。
有這份東西,對於湯秀才這段時間的去向,便會有個直觀的感受。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出閨閣記(九)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05 |
華文羅曼史 |
$ 205 |
華文小說 |
$ 205 |
大眾文學 |
$ 205 |
Literature & Fiction |
$ 221 |
古代小說 |
$ 221 |
小說/文學 |
$ 234 |
中文書 |
$ 234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出閨閣記(九)
陳瀅怎麼也沒有想到,
那令人毫無頭緒的證物珠釵,
竟是從她意想不到的人口中,得到了線索。
一旦線頭冒出,要尋著線索往下查,就簡單多了。
只是,當事關皇家祕辛,
就註定不可能只是單純的辦案與查明真相。
當跋扈的長公主當年曾密謀康王之事被翻出,
註定了這曾經的京城第一貴婦的覆滅,
連帶著,許多圍繞在長公主府與興濟伯府之間的謎團,
也被一一揭開,真相大白。
只是,當事情最終指向她的摯友──
真相與正義,惡人惡行與無辜者的生命,孰重?孰輕?
陳瀅找不出答案。
商品特色
《庶庶得正》作者姚霽珊,又一部古裝推理宅鬥作品。
纏繞延宕多時的案情,曙光乍現!
謎題易解。可是,解開又如何?
如果探求真相的代價,是讓更多人萬劫不復,那麼,她放棄。
作者簡介:
姚霽珊,金陵人士,坐望六朝煙水間,汲泉煮字、搗文成衣,文字細膩優美,擅寫景抒情,散文及小說見諸各雜誌報刊,曾出版作品《至媚紅顏》、《一花盛開一世界,一生相思為一人》、《世間女子最相思》、《願你已放下、常駐光陰中》,現為閱文集團簽約寫手,著有長篇小說《庶庶得正》、《折錦春》等。
章節試閱
第一章
裴恕脖根兒都紅了,好似那心尖尖也被這纖指撩著,跳得擂鼓也似,嗓子眼兒幾乎冒煙。
可偏偏地,那冒出來的煙卻又甜得很,彷彿那飄進傘下的細雨,也是糖水兒化出來的。
他紅著臉往四下瞧,又侷促、又歡喜、又有幾分不安。
見他已然不好意思到了極致,陳瀅亦覺心虛。
在男女之事上,她的經驗比他多了太多,總這樣戲弄他,似乎也不太好。再者說,當導師縱然有趣,只學生面皮太薄,卻也教她心軟,不忍繼續。
所以,她打算適可而止。
她故意抬頭,看向傘外灰暗的天空,給出空間,由他自己轉過來。
雨下得不疾不緩,青布傘面兒上...
裴恕脖根兒都紅了,好似那心尖尖也被這纖指撩著,跳得擂鼓也似,嗓子眼兒幾乎冒煙。
可偏偏地,那冒出來的煙卻又甜得很,彷彿那飄進傘下的細雨,也是糖水兒化出來的。
他紅著臉往四下瞧,又侷促、又歡喜、又有幾分不安。
見他已然不好意思到了極致,陳瀅亦覺心虛。
在男女之事上,她的經驗比他多了太多,總這樣戲弄他,似乎也不太好。再者說,當導師縱然有趣,只學生面皮太薄,卻也教她心軟,不忍繼續。
所以,她打算適可而止。
她故意抬頭,看向傘外灰暗的天空,給出空間,由他自己轉過來。
雨下得不疾不緩,青布傘面兒上...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