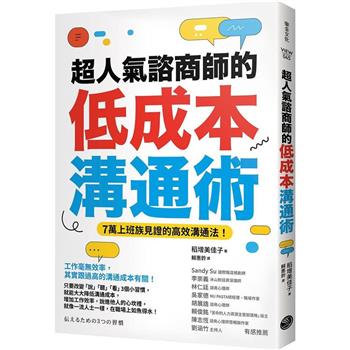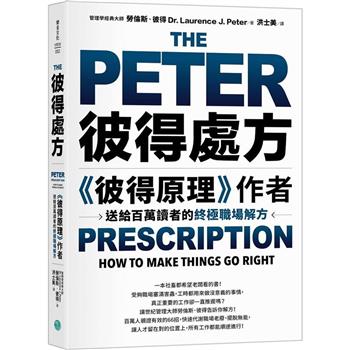第三十一章
尤明許一回湘城,就陷入了鋪天蓋地的工作裡。
這次的案件,有大量的後續工作,足夠忙一兩個月。他們組現在兵力空虛,很多案子她也要幫忙,於是頭一個星期,她幾乎把一切都拋在腦後,忙得氣都喘不過來。直至夜深人靜時,終於可以休息,想起殷逢,但一看時間,他肯定已經睡了。
尤明許也不是黏黏糊糊的性子,以前和尤英俊好時,也是他天天追著她。所以她也不太給他發簡訊說什麼肉麻的話。
顯然,如今的殷逢,也是和她差不多的性子。
到了這週六的晚上,尤明許第二天終於可以睡個懶覺,才想起來一個星期了,兩個人也沒聯絡過,殷逢連簡訊都沒給她發一則。
哪怕他還下不了床,這也不太正常。
尤明許想起離開貴州時殷逢彆扭的樣子,她也百思不得其解,到底是為了什麼。想來想去可能還是因為老九的犧牲,他心裡自責愧疚,連帶著不想面對她?
深夜裡,尤明許靠在床頭,想了一會兒,笑了。
決定等他自己想通。
「要是哪天妳離開了,我真不知道自己會幹出什麼。」
有這句話,她心裡就是踏實的。
過了兩個星期,尤明許手裡的工作總算沒那麼多了。她有了閒置時間,就得去查某一件案子。
一件十五年前,在她十歲那年發生的案子。
尤明許斟酌了半天,決定先請丁雄偉喝頓酒。他曾經是母親的同事,她一直是知道的。
這天下了班,兩人進了家餐廳的包廂,尤明許把菜單遞給丁雄偉,他向來強勢,也不推辭,點了幾個菜,尤明許又給他倒了茶。
丁雄偉面色如常地喝了幾口,說:「這頓我來,算是犒勞。」
尤明許當然不會跟錢過不去,乾脆地答:「好。」
丁雄偉笑了笑,說:「怎麼想到請我吃飯了?俗話說得好,有了媳婦忘了娘,咱們隊裡,個個都這樣。」
尤明許手裡捏著個杯子,慢條斯理地說:「我有了媳婦,也沒忘了您啊。好久沒跟您聯絡感情了,吃個飯不行啊?」
丁雄偉說:「有屁快放。」
尤明許笑了一下,正色道:「老丁,我想知道……關於媽媽的事。」
丁雄偉又喝了口茶,並沒有露出什麼意外的神色。
尤明許被懲罰者劫持那一段路,殷塵說的話,她一五一十全都寫進了報告裡,沒有半句隱瞞。報告交上去後,上面一點動靜都沒有。
丁雄偉嘆了口氣,說:「具體想知道什麼?」
尤明許說:「她和邢几復、殷塵的關係。還有她殉職的那起連環案件。」
丁雄偉說:「妳是不是挺奇怪的,她如果和那兩個犯罪分子有關係,為什麼還可以做員警,妳還可以做員警?」
尤明許沒吭聲,一雙冷清的眼直視著他。
丁雄偉看懂了她的眼神,笑了,點頭,嗓音柔和了幾分:「妳想的沒錯。妳的母親,她沒有做錯任何事。她是個優秀的員警,從始至終都是。」
尤明許的心一下子放了下來。
丁雄偉卻陷入了沉思,說:「其實當年的事,我也只知道個大概。但殷塵也和當年的事有關,我還是第一次聽說。」
那已經是很多年前了。
那時候,丁雄偉才二十多歲,和尤明許的母親──尤蕤雪一樣,是警隊新人,兩人在同一個隊裡,關係還不錯。
丁雄偉還記得尤蕤雪的性格,可沒有尤明許這麼囂張,她是個沉靜柔和的性子,但也很聰明,骨子裡那股傲勁兒,和尤明許是一樣的。相貌也比尤明許甜美一些。
這樣一個女警,局裡自然很多人追。丁雄偉當時都有點動心思,但是不太敢。只不過尤蕤雪明顯是個眼光高的,連局草──某位英俊瀟灑的副隊長,都婉拒了。於是像丁雄偉這樣的普通人,也就默默歇了心思。
局裡有一組人,開始打擊區裡的涉黑犯罪行為。那時候,還沒有凱陽集團,只有幾個犯罪集團,引起了員警的注意。
尤蕤雪也加入了工作組。
丁雄偉不在工作組裡,大部分的事,都是聽其他人說的。
聽說尤蕤雪一開始,是和個不相關的人談戀愛了。美國留學回來的高材生,商家之子,俊秀文雅,兩個人感情很好。
而局裡的打擊犯罪行為,一直在按部就班推進。
後來有一段時間,丁雄偉注意到,尤蕤雪的臉色一直不太好,有一次大家聚餐時,尤蕤雪突然乾嘔,臉色很難看。當時大家面面相覷。
又過了幾天,上級把尤蕤雪叫進辦公室,兩人說了一個小時,尤蕤雪出來了。第二天,她就從掃黑工作組調離,回到普通刑事崗位。
那時候,儘管有各種傳言,但到底已經九幾年了,人們的思想也都開放了,頂多背後說幾句,也就算了。
丁雄偉聽說,尤蕤雪男朋友有急事回了美國,才留下她一個人。也有人說她是被拋棄,有人說她被騙了。但那時候,丁雄偉就自認為是個不會偏聽偏信、耳聰目明的人,他甚至還暗中打量過,發現明顯懷了孕的尤蕤雪神色平和,眼中有光。於是丁雄偉斷定,人家和男朋友說不定好著呢,只怕那人是被什麼耽擱了,一時回不來。
那麼,既然尤蕤雪是丁雄偉這樣的菜鳥青年心中的女神,他自然也盼著女神能夠幸福。
但直到尤蕤雪請了假據說去生孩子了,也沒見那人回來。
丁雄偉再見尤蕤雪,已是兩年後。
在下面的一個小派出所。
聽說她是自請調離的。
可再見到她,丁雄偉發覺,她還是曾經那個模樣。儘管是警校高材生、員警世家出身,從分局最吃香前途無量的重案組,貶至了一個偏僻的派出所,可她看起來依然那麼寧靜溫和,傲骨內斂。只是眉宇間,似乎添了幾分初為人母的柔和光彩。
丁雄偉因為公務,和她說了幾句話,就聽到她接到也許是家裡打來的電話。
「嗯……寶寶又發燒了?」她的眉頭焦急地皺起來,「媽我實在回不去,到四醫院,兒科比較好。我明天休息就坐車回去……」
丁雄偉當時什麼也沒問。
等尤蕤雪掛了電話,眉眼間有愁色,但是很快恢復平靜。
丁雄偉說完工作,又加了一句:「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可以給我打電話。」
尤蕤雪笑著說謝謝。
但後來無論她遇到什麼,也沒有打電話和曾經的同事求助過。
後來的事,丁雄偉還是聽別人說的。
聽說尤蕤雪雖然去了基層,可是一步一個腳印,越幹越好,很快又得到重用,加入了另一個區的刑警隊。
聽說她一直沒有結婚。
還聽說,她和某個黑幫組織的小兒子,有著說不清的關係。傳言有鼻子有眼,說那小兒子本是國外留學回來,根本不沾家裡的事,也沒跟她提自己的身分。她也是被騙了,那個孩子,就是跟那人生的。
結果後來出了一連串的變故,那小兒子不得不接班。而且他身為書生,居然十分了得,傳言他以鐵血手腕,把對頭全都收拾了,還收拾得特別漂亮,後來警方重拳出擊時,那些對頭全都證據確鑿,反倒是小兒子手裡,抓著的只是房地產、金融公司這些乾乾淨淨的生意,一點事沒有。
但都是隻言片語的傳言而已。畢竟尤蕤雪多年來始終獨來獨往,而那小兒子已經進軍實業,結婚生子,生意越做越大。怎麼看,兩人都是八竿子打不著的,離得很遠很遠。
……
「妳媽媽那些年,挺不容易的。」丁雄偉嘆息。
在尤明許的記憶裡,童年雖然和外祖父母住在一起,但母親只要有時間,都會從湘城去江城看她。母親總是溫和的、平靜的,對她有無盡的愛,從未表現出任何不甘和埋怨。這也是尤明許第一次聽人提及,那些年,母親過著的,是一種怎樣的生活。謠言、懷疑、謊言、背叛、對立……
尤明許忽然就不再想要知道,母親和那個人之間,當年是真心還是欺騙;母親是否會後悔。
已經不重要了。
母親其實已經給了她答案。
兩個答案。
一個答案,是直至殉職,母親都是一名最稱職的員警,克己奉公,勤勤懇懇,立下許多不會被磨滅的功勞。
另一個答案,是母親對於她來到這個世界,沒有任何後悔和怨言,她對她傾注了一個母親全部的愛,並且也影響她,繼承母業,成為了一名員警。
尤明許眼眶一熱,垂下眼眸,喝茶遮掩。
丁雄偉看著她的神色,沉默了一會兒,說:「有關這件事,還想知道什麼嗎?」
尤明許答:「不用了。」她長吐了口氣,語氣淡然下來:「說說殷塵吧。」
丁雄偉皺眉:「殷塵……我知道的,不比妳多。當年,誰也沒注意到這號人。我不知道他是怎麼認識妳媽媽的。後來妳媽媽殉職的那個案子,我記得檔案裡,也沒有殷塵這個人。」
尤明許沉思了一下,說:「我要看當年的卷宗。」
殷塵既然提到了,邢几復也說過,殷塵是「當年纏著她的那個小子」,也許從那個案子裡,能找到什麼蛛絲馬跡。
丁雄偉答應了。
這天下午,一疊厚厚的、紙頁已經發黃的卷宗,到了尤明許手裡。
一盞柔和的檯燈下,尤明許獨坐在辦公室裡,翻著卷宗。
她也算是見過世面,經手過不少殘忍可怖的案件。但當她看到十五年前那起連環殺人案的現場照片時,還是會有噁心難受的感覺。
五次做案,五名受害者,四死一傷。尤蕤雪就是在最後一起案件裡犧牲,救下了那名受害者。
做案時間大致分布在半年內。凶手於深夜跟蹤、襲擊單身女性。那個年代,監控攝影機很少,雖然面臨經濟快速發展,城市裡荒地、空地、工地也很多。
凶手將受害者拖至無人處,性侵後勒死,以刀具重創性器官,並割下乳頭帶走。尤明許看了幾張照片,長吐了口氣,很不舒服。
受害者有的只有二十多歲,是單身女性;也有三十多歲,已經結婚生子的。孩子當年才一兩歲,就失去了母親。
凶手名叫許霸坪,是個二十多歲的青年。
警方在兩起犯罪現場發現了他的指紋和精液,有目擊者看到他在一起案發現場出現過。
還有一項非常有力的證據,是在某個銀行分理處門口的監視器,拍到了他尾隨一名受害者的畫面。
但是當警方確認這名重大嫌疑人的身分,實施抓捕時,他已潛逃至鄉下。於是警方發布通緝令,並調集大量警力,展開搜查。
大概十多天後,正是尤蕤雪所在的小組,發現了許霸坪的蹤跡。只是當支援警力趕到時,所發生的事,令所有人震驚。
從現場痕跡看,尤蕤雪和另一名員警,與許霸坪發生激烈搏鬥,尤蕤雪當場犧牲,另一名員警重傷。但另一名鄉村女孩和她的母親,活了下來。按照她們的口供,許霸坪當時情緒非常激動,拒不認罪,並試圖劫持母女倆。正是為了救她們,尤蕤雪意外犧牲,許霸坪逃走。
但這時,許霸坪已是窮途末路。
兩天後,警方就在山裡找到了許霸坪。
但他已經是一具屍體。
而且是一具面目全非、非常可怖的屍體。
他被剝了皮。而且是活剝的。
連環凶殺案,算是破了。
但許霸坪被殺的案子,這些年卻始終沒破,因為警方找不到這樣一個有動機、有做案時間的嫌疑人。那些受害者的家屬都排除了嫌疑,有動機,但是沒有時間和能力,所以這起案中案,就一直懸了下來。
尤明許合上卷宗,默坐了一會兒。
證據非常充足,許霸坪應該就是連環案的真凶。
她也知道虐殺許霸坪的凶手是誰,那人親口說過。
而現在,殷塵在逃,那人也不知所蹤,不知道是否還活在世上,還是正受盡折磨。
但是尤明許把所有涉及案件的相關人員都捋了一遍,沒有發現任何和殷塵有關的線索。
難道說,殷塵和這起案子沒有關係?
那他又是怎麼認識母親,「纏」著母親的?
時間隔得太久,母親當年又獨來獨往獨住,要查下去,只怕不容易。
尤明許蹙眉想了一會兒,放下卷宗,一口吃不成個胖子,只能慢慢來了。
她看了眼時間,夜裡九點多,算是這些天以來工作結束得很早的時間了。
想了想,她給殷逢發了則簡訊:「睡了嗎?」
過了大概一兩分鐘,她都把桌面收拾好了,才收到回覆:「沒有。妳在幹什麼?」
這些天他不聞不問不聯繫,尤明許雖然也沒空,心裡到底是有點不舒服的。只是此時看到他發過來的話,心裡才柔軟了幾分,索性直接打了個視訊過去。
兩人都到這個分上了,現在打個電話,聽著「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等待接聽的聲音,尤明許居然有幾分不自在。
他接起了。
畫面裡出現天花板,病床,繃帶,病人服。殷逢坐在床上,靜靜望著她。
尤明許一時也不說話,只是仔細打量著他。臉色看起來似乎好多了,頭髮也乾乾淨淨的,臉還是瘦,因為纏著繃帶要換藥,沒穿衣服,只是披了件病人服在肩上,露出肩膀和胸口。
他的眼神還是那樣,深深暗暗的,沒有半點溫和可愛,似乎也在打量她。
還沒等她開口,他先說話了:「瘦了。」
尤明許愣了愣,說:「最近太忙了。你能坐起來了?」她有些高興。
殷逢很冷地哼了一聲,說:「一個星期前就能起來了。」
尤明許盯了他兩眼,淡道:「厲害啊。」
他接得很順口:「那是當然!」
尤明許就忍不住笑了,眼眸盈盈。
殷逢看了她一會兒,倒是沒笑,人又往下靠了靠,倒是顯得慵懶了幾分。
他說:「妳都在忙什麼?」
尤明許就把這些天的工作大概說了說,想起剛才看的卷宗,也一併和他說了。
殷逢沉思了一會兒,說:「掃描一份給我。」
「行。」尤明許說,「當年的案情算是很明朗,只是不知道……你覺得殷塵到底是從哪兒冒出來的?」
殷逢答:「當年他才二十多歲,大學畢業不久,比……伯母還小了七八歲,在我的記憶裡,他那時候還比較正常,只是過得不太好。懲罰者組織,那時候他也沒有能力創建。我想或許是和伯母有關的什麼事,那起案子,給他帶來比較大的精神衝擊甚至創傷,所以他到現在還念念不忘,復仇、懲罰的善惡觀,或許也是從那時就開始積累成型的。」
尤明許其實也有相同的感覺,其中肯定還有隱情。甚至她想,會不會正是母親的因公殉職,才讓殷塵不再信任司法,決意成為懲罰者呢?
當然她也只是想想而已。
殷逢問:「妳有什麼打算?」
尤明許搖搖頭:「不好查,我會再想想辦法。如果殷塵真像你說的,會再現身,最好是從他身上入手。」
「嗯。」
兩人都靜了一會兒,尤明許感覺已無話可說,就說:「那你早點休息,有事給我電話。」
他盯著她,眸色難辨。
尤明許:「怎麼了?」
他沉默了幾秒鐘,說:「妳急著去幹什麼?」嘴角露出譏誚的笑。
尤明許:「……我什麼時候急了?打算下班回家。」
「回家幹什麼?」
「宵夜,睡覺!」
殷逢又問:「吃什麼宵夜?」
尤明許早已覺出味兒來,臉上就帶了似有似無的笑,答:「隨便點些外賣。你呢?今天吃了什麼?」
他不緊不慢把中飯、晚飯的菜都說了。
尤明許又問了他的病情,還有多久康復。他也一一答了,說恢復得還可以,大概還有兩個星期就能下床,只是不能劇烈運動。
尤明許心裡有股甜甜脹脹的情緒在無聲流動,又問:「那你打算什麼時候回湘城?」
他也只是盯著她,眸光幽幽,答:「再過一兩個星期吧。」
尤明許想了想,說:「不要一個星期就回來,還是等好全了,再動。」
殷逢說:「我自己有數。」
尤明許又想到了另一個話題,問:「塗鴉、小燕、景平、夢山都怎麼樣?」
其實那幾個人的情形,許夢山經常發簡訊跟她說,據說康復得都很快,所以尤明許都沒有細問。
殷逢沉默了一下。
尤明許:「怎麼了?」
殷逢的語氣淡得很:「他們都下床了。滿意了嗎?」
尤明許差點笑出聲,努力忍住,心念一動,放軟聲音說:「那是因為他們的傷都沒你重。你不要急著下床,我想你恢復得更好一點。」
兩人對視片刻,他的神色不知何時已徹底柔和下來,那目光直勾勾的,竟令尤明許又不自在了。
他把手機移得離自己近了一些,問:「有沒有想我?」
尤明許還真的沒怎麼想,實在是沒有時間精力。
她立刻反問:「你呢?想我沒有?」
他答:「如果妳不是個員警,現在早被我鎖起來了。」
他講得平平靜靜,尤明許卻心頭一跳,心想,又陰陽怪氣上了。她淡道:「你少把那套用我身上。我看這麼多天,我不主動給你電話,你也沒找我。看來你真的是很想。」
殷逢冷笑一聲,說:「那妳找過我嗎?兩個星期了,我在住院,妳到今天才想起我?」
尤明許盯著他,心想我到底在和他幹什麼?為什麼在爭這種事?
一想不對啊,他雖然住院,整天躺著,他才是閒的那個啊。尤明許斬釘截鐵地說:「不對。我忙天忙地,這幾天都是半夜才睡,那時候你早就睡了。天一亮我就忙著上班,有時候飯都顧不上吃。你整天在忙什麼?忙著打點滴嗎?忙著讓陳楓給你餵飯嗎?你為什麼不找我?」
殷逢不說話了。
|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待我有罪時(4完)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待我有罪時(4完)
鬼門關前走一遭,醒來的殷逢又有些不同。
那些彆扭,看在尤明許眼中,只覺「可愛」,
殷作家似乎越來越愛撒嬌,尤姐卻是吃軟不吃硬,
他一直記不起曾說過的話,做起來倒是毫不含糊,
她,還要繼續等下去嗎?
尤明許母親當年因公殉職,十五年後,
明韜作為殺手學徒,複製同一樁刑案,
手法青出於藍,卻被迅速「處理」。
明韜明顯只是引子,有殷塵女友蘇子懿這個「共犯」,
加上受害者指認,殷逢這個綁架主謀板上釘釘,
連尤明許都被牽連繳槍,她要如何替殷逢洗脫罪名?
本書收錄番外〈本應是一對〉、以及實體書番外〈寶寶的一天〉、〈簽售〉(《他來了,請閉眼》聯合番外)。
作者簡介:
丁墨,生於湘地,曾經南北漂泊,如今定居長沙。
喜愛編織刺激又甜寵的愛情故事,遊走於懸疑、科幻、商戰等多個領域。每一次寫作,都是懷抱理想主義的現實征戰。
中國作協成員,女性網路文學著名白金大神。曾獲茅盾文學獎網路文學新人提名,2017年度IP影響力作者、年度十大讀書影響力大V。並入選中國作協年度十大網路文學作品排行榜。
章節試閱
第三十一章
尤明許一回湘城,就陷入了鋪天蓋地的工作裡。
這次的案件,有大量的後續工作,足夠忙一兩個月。他們組現在兵力空虛,很多案子她也要幫忙,於是頭一個星期,她幾乎把一切都拋在腦後,忙得氣都喘不過來。直至夜深人靜時,終於可以休息,想起殷逢,但一看時間,他肯定已經睡了。
尤明許也不是黏黏糊糊的性子,以前和尤英俊好時,也是他天天追著她。所以她也不太給他發簡訊說什麼肉麻的話。
顯然,如今的殷逢,也是和她差不多的性子。
到了這週六的晚上,尤明許第二天終於可以睡個懶覺,才想起來一個星期了,兩個人也沒聯絡過...
尤明許一回湘城,就陷入了鋪天蓋地的工作裡。
這次的案件,有大量的後續工作,足夠忙一兩個月。他們組現在兵力空虛,很多案子她也要幫忙,於是頭一個星期,她幾乎把一切都拋在腦後,忙得氣都喘不過來。直至夜深人靜時,終於可以休息,想起殷逢,但一看時間,他肯定已經睡了。
尤明許也不是黏黏糊糊的性子,以前和尤英俊好時,也是他天天追著她。所以她也不太給他發簡訊說什麼肉麻的話。
顯然,如今的殷逢,也是和她差不多的性子。
到了這週六的晚上,尤明許第二天終於可以睡個懶覺,才想起來一個星期了,兩個人也沒聯絡過...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