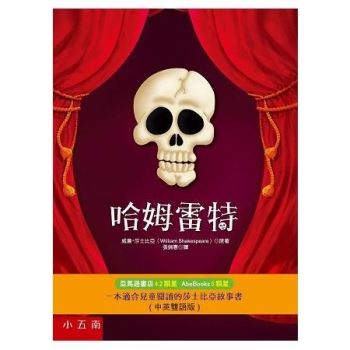十年等待,《知否》作者最新力作!
改編電視劇已殺青!!
曾經的小太妹穿越重生成將軍的「嫋嫋」嫡女?!
既已注定得走這一遭,她自是要奮力自在活著!
改編電視劇已殺青!!
曾經的小太妹穿越重生成將軍的「嫋嫋」嫡女?!
既已注定得走這一遭,她自是要奮力自在活著!
預備役小太妹迷途知返,好不容易走回人生正途,
怎料因一次見義勇為,竟穿越至她難以辨識的古代,
重生成了個正病病殃殃的……小女公子?!
且原身處境大大不妙──
雙親遠走十年,同住的叔母故意輕怠教養,
小姑娘程少商「粗鄙蠻橫」的惡名遠揚。
但沒關係,憑她靈活的腦袋與過去的「人生歷練」,
想活出一條路來,想來不是難事……
程氏夫妻突然歸來,令程少商意外的是,
老爹程始實則愛女逾恆,聲聲「嫋嫋」難掩疼愛之情。
娘親蕭夫人戰鬥力滿分,收拾虧待女兒的人毫不手軟,
但對她這個「目不識丁」、「桀驁不馴」的女兒,
卻是怎麼也看不過眼……
罷了,對早有成見之人,何必費力討好?
沒心沒肺才能無所顧忌。
她要的是能自在自立,不被拘於一方,坐困愁城!
本書特色
◎華文知名經典《知否》作者,睽違十年最新力作!
◎一注孤勇,令人心悸,她見義勇為,卻穿越重生,成為叛逆的將軍嫡女──
◎無論前世今生,她與父母都是緣淺,不過就是重歷坎坷童年嘛……這回,她也能再次打開一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