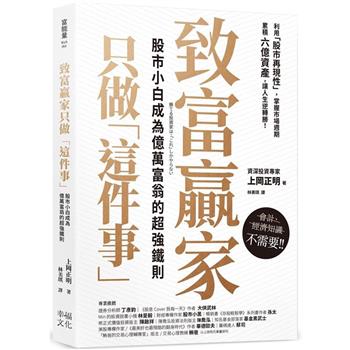縱使程少商步步為營,麻煩依舊紛至沓來,
最後連栽贓誣陷、害人性命的事也安到了她頭上。
但這些都不是讓她覺得最棘手的,而是──
自己似攤上了個敏感易怒又熱衷於胡思亂想的未婚夫?
「我覺得,她對我用情還沒那麼深。」
「妳畏懼我,顧忌我,還要提防我!」
「在妳心中,我究竟算什麼?」
這個「如何待凌不疑好」的難題,她何時才能及格啊?
幾番衝突後,凌不疑的悽愴、怨懟,
終教少商正視自己不願承認的心意。
一方本著「有過就改」的正向態度,
另一方則有皇帝為養子「助攻」,
一招「苦肉計」,讓程少商與凌不疑的感情更進一步。
正當兩情繾綣之際,忽爆出太子舊愛殺夫一案,
而太子竟也被牽連其中!
皇后與太子向來待兩人親厚,他倆又豈能置身事外?
本書特色
一人獨行,怎及兩情繾綣?
她當他是天上明月不可親,他卻要教她看盡他有血有肉的一面。
不須再說什麼自在、束縛,重要的是這個男人值得她好好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