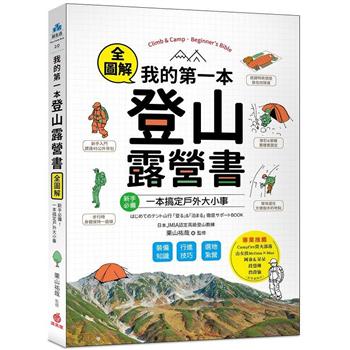第一章
杜庭蘭望著窗外,天色不早了,紅奴遲遲沒有回來。
不知紅奴見沒見到盧兆安?進士宴開筵在即,再晚她就別想當面跟盧兆安對質了。
一想到盧兆安,杜庭蘭心裡就油煎似的難過,這半個月他避而不見,害她悒怏成疾,她現在有一肚子的話要問他,只恨此人連當面對質的擔當都沒有。
不能再等下去了。杜庭蘭起身悄然打量四周,母親在西苑戲場看百戲,女眷們大多去了園子賞花,四下裡無人,正是離庵的好時機。
杜庭蘭咬了咬唇,剛要放下手中的繡剪,廊下忽然傳來說笑聲。
「今年明經科取了百餘人,進士科卻只有區區二十人,聽說年紀都不小了,大半已婚配,最老的進士五十有餘,膝下兒女都比阿婉年長。」有位夫人道。
「就是。」另一位夫人輕笑,「想不到葛家為了給女兒挑夫婿,竟將主意打到老叟頭上。」
「其實不怪葛家今年如此上心,妳們頭幾日在東都,不知道這次進士科拔頭籌的是位才二十出頭的公子,此人名喚盧兆安,作得一手好詩文,人也生得丰神俊朗,有意婚配的何止葛家,好些名公巨卿都在打聽這位盧進士。」
杜庭蘭隔著半捲珠簾,聽到「盧兆安」這三個字覺得無比刺耳。杜庭蘭心裡彷彿激起了巨浪,一時竟忘了手中還握著繡剪。
「但昨夜我聽我家二郎說,放榜那日尚書省的鄭僕射聽說盧兆安拔得頭籌,早把他叫到跟前問話,假如盧公子在揚州沒有婚配,鄭僕射多半要延媒議親了。」
這話顯然讓人吃驚不小,另一位夫人道:「盧公子一舉成名天下知,滎陽鄭氏更是百年望族,說起來倒是一樁良緣。既是宰相親自問話,盧公子怎麼回的?」
「盧公子說他尚未婚配。」
杜庭蘭臉上血色瞬間褪了個一乾二淨,不過數月工夫,此人竟將和她的關係一筆勾銷。
皎日之誓,言猶在耳,當初有多讓她心馳神蕩,此刻就有多諷刺。
珠簾外人影綽綽,眼看有人要進屋,杜庭蘭勉強支著胳膊欲起身,忽覺掌心一陣溼熱,低頭才發現被剪子劃出了一道口子,血珠湧出,紅得驚心刺目。
杜庭蘭喪魂落魄地望著那片模糊的紅色,如今只後悔當初為何要擅自去揚州城外踏青,若沒有桃花林中那場邂逅,怎有今日之辱?!
「娘子!」傷口突然被人用帕子死死按住,杜庭蘭木然抬頭,原來是丫鬟紅奴回來了。
杜庭蘭心中針扎似地疼,剛才她盼著丫鬟把話帶給盧兆安,現下想起那人就要作嘔。
紅奴急急忙忙檢視完傷口,拿出一件物事低聲道:「盧公子讓奴把這個帶給娘子,說要娘子去月燈閣外的竹林見他。」
杜庭蘭冷笑一聲,奪過那彩勝(彩勝:又稱旛勝。唐宋時代,每逢立春日,會剪紙或綢作「旛」戴在頭上或繫在花下,以慶祝春日來臨。)要撕爛,奈何手指顫動,撕了一下沒撕動,反讓手掌的傷口再次迸開了。
◎
滕玉意掀簾邁入屋內,驚訝道:「咦,表姊不在此處?」
沙彌尼(沙彌尼:未滿二十歲出家的女子。)也吃了一驚,剛才眾貴女去西苑戲場觀百戲,杜家小娘子自願留下來剪彩勝,案几上還擺著幾枚剪好的金箔片,人卻不見了。
不過這也不奇怪,今日是上巳節,大批百姓出城祓禊(祓禊:古人在水邊以香薰草藥沐浴,以除不祥的一種祭祀。),靜福庵因為毗鄰曲江池,一大早也是車馬盈門,庵裡這樣大,哪能處處照管得到?
「貧尼也不知杜檀越去了何處,不過前頭胡人們開始耍百戲了,杜檀越去了戲場也未可知。滕檀越,可要貧尼為妳帶路?」
沙彌尼說著打量著滕玉意,今日庵裡仕女如雲,這般出色的可不多見,聽說她跟那位杜檀越是姨表親,也不知有什麼急事,一進庵就忙著找杜家人。
只聽滕玉意笑道:「不必了,我表姊不喜看百戲,興許在園子裡賞花。師父請留步,我自去尋她。」
走了兩步,滕玉意突然回身指了指案几,「師父,這些彩勝是我表姊剪的?」
小沙彌尼愣了愣,才道:「是。」
「正好我去找表姊,小師父能不能讓我把這些彩勝帶走?」
本就是消遣的玩意,何況用的也不是庵裡的金箔和玉片,小沙彌尼忙道:「請便。」
這時另一位沙彌尼尋過來:「聖人要觀大酺(大酺:大宴飲。秦漢有法,三人以上不得聚飲,後帝王為表示歡慶,帝賜大酺,特許民間舉行大宴飲。),今夜長安城不宵禁,江邊的月燈閣要辦進士宴了,住持讓妳看好眾女尼,不許到月燈閣附近去。」
沙彌尼恭謹地聽著,難怪剛才庵門口過去好多騎著銀鞍白馬的少年郎君,原來是為了一年一度的進士宴而來。
「弟子知道了。」轉頭她才發現滕玉意已經收好彩勝離開了。
滕玉意一邊走一邊打量不遠處的月燈閣,朱甍碧瓦隱在薄薄暮色中,簷角下點起了流光溢彩的琉璃燈。
前世杜表姊就死在了上巳節這晚,丫鬟紅奴也遭了毒手。主僕倆本來好好地跟姨母在靜福庵禮佛,不知何故竟私自出了庵,等找到表姊和紅奴時,一主一僕橫屍在離月燈閣不遠的竹林裡。
出事時滕玉意在揚州,但也知表姊死得離奇。
表姊一貫孝順穩重,就算不喜熱鬧也會在姨母身邊侍奉,為何姨母去了西苑觀百戲,表姊會留在僻靜的雲會堂?
這些案几上的彩勝更是莫名,今日並非「人日」(人日:女媧創世,第七天造人,故以農曆正月初七為「人日」。這天女子會用彩紙、絲帛、軟金銀等材料製成小人形狀的彩勝戴於頭髮上或貼在屏風。人們也會製作各種花朵形狀的花勝相互饋贈。),表姊怎麼想起來剪這個了?倘若表姊有意要安排獨處的機會,剪彩勝又是為了給誰傳遞消息?
翻找了一會兒未能找到隻言片語,滕玉意倒也不覺得意外,表姊雖然性情柔弱,做起事來卻很謹慎。前世姨父姨母查了那麼久,始終沒能找出引表姊去庵外的那個人是誰。
想到當時表姊被人勒死後的慘狀,滕玉意恨恨地抬頭看著天色。
「碧螺,妳和青桂速去西苑找姨母,我帶白芷去庵外的竹林。若是姨母來時我和表姊未回,就讓她老人家帶人到月燈閣外的竹林來尋我們,切記要快。」
碧螺和青桂應聲是,滕玉意摸向袖中的那張拜帖,還好來之前就做了萬全的準備。
庵門口比之前冷清了不少,遊人們全擁到隔壁西苑看表演,高高的戲臺上,胡人正表演幻術,樂聲一轉,康國胡女扭動腰肢跳起了妖嬈的柘枝舞。
滕玉意和白芷游目四顧,未能在人群中找到杜庭蘭。
她們行至半路時,犢車突然停了,一個名喚端福的奴僕攔到車前,「小人問過一圈了,只有一位賣餳粥的小販見過杜家娘子,這人說杜娘子帶著婢女往江畔東南方向去了。」
滕玉意順著方向看,正是那片竹林。她忙對端福說:「跟在車後。」
天色已晚,出事往往只在一瞬間,車夫揚鞭加快車速。
那是長安城最大的一片竹林,長數百公尺。人在其中極易迷路,所以前世那人在林中悄無聲息地殺死表姊和紅奴,又悄無聲息地離去。
前世滕玉意趕到長安時,表姊已經入棺。她哭著幫姨母整理表姊的遺物,表姊出事那日身上所穿的鬱金裙(鬱金裙:古時用鬱金染製的金黃色裙。亦泛指黃裙。),正是她送給表姊的生辰禮物。
這裙子是由揚州繡娘一針一線縫製而成,顏色如暖金,華貴如雲霓,即便在繁盛的長安也不多見。
今日滕玉意有備而來,一到靜福庵就派出身邊下人四處找尋表姊,以鬱金裙為線索,果然很快就打聽到了表姊的行蹤。
竹林並不遠,他們越往前走行人越少。
車上,滕玉意沉著臉從懷中摸出一樣物事,婢女白芷在一旁嘆了口氣。
數日前她們從揚州來長安途中,小娘子不慎落水大病一場,醒來身邊就多了這柄怪劍。
那是柄翡翠小劍,通體瑩綠,長約一尺。依她看有些奇怪,劍是世間至堅至韌之物,豈有拿翡翠做劍之理?
況且自從夫人去世,小娘子從不擺弄府裡的兵器,身為名將之女,卻養得比儒官的千金還要嬌怯。這回娘子一下船直奔靜福庵也就罷了,還把這翡翠小劍藏在袖中。
白芷打小服侍滕玉意,深知小主人面上甜美,背地裡一肚子壞水,平日裡跟滕府往來的世家千金,明裡暗裡都吃過娘子的苦頭。
老爺常年戍邊無暇管教女兒,眼看娘子的性子越發刁鑽,無奈之下將娘子送往揚州杜府,託姨妹杜夫人代為管束。
杜家家風清正,杜夫人待娘子如親骨肉一般。杜家的長女杜庭蘭,更是處處以表妹為重。她們相處幾年下來,娘子早將姨母和表姊視為至親。
白芷打量著娘子眼裡浮動的戾色,心知倘若再找不到杜娘子,小娘子絕對會做出什麼意想不到的驚人之舉。
這樣想著,白芷往窗外看去,原來犢車已到了一片竹林前,「娘子,妳看。」
竹林入口處停著一輛鑲金飾玉的犢車,好些僕從忙著在林外設幄幕,瞧這富貴至極的排場,恐怕還不是尋常的公卿貴族。
滕玉意自顧自地戴好冪䍦下了車,視那些僕從如無物,逕自往竹林走去。
豪僕們望見滕玉意,立刻上前阻攔:「小娘子請留步。」
滕玉意斂衽行了一禮,笑問:「此處並非禁苑,何故不讓通行?」
僕從道:「我家公子要去江畔擊球,故在此處設了幔帳,等他出了林子,自然就放行了。」
白芷臉色微變,這話霸道至極,偌大一片竹林,說不讓進就不讓進。
滕玉意倒沉得住氣,點頭笑道:「巧了,正好我也要抄近路去江邊赴宴。」
僕人們互望一眼,江畔筵席不只一處,但赴宴者無一不是達官貴人,這女子輕車簡從,委實看不出來歷。
「既是赴宴,娘子想必有帖子。」
「帖子?」
這時犢車前一位中年僕婦道:「今晚除了進士宴,陛下也會在紫雲樓觀大酺,隨行的王孫公子可不少,消息傳揚出去,引來了多少癡頭癡腦的小娘子。」
滕玉意心中一哂,真是冤家路窄,居然在這裡遇見這對主僕。
那僕婦也在端詳滕玉意,小娘子頭戴冪䍦看不清相貌,不過她心裡確定,以往從未在長安見過這號人物。這個小娘子口口聲聲要抄近路去江邊,卻連帖子都拿不出,她自恃身分並不想說重話,只是這一路都攆了多少這樣不知輕重的女子了。
婦人臉上添了輕慢之色,對那幾個豪僕道:「多半又是奔著你家公子來的。這位小娘子,老身奉勸妳一句,他家公子可不好惹,趁早走吧,省得自討沒趣。」
這番話直接將滕玉意打入了攀高結貴之流,白芷臉漲得通紅,正要駁斥幾句,滕玉意瞧那僕婦一眼,冷笑:「是麼?若我偏要進去呢?」
說話間她從袖中取出一樣物事,對攔路的那幾個僕從道:「時辰不早了,請你家主人行個方便。」
眾人面色微變,那是一張郡王府常用的緗色拜帖,上款是淮南節度使兼揚州刺史滕紹,下款是淳安郡王的親筆簽名。
他們平日總跟淳安郡王打交道,郡王的字跡他們一眼就能認出。
淳安郡王是本朝宗室,當今聖上的堂弟。淮南節度使滕紹,則是威名遠播的名將。聽說多年前淳安郡王隨陛下去驪山駐蹕時不慎遇過一次險,正為滕紹所救。
這兩號人物都是自家小郎君的前輩,即便小郎君見了也得下馬施禮。
眾僕不敢再攔,只是仍將婦人和她身後那輛犢車擋在林外。
中年僕婦半張著嘴望著滕玉意,忽聽犢車裡有人嚴厲地咳嗽一聲,聽聲音是位極年輕的小娘子。
婦人回過了神,趕忙換了一副恭謹的笑臉向滕玉意賠罪。
滕玉意瞥了那個僕婦一眼,帶著端福和白芷往林中走去,邊走邊對老車夫說:「你在此處等消息,姨母來了,立刻帶她們到林中找我們。
白芷暗自為那僕婦捏了把汗,以娘子睚眥必報的性子,難保不會找那僕婦算後帳。
「娘子,妳認識那僕婦的主人嗎?」
滕玉意讓白芷點上燈籠,心道:何止認識,三個月後鎮國公的大公子段寧遠突然上門與她退親,正是為了犢車裡的董二娘。
當時眾人聽到消息無不詫異,父親更是驚怒交加。鎮國公老臉掛不住,綁了兒子來請罪,不料段寧遠頑固異常,寧受笞刑也要退親。
「阿爺若是不解氣,再加一百下也使得。」
昏昏霧雨裡,穿墨色襴衫的年輕男子直挺挺地跪到庭前,擺出一副寧死也不回頭的架勢。
鎮國公氣得七竅生煙,奪過鞭子親自施笞刑。
「老夫今日就打死此獠!」
父親冷眼旁觀,直到鎮國公把段寧遠打得半死才開口:「無故退婚,錯不在吾兒。你背信在先,休想將過錯推到玉兒身上,此事傳揚出去,勢必引發街談巷議,但叫我聽到半句指摘玉兒的話,別怪我滕紹無情!」
說罷,父親當眾撕毀了通婚書和答婚書,將奄奄一息的段寧遠逐出了府。
起先坊間提起此事,無不驚訝段寧遠會做出這種背德之事,但隨著時間推移,漸漸傳出了別的說法。
說段寧遠是公認的篤行君子,情願背負罵名行此事,定是因為滕紹的女兒德行有虧。
又說聽說這位小娘子表裡不一,頂著張鮮花般的臉,性情卻極其狡詐。
這套說辭越演越烈,沒多久就傳到了滕紹的耳裡。女子的名聲何其重要,今後誰還敢向滕家提親?但不等滕紹從淮南道趕回來親自處理,段小將軍就因與董二娘幽會被人給撞見了。
那是一次秋日射禮,與宴者幾乎都是王公貴人,地點在樂遊原,附近有座荒廢已久的佛寺,當日不知誰說寺中有奇花盛放,一下子挑起了眾人的興致。
大家過去尋樂,不巧撞見了段小將軍和萬年縣董明府的二千金幽會。
董二娘為了方便出行身著男子胡裝,然而掩不住嬌婉之態。
董二娘淚光盈盈,段寧遠溫聲寬慰,兩人倒是守禮,但誰都看得出段寧遠對董二娘的傾慕和呵護。
此事激起軒然大波,兩人繾綣綢繆,可見早有往來。段小將軍的品行人人稱道,怎知他毀棄婚約竟是因為戀上了別的女子。
而且,早前坊間那麼多關於滕家小娘子的無禮揣測,段小將軍居然一句都不曾維護,只顧心愛之人卻任憑滕家小娘子被人詆毀,簡直是鐵石心腸。
一時間人言籍籍,鎮國公府丟盡了臉。國公夫人不怪兒子只恨董二娘,寧死也不讓董二娘進門。
當晚滕玉意歪靠在榻上,氣定神閒地喝著酒盞裡的石凍春。
段寧遠要跟誰雙宿雙飛她毫無興趣,但因為一己之私妄圖把她也賠進去,未免欺人太甚。
段寧遠是個極謹慎的人,她為了布這一場局不知費了多少心思,終於等來這廝身敗名裂的一天,她怎能不豪飲?
僕婦看滕玉意等人順利入內,眼饞之下,也試圖上前商量,但一眾豪僕將她們攔在林外,再也不肯放行。
僕婦嗓門不小,白芷在前頭不免聽見幾句,才知這僕婦是萬年縣董明府家的管事娘子。
白芷雖常年在揚州,但也知長安城分為兩縣,東城屬萬年縣,西城屬長安縣。
兩縣縣令說來只是正五品上的官階,但兩縣地處京畿,縣令執掌實權,算得上有頭有臉的人物,無怪乎府裡的一個管事娘子都如此跋扈。
中年僕婦跟那幫豪僕交涉一番全無效用,只聽犢車裡的人喚了一聲,婦人忙上了車又掀簾出來,悻悻然地吩咐車夫道:「二娘擔心老夫人的病體,趕著赴完宴回城侍奉,莫在此處乾耗了,另繞遠路吧。」
車夫應了,香車轔轔,漸行漸遠。
白芷扭頭看向身邊的滕玉意,娘子一進到林中就如臨大敵,她心裡再好奇,也不敢多問了,只奇怪那些豪僕的公子究竟什麼身分,連萬年縣縣令都不放在眼裡,而且想必人已經出了林子,因為起先還能聽到不遠處有說笑聲和腳步聲,漸漸只剩風聲。
靜水深流,越安靜越詭異。
走了一段路,也分不清東西南北,白芷只覺得心裡發毛,還好身邊跟著端福,這老奴身手不凡忠心耿耿,有他在身邊就不必怕。
空氣溼涼,慢慢滲入一絲腥味,三人正疑惑間,林中驀地傳來一聲女子的驚叫聲,樹梢簌簌作響,好像有什麼龐然大物從頭頂飛過。
滕玉意低喝道:「端福!」
「是!」只聽噹啷一聲,刀刃寒光迫人,端福拔刀飛縱而去。
滕玉意提裙急追,那女子雖然只短促地叫了一聲,但她一下就聽出是表姊的聲音,只恨頭頂那巨物掠過時帶著風,竟不知是人是畜。
她腦子裡一瞬間轉過千萬個念頭,凶手不會是封林之人──既要殺人,何必大張旗鼓?當眾攔了那麼多犢車不讓進,無異於向天下昭告他是凶手。
依她看,凶手多半藏在林子暗處,先前她因怕遭暗算,一進入林中便萬分防備,哪知情況比她預料的還要詭異。
利器鏘然作響,端福已然跟那東西交了手,他的兵器是千年玄鐵所製,劈石斬金。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攻玉(一)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20 |
二手中文書 |
$ 237 |
言情小說 |
$ 270 |
靈異/推理 |
$ 270 |
中文書 |
$ 270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攻玉(一)
將軍之女滕玉意遭奸人殺害,
墜入幽冥之際再次甦醒,
發現自己竟重生回家人相繼離世之前,
身邊還多出了一把詭異的翡翠小劍護身。
更奇怪的是,原本前世死於歹人之手的表姊,
這一世卻遭妖怪襲擊,命在旦夕;
過去她從來沒有聽說過長安城內有邪物作祟,
如今卻接連不斷地遇上各種邪門怪事?!
這一世,很多事情似乎都變得不太對勁……
為了解救表姊等人所中的妖毒,
滕玉意出發找尋救援,不想竟因此反踏入妖物所設迷障,
情況危急之際,幸有成王世子藺承佑出手相救。
前世僅有一面之緣的兩人,今世因合力抗妖有了更多的交集,
也因滕玉意手中那把翡翠劍而結下了意外的梁子。
她原以為重生僅是為了換取家人性命無虞,
不料卻被這位世子扯入意想不到的妖異險惡之境……
作者簡介:
凝隴,晉江金榜人氣作者,三部作品均廣受歡迎,代表作《花重錦官城》獲第十五屆華語文學傳媒──年度網路作家大獎。
微博搜索:凝隴
章節試閱
第一章
杜庭蘭望著窗外,天色不早了,紅奴遲遲沒有回來。
不知紅奴見沒見到盧兆安?進士宴開筵在即,再晚她就別想當面跟盧兆安對質了。
一想到盧兆安,杜庭蘭心裡就油煎似的難過,這半個月他避而不見,害她悒怏成疾,她現在有一肚子的話要問他,只恨此人連當面對質的擔當都沒有。
不能再等下去了。杜庭蘭起身悄然打量四周,母親在西苑戲場看百戲,女眷們大多去了園子賞花,四下裡無人,正是離庵的好時機。
杜庭蘭咬了咬唇,剛要放下手中的繡剪,廊下忽然傳來說笑聲。
「今年明經科取了百餘人,進士科卻只有區區二十人,聽說年紀都...
杜庭蘭望著窗外,天色不早了,紅奴遲遲沒有回來。
不知紅奴見沒見到盧兆安?進士宴開筵在即,再晚她就別想當面跟盧兆安對質了。
一想到盧兆安,杜庭蘭心裡就油煎似的難過,這半個月他避而不見,害她悒怏成疾,她現在有一肚子的話要問他,只恨此人連當面對質的擔當都沒有。
不能再等下去了。杜庭蘭起身悄然打量四周,母親在西苑戲場看百戲,女眷們大多去了園子賞花,四下裡無人,正是離庵的好時機。
杜庭蘭咬了咬唇,剛要放下手中的繡剪,廊下忽然傳來說笑聲。
「今年明經科取了百餘人,進士科卻只有區區二十人,聽說年紀都...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