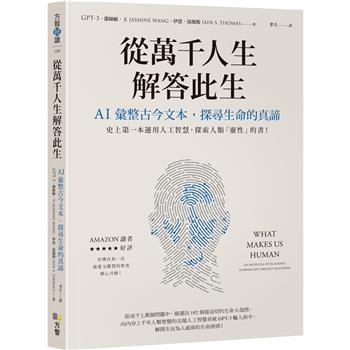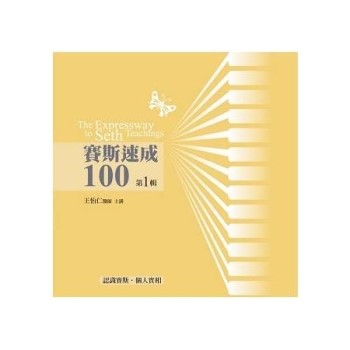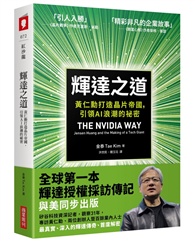長安城內一連發生數起剖腹取胎的駭人命案,
懷胎未足月的婦人、消失的嬰胎、室內殘留的迷香,
還有逗留現場卻滿手血腥的詭異男人──
看似大案已破,但曾近身與真凶打過交道的滕玉意,
一眼便識破凶手另有其人!
藺承佑懷疑其中又是妖魔作祟之故,他能否勘破背後真相?
滕玉意受帖前往玉真女觀參加賞花會,
正當眾家貴女開心遊玩之際,忽然天響巨雷、狂風四起,
當混亂散去,一行人卻被困在了桃花林的迷障中。
忽然現身桃林裡的神祕僧人到底是人是鬼?
小涯劍一再示警的「耐重」又是何方神聖?
一聽到滕玉意又遭逢危險,藺承佑頓感心焦不安。
怪哉,明明赤金色的蠱印還在,
本該斷情絕愛的他,怎會對這小娘子動了心?
可當得知她曾經夢見過他,又心繫著他的安危時,
他的心為何不自覺地跟著發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