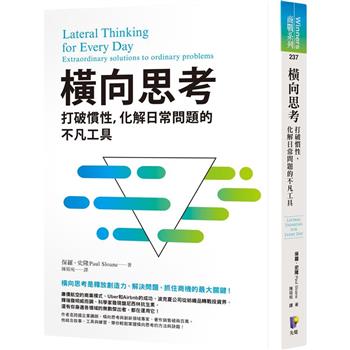第一章
眼看時辰不早,藺承佑起身告辭。
他唯恐翻窗時發出動靜,走時並未撤走小鬼,而是把送走小鬼的法子告訴了滕玉意,讓她等他走後再撤。
兩人走到窗前,藺承佑轉頭看著滕玉意說:「知道怎麼做了?」
「知道。」滕玉意方才聽得很仔細,忙把法子原樣複述了一遍。
藺承佑想了想,「差不多吧。」
乜了滕玉意一眼,又道:「無為妳也算是青雲觀的半個俗家子弟了,是時候學著自己施展這些簡單的道法了。我出去後在屋脊上等一等,假如妳做得不錯,說明已經入了門,那麼下回帶妳除祟也就沒什麼顧慮了。要是做得不夠好,說明還差火候,我也是很怕被人拖後腿的,帶妳除祟的事就得再等一等了。」
滕玉意一聽這話,忙卯足了勁,「世子瞧著就是。」
藺承佑在心裡一笑,很快便翻窗出去。事不宜遲,滕玉意忙用火摺子點燃藺承佑留下的符籙,口中念念有詞,先送走窗外的小鬼,再送走門外的小鬼,末了把門口和窗縫的引魂粉清掃得一點不剩。
做完這一切,滕玉意低頭看腕子上的玄音鈴,玄音鈴果然不再輕輕搖動,這說明她成功把小鬼們都送走了。
她心知藺承佑未走遠,恨不能對窗外高興地喊上一句「我做得不錯吧?」
藺承佑屏息貓在屋簷上,見狀笑了笑,身形一縱,輕飄飄地沒入了夜色中。
梳洗的時候,滕玉意時不時能感覺到阿姊朝自己投來疑惑的目光,等到兩人上床躺下,阿姊果然開口問她:「妳跟世子一起除過祟?」
滕玉意不能對阿姊說自己這樣做是為了攢功德,只好含糊道:「兩個小道長拉我去的,正好我最近總是撞邪,覺得學些道法對自己大有益處,所以就跟著去了。」
杜庭蘭把一隻手壓在自己的右臉下,另一隻手替妹妹掖了掖被角,「妳沒瞧出來藺承佑喜歡妳?」
滕玉意一愣。
「妳想想,如果他不是把妳的事極放在心上,怎會一聽說書院有事就馬上趕過來?」
滕玉意驚訝地張了張嘴,「但這是我們事先說好的,藺承佑本來就是個重諾守信的人──」
「帶妳除祟也是為了要履約?妳又不懂道術,他帶著妳不嫌拖累麼?」
滕玉意怔住了,與此同時,心裡湧出一種很奇怪的悸動感,這感覺不能算陌生,此前也曾竄上過心頭,但每回只短暫地停留,一瞬就會消逝不見。她呆了好一會,出聲打斷阿姊:「那回他們之所以帶我去除祟,是為了幫我試一試玄音鈴是否恢復了法力。這事說起來還是因為我要進書院念書了,藺承佑聽說我身邊鬧賊,也很好奇那賊是誰。」
杜庭蘭微笑,「妳身邊鬧賊又與他有什麼相干?成王夫婦眼下不在長安,成王府的一干事宜都需藺承佑打理,他如今又在大理寺任職,經手的都是錯綜複雜的大案,他每天四處奔波,本就很忙了,倘或不是心裡非常在意,有必要抽出精力來照管妳嗎?」
滕玉意再次滯住了,因為她居然覺得阿姊的話很有道理。
「不對、不對。藺承佑自己說過,他是因為收了我送的紫玉鞍才答應要幫忙的。」
杜庭蘭嘆氣:「成王府每年不知要收到多少天下異寶,假如每收一份珍品就要答應幫一次忙,藺承佑不知要幫多少人的忙了。」
「我跟那些人可不一樣,我跟藺承佑還有絕聖、棄智有一份過命的交情。絕聖、棄智說,那回要是沒有我幫忙,大夥不能那麼順利降服屍邪,後頭除去血羅剎,我也占了很大的一份功勞,藺承佑是非分明,很清楚我在其中幫了多大的忙,如今我被人暗算,他衝著這份交情也不會不管的。」
滕玉意兀自滔滔不絕,杜庭蘭卻只靜靜聽著,等妹妹一口氣說完這番話,她笑著說:「這些話,妳是不是總在心裡對自己說?」
滕玉意啞然一瞬,旋即振振有詞:「阿姊,妳忘記藺承佑還中著絕情蠱了?妳看看盧兆安那賤人給妳下的蠱有多毒辣就知道了,除非宿主險些身亡,否則很難解開蠱毒,藺承佑這蠱毒料著更不好解。再說就算蠱毒解了,藺承佑要是喜歡誰,犯得著遮遮掩掩嗎?他每回都告訴我他只是幫個忙,一再叫我別多想。」
杜庭蘭沒接茬,這也是她最想不通的一點。
藺承佑心悅妹妹,這點她絕不會看錯,但以藺承佑坦蕩的性子,喜歡誰一定會大方承認,他前前後後為妹妹做了這麼多事,卻連自己的心意都沒讓妹妹知道,這實在令人想不通,難不成其中有什麼隱情?
滕玉意看阿姊不說話,只當阿姊被自己說服了,把衾被蒙到頭頂,在被子裡悶聲說:「阿姊睡吧。」
杜庭蘭卻又道:「浴佛節那一晚藺承佑把妳約出去,妳回來之後頭上多了一對步搖,當時因為出了武大娘的事,阿姊也沒心思追問。現在阿姊要問妳,那對步搖可是藺承佑送妳的?即使答應幫妳的忙,有什麼必要送這麼昂貴的首飾?」
「早說了是為了還人情。他說他不習慣收這麼貴重的生辰禮,那步搖算是回禮。」
「噢,所以妳就接了?」
滕玉意聽得不耐煩,翻個身背對著阿姊,「我很喜歡那個樣式。這很不妥麼?那我還回去好了。」
杜庭蘭生恐妹妹在被子裡悶壞,拉拽被角試圖讓妹妹的腦袋露出來,「妳好好同阿姊說話。妳是不是也早就疑心藺承佑喜歡妳了?」
滕玉意一邊把自己捂得更嚴實,一邊在被子裡「哼」了一聲,「他可沒說過喜歡我。再說了,世間男子無有不薄情的,就算他眼下喜歡我,保不齊哪一日就變心了。倘若相信男人的話,日後準會傷透心肝的。別說藺承佑未必喜歡我,就算真喜歡我也不會同意。我早就想好了,這輩子絕不嫁人。」
杜庭蘭手頓在了半空,燭臺早就熄了,黑暗中只能看到模糊的輪廓,面前那條「長蟲」仍在扭動,她卻不知如何接話了。
姨母去世時她雖不在身邊,但也聽說過姨母去世時的詳情──姨母臥病在床,姨父卻急著親自護送一位鄔姓女子離開,等到姨父趕回來時,夫妻倆都沒能見上最後一面。
妹妹因為這件事,心裡結了一個死疙瘩,這些年一直對姨父冷冰冰的。再加上前一陣子出了段寧遠的事,難怪妹妹會乾脆斷了婚嫁的念頭。
杜庭蘭在心裡嘆了口氣,輕輕搡了搡妹妹的肩膀,「妳把頭鑽出來,阿姊不說了。」
滕玉意正好憋得慌,依言把腦袋鑽出來,只是雙眼仍然緊緊閉著,口裡嘟噥著:「我睡著了。」
杜庭蘭望著黑暗中模糊的臉龐,只覺得千頭萬緒不知如何開口,末了只輕輕拍了拍妹妹的被子,「睡吧、睡吧。」
看妹妹這表現,也不像是全然不在意藺承佑。藺承佑光明磊落,光是救妹妹就救過好幾回,兩人共同經歷了這麼多事,又豈是一個段寧遠能相提並論的?越在意,反應就越大,所以妹妹才會急著否認,還一口氣列舉了這麼多藺承佑不可能喜歡自己的理由。
還有那對步搖,換別人送妹妹那對步搖,估計瞧都懶得瞧一眼。肯收下,只因送禮的人是藺承佑。
只不過妹妹在男女一事上還懵懵懂懂的,加上心結太重,即便明白過來,也不可能輕易敞開心懷。
杜庭蘭憂心忡忡,這種事不戳破則已,一戳破必然要得出個結果。到時候兩個人少不了鬧一場彆扭,萬一妹妹鑽了牛角尖,說不定會跟藺承佑斷絕往來……
緊接著想起方才兩人相處的情形,兩個人自有一份默契,交流起來外人壓根插不上話。
罷了,橫豎這種事外人幫不了忙,就由著兩個人自己鬧去吧。鬧著鬧著,這結說不定就解開了。
◎
第二日,藺承佑沒去大理寺,而是在成王府等消息,用完午膳沒多久,寬奴就跑來了。
「世子料事如神。昨日一整晚盧兆安那邊都沒動靜,今早香象書院放了端午節的假,學生們各自回府,沒多久盧兆安那邊就有動靜了。」
藺承佑在遊廊前的一株茶花前停下,「那人是誰?」
「一個賣餳粥的老婆子。」寬奴說,「這些日子盧兆安忙著備考制舉,鮮少出門,老婆子剛吆喝兩聲,盧兆安就出來了。那附近全是住戶,老婆子要是誠心做買賣,一定會多賣幾個時辰,但是盧兆安買完粥沒多久,老婆子就推車走了。我們幾個一直跟出坊門,這老婆子始終沒露出破綻,可等她把車推到醴泉坊的永安大街時,有個貴戶的下人出來買粥,小人認出那是誰的下人,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藺承佑道:「誰的下人?」
寬奴說了一個名字。
藺承佑皺了皺眉。
「太狠毒了。」寬奴摸摸發涼的後頸,「那回世子過生辰,這人也曾上門賀壽,買粥的下人就是那人身邊最得力的大婢女,小人絕不會認錯的。」
藺承佑第一個念頭也是「太狠毒了」。
昨晚他和滕玉意列舉了重點懷疑的對象,此人的名字雖然也在列,但他們心裡並不覺得那人會與此事有關,今日知道這消息,未嘗不意外。
「說說當時的情形。」
「婢女靠近買粥,這老婆子故技重施,等婢女買了粥,只捱了一會就推車走了。沒多久老婆子回到了附近的下處,過後便再也沒出來過。這幫人藏得實在太深了,而且整件事做得滴水不漏,要不是世子說今日一定會有人給盧兆安送東西,小的也不會留意一個賣餳粥的老婆子。世子,你怎麼知道他們今日會傳遞東西的?」
藺承佑只在心裡想:一個一心想當皇后的貴女,即便在皓月散人的引誘下接觸了邪術,又如何知道盧兆安也是這夥人中的一員?
莫不是幕後主家有意幫襯這位貴女,故意放了些風聲給對方?
是了,一旦這位貴女如願當上了太子妃,對幕後主家有百利而無一害。
貴女早年做過的那些骯髒伎倆,幕後主家心知肚明,到了適當的時機,他便可以拿這個來脅迫這位太子妃。
此女未必知道此人的真實身分,甚至未必知道對方的真實目的,但她為了保全自己的榮華富貴,一定會乖乖從命的。
只要控制了東宮,接下來無論是謀逆或是弒君,都會變得容易許多。
瞧瞧這人心思是多麼縝密,考慮問題又是多麼長遠。
「很好。」藺承佑道,「挑幾個最精明能幹的,務必把這老婆子給我盯死了,她屋子裡應該藏著不少好東西,到時候都是定罪的鐵證。等我這邊布置得差不多了,直接抓人便是。還有,既然知道書院裡害人的那位是誰了,我這邊會多放點關於太子妃人選的風聲,那女孩聽多了,必然按捺不住的,人一亂,就容易出岔子,這幾日你們好好跟著她,說不定能逮到更多的破綻。」
「好。」寬奴想了想又說:「可惜浴佛節那晚抓到的幾個『尾巴』,因為毒發身亡沒法確認身分了。但是前頭跟蹤世子的那幾個潑皮,小人已經按照世子的囑咐查過,有兩個人曾經是朝廷的逃犯,二十年前逃到淮西道後就杳無蹤跡了,但不知為什麼,前一陣子偷偷潛回了長安。小人猜他們八成是彭震養的死士,就不知為何盯上世子?」
「這還不明白嗎?」藺承佑一嗤,「這幫人是在我抓住莊穆以後才開始盯梢我的。彭震萬萬沒想到莊穆會暴露,礙於不能堂而皇之去大理寺劫獄,只好令人偷偷盯梢我。我去摘星樓買名貴首飾的風聲,就是彭家人放出來的。至於浴佛節那晚盯梢我的幾個『尾巴』……」
有可能是盧兆安那位幕後主家派來的,但也可能是那位貴女自己雇的人,他們跟了他一路,卻又屢屢暴露行蹤,這樣做的目的,無非是想促使他與鄧唯禮相遇,即便當晚沒成功,過後也會用別的法子製造他與鄧唯禮私會的假象。結果僥倖當晚就讓他們成功了,這幾個尾巴再無用處,所以一被抓就毒發身亡了。
想到此處,藺承佑心裡忽然產生一種異樣的感覺。
他曾無數次設想皓月散人那位幕後主家是誰,在他看來,那人可能是跟彭家一樣懷有異心的某位強藩,或是對中原虎視眈眈的某個鄰國派來的細作,也有可能是某位藩國王子,甚至可能是朝中某位因為被冷落而懷恨在心的大臣。
總之不論是出於什麼目的,那人除了財力、物力,還需有遠勝常人的謀略手段。
但是他越查越覺得,除了以上種種,此人好像還對他的行事風格很熟悉。
「對了,可查清楚盧兆安在揚州時都與哪些人來往密切?」
「大多是揚州城的名人墨客。這幫人也常常到長安和洛陽遊歷,若是賞識盧兆安的才華,極有可能引見他認識京中貴要。」
「好好查一查這幫人的底細。」藺承佑道,「特別是近一年來過長安的,這幫縉紳表面上閒雲野鶴,實則可能與京城某些勢力暗中有來往。」
「是。」
「對了,我要出門,替我備馬吧。」他得去找太子打聽一件事。
除了太子,明日他還有一個人要見。
「還有,明日要出城狩獵,你幫我安排見一個人。」
寬奴一愣:「誰?」
「武元洛。」
既然知道書院裡那個人是誰了,此前很多事就能串聯起來了,不過他還是覺得有些不可思議,所以得向武元洛當面確認一些事。
◎
武元洛和藺承佑在菊霜齋對坐著喝茶。
武元洛臉色很難看,今日原本要隨君出城狩獵,走到半路就被藺承佑攔下來了,沒等他弄明白怎麼回事,藺承佑就以要調查案情為由,把他請到了菊霜齋。
這地方讓他覺得很不舒服,偏巧又坐在窗邊,他想起那晚大妹妹出事的情形,幾乎一刻都坐不住。
但他也知道,藺承佑無事絕不可能把他約到這種地方來,便勉強按捺著喝了口茶,啞著嗓子問:「找我何事?」
藺承佑打量武元洛,短短幾日這人就憔悴不少,家中出了這樣的大事,武元洛身為武家長子,必定焦頭爛額。
估摸著氣氛醞釀得差不多了,他開門見山道:「說吧,那晚你為何故意接近滕娘子?」
武元洛萬萬沒想到藺承佑一開口就問這個,望了藺承佑一會,淡淡道:「這件事與閣下有關嗎?」
廢話,當然與我有關。藺承佑譏笑:「你是怎麼認得滕娘子的?」
武元洛望了藺承佑一會,突然笑道:「怪不得那日在驪山上你會好心借玉牌,我早該看出你對滕娘子的心思,你故意搗亂就是怕我接近她吧?」
藺承佑並不接話,只笑道:「你武元洛一向眼高於頂,怎會突然對滕娘子產生興趣?她來長安沒多久,你充其量瞧見了她的模樣,至於性情如何你可是毫不清楚,結果一上驪山,你就迫不及待讓你妹妹幫你製造機會接近她。」
武元洛哼笑:「大理寺不是很忙嗎?要是你只想打聽這種無聊的事,我可沒工夫奉陪。」
「無聊不無聊,你說了可不算。」藺承佑笑容一淡,「我來猜猜吧,你是不是聽人說起了桃林的那件事?玉真女觀的迷宮天下聞名,滕娘子第一回去觀裡遊樂,論理並不清楚觀裡的迷局,但她卻成功破解耐重的謎題,帶領同伴們逃出生天,你聽說這件事,一定對這個聰明絕倫的小娘子很好奇。」
武元洛沒吭聲,但表情已經說明了一切。
「長安從來不乏貌美端莊的仕女,你武元洛自小在錦繡堆裡長大,面對這樣的女子只覺得無趣;但是滕娘子就不一樣了,她當日的那番作為讓你刮目相看,你有神童之名,但這個女孩的機智顯然不在你之下,在那之後你又從某個人的口裡聽說了種種關於她的事蹟,對滕娘子更是心生嚮往,沒多久你終於等來機會接近她,於是便毫不猶豫地出手了。」
武元洛微微一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藺承佑,你不是也相中了滕娘子嗎?」
藺承佑話鋒一轉:「所以那回在驪山上你藉故接近滕娘子,究竟是你的主意?還是──」
武元洛忽然覺得有點不對勁了,琢磨了一會道:「這話什麼意思?」
「直接回答我的問題。」
武元洛雖然疑竇叢生,但還是把答案說了出來。
藺承佑默了默,若非向當事人求證,任誰也想不到實情會是這樣。
「還有一件事也讓我很好奇,能不能說說為何你更偏疼大妹妹武緗?」
聽完武元洛的話,藺承佑心裡已經有了答案。
「你再把浴佛節前幾日府裡發生的事,以及當晚你們兄妹從府裡出來後的種種,從頭到尾、一字不漏地告訴我。」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攻玉(七)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攻玉(七)
前世她才聽聞太子有意迎娶自己,後便遭逢毒手;
今生表姊偶然與太子一遊,又被人偷了詩稿嫁禍。
重生之後,滕玉意一直困惑自己死於非命的原因,
直到眼見這一連串關聯,才發現或許一切,
就藏於與她有著同窗情誼、競逐太子妃的眾家貴女之中……
為了解除滕玉意因借命重生反使妖患纏身的境況,
藺承佑不只親自帶她除祟積德,更暗下決心要護她長命百歲。
七欲天布下的迷離幻境,竟是兩人大婚的場面,
而水下朦朧的一吻更是縈繞彼此心中久久不散。
當歷劫歸來後,發現旁人也知曉她的好,
當著皇親眾臣的面,藺承佑情不自禁地請皇上指親,
沒想到得來的答覆竟是──她、不、嫁?
源源不斷的妖異禍事,伴隨無極門的陰狠手段,
城中的反抗勢力正蠢蠢欲動、伺機而起,
平叛在即,烽火將起,長安是否還能永保太平──
作者簡介:
凝隴,晉江金榜人氣作者,三部作品均廣受歡迎,代表作《花重錦官城》獲第十五屆華語文學傳媒──年度網路作家大獎。
微博搜索:凝隴
章節試閱
第一章
眼看時辰不早,藺承佑起身告辭。
他唯恐翻窗時發出動靜,走時並未撤走小鬼,而是把送走小鬼的法子告訴了滕玉意,讓她等他走後再撤。
兩人走到窗前,藺承佑轉頭看著滕玉意說:「知道怎麼做了?」
「知道。」滕玉意方才聽得很仔細,忙把法子原樣複述了一遍。
藺承佑想了想,「差不多吧。」
乜了滕玉意一眼,又道:「無為妳也算是青雲觀的半個俗家子弟了,是時候學著自己施展這些簡單的道法了。我出去後在屋脊上等一等,假如妳做得不錯,說明已經入了門,那麼下回帶妳除祟也就沒什麼顧慮了。要是做得不夠好,說明還差火候,我...
眼看時辰不早,藺承佑起身告辭。
他唯恐翻窗時發出動靜,走時並未撤走小鬼,而是把送走小鬼的法子告訴了滕玉意,讓她等他走後再撤。
兩人走到窗前,藺承佑轉頭看著滕玉意說:「知道怎麼做了?」
「知道。」滕玉意方才聽得很仔細,忙把法子原樣複述了一遍。
藺承佑想了想,「差不多吧。」
乜了滕玉意一眼,又道:「無為妳也算是青雲觀的半個俗家子弟了,是時候學著自己施展這些簡單的道法了。我出去後在屋脊上等一等,假如妳做得不錯,說明已經入了門,那麼下回帶妳除祟也就沒什麼顧慮了。要是做得不夠好,說明還差火候,我...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