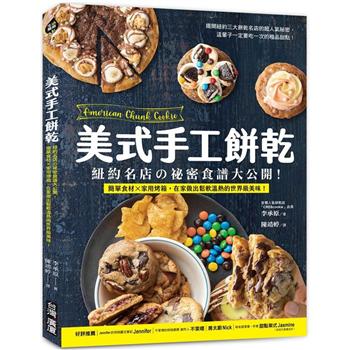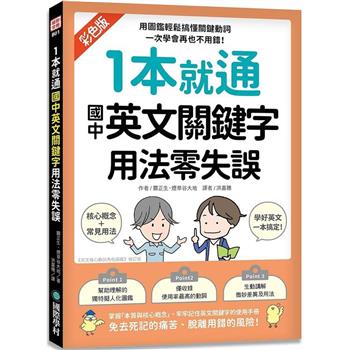第一章
對於民眾來說,皇后陌生,也不陌生。
先前朝廷的告示已經傳遍了,大家都知道先帝駕崩,新帝登基,還有一個新皇后,這個皇后是衛將軍楚岺的女兒。不過也沒有什麼具體的念頭,就是遙遠的皇城裡皇帝的妻子而已。
此時此刻,死裡逃生的城中民眾紛紛湧出來,看著通過城門走進來的人馬,看著為首騎在馬上的女子──她的年紀也就十四、五歲吧,身上背著弓弩,馬背上懸著刀,衣袍簡陋,且遍布血跡。
她就是楚將軍的女兒,虎父無犬女;她就是大夏新的皇后,但並不是遙不可及,高高在上──楚將軍在雲中郡守衛邊郡,阻擋了西涼大軍,他的女兒則從遙遠的皇城來到這裡,殺掉了西涼散兵。
他們以為他們被拋棄了,沒想到皇后娘娘親自來救他們。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威武!」
「叩謝皇后娘娘救命大恩!」
無數的聲音如雪花一般,鋪天蓋地,席捲城池。
行走在隊伍中的丁大錘腿腳一軟,還好旁邊有人及時扶住他,他轉頭看,是自己的「妻子」──丁大嬸依舊蒙著臉,雪花飛舞,讓她的面容更加模糊。「妳、妳……」丁大錘忍不住低聲說,「妳可猜到她、她──」這個女孩兒竟然是皇后。
皇后!先前對著西涼兵衝殺的時候他都沒有半點腿軟,但聽到鋪天蓋地的喊皇后聲,他真要跪下去。女孩兒說自己家大業大,他猜過是真的,但再猜也猜不到家大業大到這種地步啊!這可怎麼辦?這條大魚,還能釣嗎?
嗯……丁大錘又站直了身子,看著扶著自己胳膊的女子,如果立刻把這女子按在地上,揭穿她的身分和歹意,自己在皇后面前也算是戴罪立功了吧?
入城之後,謝燕來帶著兵馬清剿附近的西涼散兵,楚昭與官員們去撫慰民眾、傷者,還好城池未破,傷亡不算太大。
楚昭親自為傷者裹敷傷口,女孩兒束紮衣袖,對血肉翻捲的傷口沒有絲毫的畏懼,倒是讓得知身分的傷者都顧不上疼痛,惶恐道謝。
一直到暮色降臨,楚昭才回到官衙,剛洗漱更衣,謝燕來披著一身厚雪踏步而來。
「吃了嗎?傷口包紮過了嗎?」楚昭一迭聲問。
謝燕來瞥了她一眼,才不回答她這些沒用的問題,只道:「這附近已經清剿了,算下來大約有百數西涼兵。」又嗤聲:「真是可笑,區區百數就能肆虐這麼久。」
楚昭輕嘆:「到底是許久未經戰事,措手不及。」再抬頭問:「你傷──」
「飯沒吃,傷處理過了。」謝燕來不耐煩地打斷她,又問:「還有別的事嗎?沒有,末將告退。」說著話轉腳要走。
楚昭伸手揪住他袖子,「有、有、有。」
謝燕來斜眼看著她,沒有再邁步。
「先前你為什麼不說我們是我父親派來的援兵?」楚昭笑問。
當時她還沒接近,謝燕來已經跟城池的將官喊出了她的身分。她一路走來都是隱瞞身分,連躊躇不能前的時候都沒有告知當地駐軍,此時一路順暢,卻揭穿了身分?「我不是怪罪你啊。」楚昭又道,「我是說,那樣更能為我父親增加聲望呢。」
謝燕來呵了聲,「我怕妳怪罪嗎?」居高臨下看了這女孩兒一眼,冷冷說:「妳父親是妳父親,妳是妳,你們雖然是父女,但並不就是一體。而且妳父親就要死了,死了聲望就沒了,妳還活著,還要活下去,比起妳父親,是妳更需要聲望。」說罷甩袖子掙脫楚昭的手,大步走了出去。
楚昭看著翻動的門簾,怔怔又呆呆的。
她一直以為自己是不幸的,就算醒來重活也堵著一口氣,直到此時此刻,那一口氣輕輕吐出來──她是幸運的,這一世能遇到這麼一個為自己著想的人。她抬起頭,喚道:「來人。」
老白應聲走進來,對楚昭俯首聽令。
楚昭道:「傳令,露布,報皇后剿望城西涼兵大捷。」
謝燕來離開楚昭這裡,並沒有回去吃飯,而是來到另一處房屋前。
兵馬都駐紮在城門,一是為了警戒,二是不擾民,畢竟這裡剛經歷過圍城,只有女眷跟著楚昭住進來。謝燕來走近時,屋簷上響起了鳥鳴,如同鳥兒受驚飛過,謝燕來頭都不抬一下,抬手就推開了屋門,「匡噹」一聲,人裹著寒氣衝進去,屋子裡的一男一女嚇了一跳。
丁大錘坐在椅子上,瞪眼僵硬,似乎忘記了起身,倒是那婦人──丁大嬸,受驚過後忙施禮:「謝校尉。」
謝燕來看著兩人,淡淡說:「大叔、大嬸不要怪我不請而入。」
丁大錘僵硬著身子,磕磕巴巴說:「……什麼?」
丁大嬸還蒙著臉,但從眼睛裡可以感受到她在笑,她接過丈夫的話,說:「謝大人客──」
「氣」還沒說出來,謝燕來已經再次開口:「──因為丁大嬸你們已經接到我來的警報,就不用我再多此一問了。」他說。年輕人身高瘦長,面容桀驁,長腿一勾將一把椅子帶過來,大馬金刀坐上去,冷冷看著兩人。
謝燕來剛來的時候就先把丁大錘這些人見了一遍,一個一個盯著看,連丁大嬸都不放過,還不客氣地問為什麼蒙著臉。丁大嬸說受過傷,面殘,怕嚇到人,自慚形穢,謝燕來當時就笑:「大嬸怕嚇到什麼人?嚇到你們身邊的這些人?那他們不配當妳同伴。至於嚇到其他人,那不是正合適?」
他說這話的時候,楚昭在後戳了他好幾下,見戳他不理會,乾脆說有其他的事,把他扯走了。
接下來謝燕來沒有再揪著蒙面的事不放,也不再盯著他們這些好心的獵戶,把他們排兵布陣,和身邊的兵將一樣呼來喝去,直到今天,才坐在這裡,看著這兩人。「丁大叔怎麼來這裡了?」謝燕來問,「你們夫妻兩個不是知道避諱嗎?一路上比陌生人還陌生人。」
「我當家的把胳膊扭到了。」丁大嬸說,「我不放心,叫他過來看一看。」說著看了眼謝燕來。「這夫妻相處,在心不在外,看起來陌生,但其實都是互相惦記的。」
跟他說這些做什麼?誰在意他們夫妻怎麼相處。謝燕來嗤笑,挑眉道:「為什麼扭到胳膊啊?先前衝陣殺敵的時候也沒見到丁大錘你受傷啊。」他說的是丁大錘,但視線看著丁大嬸,嘴角似笑非笑。
丁大嬸垂下視線,用手戳了戳丁大錘,「你說嘛,有什麼好丟人的。」
丁大錘被戳了下,僵著身子,說:「因為……我被嚇到了,所以沒站穩,摔倒了,脫臼。」
他說完了,丁大嬸才接著說:「我們真沒想到小姐她身分如此不凡──」
謝燕來呵呵笑:「大嬸,別這麼謙遜,有什麼你們沒想到的啊?你們要是沒想到,會被一個小丫頭說動來為她拚命?」
丁大嬸眼裡似有笑意,再次伸手戳一旁的丁大錘,「當家的──」
「行了,大嬸,不用裝了。」謝燕來打斷她,說:「妳才是當家的,這位丁大叔不是妳的丈夫,或者是,但也只是傀儡而已。」
沒錯,他是傀儡,還是能被隨意打的傀儡,終於有人看出來了!丁大錘眼角差點滴淚。這個女人才是大山賊啊──他真想大喊一聲,但想到適才不過是略動了心思,略動了下身形,就被這女人幾乎拆了……眼前這個謝校尉跟這女人打起來可能不相上下,但不相上下之前,這女人解決他可是輕而易舉……丁大錘僵硬著身子繼續做傀儡。
丁大嬸垂著頭,眼裡的笑意再也掩飾不住,然後抬起頭,看著這年輕小將。
「是。」她說,「我的確是當家的,我們也猜到小姐身分不凡,但校尉,我們再猜也猜不到小姐會是人間龍鳳啊!這場面,真是嚇壞人了。」
嚇壞了?謝燕來看著這婦人的一雙眼,看不出來半點驚嚇,只有歡喜──「覺得發了大財了嗎?」他淡淡說。
丁大嬸說:「是,走了大運了。」這一次不待年輕小將審問,主動開口:「我們這樣身分的人,原本只想求財,如今遇到這般機緣,就想再求個運道。」
謝燕來看著她,這婦人自從承認自己是當家的,雖然依舊柔弱,但氣勢不同了。「有所求,就要知道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他淡淡說。
丁大嬸沒有回答,眼中含笑反問:「校尉一路應該親眼看到我們求財的心意了吧?所以我們今日還能坐在這裡。」
謝燕來看著這婦人,不喜不怒。
丁大嬸也沒有惶恐,鄭重施禮:「校尉,我們聲名狼藉、苟且偷生,能為皇后娘娘鞍前馬後,是天上落下來的大好事,請謝校尉接下來再看看我們求運道的心意。」
「當家的果然不一般。」謝燕來站起來,看著這婦人,幽幽道:「既然當家的知道我看著,那就別怪我看不順眼的時候,砍掉你們的頭──」
他說到這裡時,門外有腳步響。「阿九──」女聲喚。
謝燕來幽冷的臉頓時浮現不耐煩,也不答話。
女孩兒已經推門進來了,眉眼燦爛一笑。「你果然在這裡。」她說,對他招手,「我正要找你呢。」
謝燕來冷冷說:「末將不是妳隨從,娘娘有吩咐找老白去。」
楚昭根本不理會他的冷臉,扯住他衣袖,「要緊的事,天大的事,離了你不行,快跟我來。」說罷向外走。
謝燕來唯恐被扯壞了衣袖,只能跟著出去,「楚昭!妳注意身分。」
楚昭回頭一笑:「我身分高高在上,誰能奈我何?」
謝燕來哈的笑了,「厲害啊阿昭小姐,不是先前離開皇城都躊躇的時候了。」
楚昭也笑了,「好了,不要胡扯了。」回頭看了眼這邊的屋子,見丁大嬸站在門口目送,便對她笑了笑,再收回視線看謝燕來,「你又來嚇唬人家幹什麼?」
謝燕來抬著下巴看她,「難道妳以為妳裝聾作啞,人家就真以為妳裝聾作啞嗎?」又冷笑,「人用了,就不問問清楚嗎?」
楚昭知道謝燕來一來就貓兒一般盯上了丁大錘這些山賊,一雙眼看來看去,幾乎把這些山賊看得神魂出竅,想到這裡,她忍不住笑。「看破不說破嘛。」她說,「我知道他們知道,他們知道我知道,這不就行了?」說到這裡又哼了聲,「當初你呀,非要揪著我說破,害我今天多走一遍這條路。」
謝燕來的眼尾一沉,「我是個怕死的人,要說破一切危險,楚小姐不怕請隨意。」說罷一甩袖子,大步向前去。
「你生什麼氣啊。」楚昭笑道,追上去,「我沒有怪你哦,過去的事我可沒那麼小氣,你也別那麼小氣……」
兩人一前一後,在視線裡越來越遠,聽不到說什麼,但丁大嬸依舊站在門口看著,眼裡的笑意溢出來。「這謝校尉,還不錯。」她點頭。
丁大錘在後忍不住說:「他太凶了吧,哪裡不錯?」對他們凶,對那位小姐也很凶。
「他對我們凶,是擔心那位小姐,想要護她周全。」丁大嬸含笑說。
所以那位小姐啊,也一點都不害怕他。丁大嬸看著遠處,女孩兒搖搖晃晃跟在小將身側說說笑笑,那小將肩背挺直闊步不理會,但背負在身後的手勾在一起,小尾指晃啊晃。
◎
「報──」
「雲中郡外西涼兵被誅──」
「大捷,望城大捷──」
「皇后楚氏望城大捷──」
飛馳的驛兵背後插著飛揚的帛錦旗穿過了城池,本就繁鬧的大街上瞬時如同爆竹炸裂。
二樓的包廂裡,齊樂雲「砰、砰」兩聲將窗戶推開,冷風裹著喧囂聲湧進來,室內穿著單薄的女孩兒們發出抱怨:「齊樂雲妳幹什麼!」
齊樂雲站在窗邊大聲說:「讓大家聽清楚些。」
女孩兒們嗔怪:「還用這樣聽?」「我們早聽清楚了。」
這些人非富即貴,消息靈通,這次又是露布飛捷,早在到達京城之前,家中已經得到消息了。大家顧不得理會窗邊的齊樂雲,紛紛看著坐在正中的楚棠。「阿棠,這到底怎麼回事?」「楚昭怎麼去邊郡了?」
楚棠伸手按住心口,「這件事終於可以說了,我瞞得好辛苦啊,妳們不知道,我的心、我的身備受──」
女孩兒們不待她說話就打斷,搖晃著,「別管妳的心、妳的身了。」「快說怎麼回事!」
楚棠被搖晃得直笑,避開女孩兒們走出幾步。
「這件事很簡單,當京城諸人紛紛指責我叔父主將不力,痛惜民眾之苦時,楚昭她從宮中率兵而出──」她站定腳,伸手向前一揮,宛如利劍,劈下,「直奔邊郡,誅賊,救民。」
很簡單。聽起來,是很簡單,但做起來那麼遠,那麼險──女孩兒們神情激動地看著她。
楚棠轉過頭看大家,「這就是我楚氏,救國護民,不懼罵名艱險,我們不說,只做。」
齊樂雲在窗邊一拍,「怎能不說!先前有過,楚將軍被罵,現在有功,就要誇!阿棠,楚園開宴,下帖子,都來誇皇后!」
「荒唐!」
朝堂大殿裡,在隔了許久後,滿耳都是在說皇后。
在露布飛捷進京之前,朝廷大多數官員也都接到消息,當時就堵在了太傅和謝三公子的所在。
先不說皇后為什麼出現在邊郡,把這個消息壓下去,只說大捷,不要說皇后,但依舊沒有用,露布飛捷喊著皇后的名義,穿城過鎮直達京城,人盡皆知。
朝殿上,滿朝文武追問太傅,包括謝燕芳,以及坐在龍椅上的小皇帝,事到如今,大家都心裡透澈了。
「外邊現在沸沸揚揚傳皇后什麼深宮聽到百姓遭難心不安,連夜帶兵赴邊關──都是假的!」皇后在這件事發生之前,就不在深宮了。
朝官們看向龍椅,龍椅後簾子還垂著,後邊已經許久沒有人──當然,簾子後本就該沒有人。當時說皇后救護皇帝時的傷復發要休養,所以不能再陪同皇帝上朝──他們巴不得她一輩子都傷不好呢,為此歡呼雀躍,感謝上天有眼,誰想到那楚后不在朝中垂簾聽政,竟然帶兵跑去邊郡了!古往今來,哪有這樣的荒唐事!更荒唐的是,皇帝也就罷了,年紀小什麼都不懂,也什麼都管不了,監國太傅,還有謝燕芳,這兩人可別說自己不知道!真要他們兩個也不知道,那這大夏就是楚后一手遮天了。
「太傅、謝大人,你們怎能這樣縱容皇后,做出這種荒唐事?」這一刻,滿朝文武齊聲質問。
鄧弈自始至終都不說話。
「諸位,這也不算荒唐事。」謝燕芳道,「這畢竟是捷報,喜事──」
「謝大人!」一個官員憤聲打斷謝燕芳,「現在說的不是捷報,是皇后離宮!」
謝燕芳緩聲道:「其實也還是這件事,皇后離開宮廷就是為了救護邊民。」
「謝大人吶。」一個年老的官員顫聲,「我們大夏已經到了需要皇后領兵打仗的地步了嗎?這難道還不是荒唐事嗎?如果大夏真到了這種地步,本官雖然老邁,但也敢赴死一戰!」
謝燕芳對他一禮,道:「大人之心,燕芳明白。」
明白?光說好聽話,就是不說這件事有什麼用!幾個官員急著上前一步──
「有什麼荒唐的?」鄧弈的聲音從前方砸下來,「如果這是荒唐事,先前也不是沒有過。」
大家看向他。
「別忘了,陛下──」鄧弈說,「就是楚皇后親自御馬殺敵救下來的。」他掃了眼在場的諸官,「我大夏如今本就是國朝不穩,荒唐事不斷,楚皇后能親手殺賊護陛下,當然也能親赴邊關守疆土。我大夏有如此皇后是不幸中的大幸,爾等有什麼好質問的!現在聽到消息,你們說荒唐,說自己要去殺敵,先前怎麼不說?當然,現在說也不晚──」鄧弈的視線落在那位老大人身上,「你們想要如同皇后一般上陣殺敵、守衛疆土,就請即刻赴邊關吧。」
滿朝譁然,這是威脅!
那老大人又是氣又是急:「好你個鄧弈,本官這就脫下官袍,去邊關殺敵!」再號召其他人:「我等都去,我等為大夏赴死,這朝堂就留給太傅一人足矣!」
大殿裡不少官員當即脫下官帽,有人憤慨,有人哭先帝,亂作一團。
這是自臨朝以來,蕭羽第一次見到這場面,他坐在高高的龍椅上,越過這些官員,似乎看到了那一夜──那一夜好像也這麼亂,不,那一夜不亂,那一夜只有黑暗、兵器、火光。蕭羽要抱緊懷裡的竹筒,伸手發現空空──竹筒留在寢宮了。
怎麼辦?竹筒不在,姐姐也不在……
「阿羽。」有聲音傳來。
這聲音跟母親好像,但又不一樣,他快要忘記母親的聲音了……蕭羽循聲看去,撞上一雙明亮又溫暖的眼。
「阿羽。」謝燕芳說,「還記得舅舅告訴你的話嗎?」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楚后(四)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楚后(四)
楚后露布飛捷!
在奔赴邊郡的路上,傳來西涼兵潛入國境襲殺的消息,
她楚昭身為一國之母,邊關大將之女,自是責無旁貸,
哪怕此舉招搖,在有心人眼中她這皇后──所圖甚大。
上一世她當皇后,讓很多人如意,只有她自己倒楣,
這一世她做楚后,也許人厭狗嫌,但就像謝燕來說的,
她不會總是走霉運的!
最好的證明,就是她終於見到了心心念念的父親,
還有……母親?
楚岺病重,西涼大軍叩關,邊境形勢危急。
楚昭能代父守關,能起激勵人心之效,
卻仍無法扭轉父親的結局……
偏偏值此情勢險峻之際,中山王父子竟也趁隙起兵!
她已見到本來不及見到的人,救下原不該存在的生命,
更遇到了前一世未曾相識的人,
既然無憾,這一戰就算與敵同歸於盡,她也贏了。
商品特色
不留遺憾,
即使輸了,也是贏了。
想自由自在,就要有力量。這是她的天地,她創造的新的一世。
只要是為自己而戰,即使在別人眼裡沒有意義,也能讓人開心。
作者簡介:
希行,女,生於燕趙之地,平凡上班族,雙魚座小主婦,以筆編織五彩燦爛的故事為平淡生活增添幾分趣味,偏好鄉土氣息,愛有一技之長的女主,愛讀書,愛旅遊,用有限的時間和金錢,過出無限的生活和情趣,生平最大的理想,不求能寫出神來之作,但求看過故事的女子們,都能悅之一笑心有所安便足矣。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對於民眾來說,皇后陌生,也不陌生。
先前朝廷的告示已經傳遍了,大家都知道先帝駕崩,新帝登基,還有一個新皇后,這個皇后是衛將軍楚岺的女兒。不過也沒有什麼具體的念頭,就是遙遠的皇城裡皇帝的妻子而已。
此時此刻,死裡逃生的城中民眾紛紛湧出來,看著通過城門走進來的人馬,看著為首騎在馬上的女子──她的年紀也就十四、五歲吧,身上背著弓弩,馬背上懸著刀,衣袍簡陋,且遍布血跡。
她就是楚將軍的女兒,虎父無犬女;她就是大夏新的皇后,但並不是遙不可及,高高在上──楚將軍在雲中郡守衛邊郡,阻擋了西涼大軍,他的...
對於民眾來說,皇后陌生,也不陌生。
先前朝廷的告示已經傳遍了,大家都知道先帝駕崩,新帝登基,還有一個新皇后,這個皇后是衛將軍楚岺的女兒。不過也沒有什麼具體的念頭,就是遙遠的皇城裡皇帝的妻子而已。
此時此刻,死裡逃生的城中民眾紛紛湧出來,看著通過城門走進來的人馬,看著為首騎在馬上的女子──她的年紀也就十四、五歲吧,身上背著弓弩,馬背上懸著刀,衣袍簡陋,且遍布血跡。
她就是楚將軍的女兒,虎父無犬女;她就是大夏新的皇后,但並不是遙不可及,高高在上──楚將軍在雲中郡守衛邊郡,阻擋了西涼大軍,他的...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