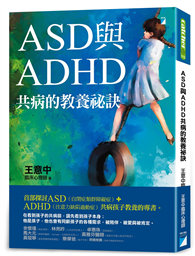第一章
陳氏出身耕讀世家,從小養在深閨學規矩,性格柔順。王氏則不同,她出身商賈不說,而且從小就有主見,帳務的事一點就通,當年郁棠的祖父就是瞧中她這點才給郁博求娶的。因而王氏的性格頗為爽利,自家人說話的時候喜歡直來直去的。
妯娌倆見郁棠這一副懵然的樣子,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王氏更是搶在陳氏之前快言快語地道:「妳是不是已經知道李夫人來我們家鬧事了?可惜妳回來晚了,不然就可以看看李夫人那狼狽樣了!哼!想欺負我們家,門都沒有!」
這樣潑辣的大伯母,她還是在小時候見過。後來,大伯母的話越來越少,人也越來越沒有精神,遇事、遇人總是忍讓的時候多,直抒其意的時候少。
是因為境遇的緣故吧?前世,她的家人死的死,散的散,兒子、姪女都活得艱難,連個能撐腰的親人都沒有,她自然怕給兒子、姪女惹麻煩,處處都息事寧人了。
這一世,諸事皆順,家裡的日子像那芝麻開花,一節還比一節高,眼看著就要興盛起來了。大伯母腰桿直了,別說是李夫人了,就是知府夫人來,沒有道理的事只怕大伯母也敢辯幾句了。
這樣的長輩,不僅讓她覺得揚眉吐氣,更多的則是欣慰和驕傲。
有一天,她也能作為父母、長輩的依靠和底氣,也不枉父母和長輩在自己幼小的時候為她遮風擋雨了,讓她有個回報的機會。
郁棠眼睛微微有些模糊地上前挽了大伯母的胳膊,低聲笑道:「大伯母說這話是什麼意思?我這不過出了趟門,怎麼回來就感覺天翻地覆了似的?您快給我說說前因後果唄!」
陳氏嗔笑著拍了拍她的肩膀,喝斥了她一句「怎麼跟妳大伯母說話的」,就去給她倒了杯茶,示意大家坐下來說話。
郁棠挨著王氏坐下。
王氏這才笑著把之前發生的事一一告訴了她。
原來,初二的時候李端去杭州城給顧家拜年,不承想顧大老爺病了,顧曦和父親、繼母都去了長房那邊探病。他到了之後,顧家大爺只是露了個面就把他交給了顧家二房的管事。那管事也不知道是怎麼想的,擺了桌酒席就把他一個人留在了客房,既沒有安排作陪招待的,也沒有安排服侍的,李端心裡就隱隱有些不高興,找了個藉口,當天晚上就趕回了臨安城。等到初八,顧家二房突然來人,說是顧二老爺請了李端到家裡說話。李端不敢怠慢,換了身新衣裳就帶著重禮去了杭州城。
誰知道顧二老爺和李端喝了半天的茶,委婉地表示,顧小姐年紀還小,原本定下的婚期要推遲幾年,到時候再議。
李端一聽就炸了。
顧家雖然沒有明說要退親,可這就是拖著不辦的意思。
他追問理由。顧家只說是給顧小姐算了個命,顧小姐近幾年不宜婚嫁,否則要有性命之憂。顧家人聽著嚇壞了,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決定等兩年再說。
這理由聽著義正辭嚴,李端很在乎這門親事,不想和顧家撕破臉,只好順著顧家的意思和顧二老爺打了半天的太極,把這件事給圓了過去。
可他不是那種遇事沒個主見的人。他一出了顧府就撒了銀子差人去打聽這件事。
很快,顧家已經知道了李家和郁家恩怨的事傳到了他的耳朵裡。
發生的事是事實,他不能說沒有,可怎樣扭轉顧家對他的印象,還得從長計議。
他先回了臨安城。結果一下碼頭就發現了三木鬼鬼祟祟地偷窺他。他原本心中就有氣,抓著三木就狠狠地審了一通。
三木什麼也不說,李端一無所獲,卻把懷疑的目光投到了郁家人身上。
等他回到府裡,林氏立刻就從兒子身邊服侍的人嘴裡知道了這件事。她認定是郁家在搗鬼,想著兒子這兩年就要下場,還指望著顧小姐的胞兄顧昶幫襯提攜,要是顧家和李家的婚事有了變化,李端怎麼辦?他們李家怎麼辦?
要知道,他們家和李家分了宗,不知道多少人盯著,想看他們家笑話的不少,想趁機從他們家弄點好處的就更多了。
她又急又氣,帶著幾個孔武有力的僕婦就找上門來。
陳氏當時一個人在家,根本不敢開門,陳婆子看著不對,悄悄從後門跑去找王氏。
王氏可不是省油的燈,氣勢洶洶地就跑了過來,當場就和林氏懟上了。
林氏畢竟是當大家閨秀養大的,這麼多年來順風順水,不看僧面看佛面,有什麼衝突的時候,別人都讓著她,她哪裡見過王氏這種市井閭巷作派?幾個回合就被氣得昏了過去,被家裡的僕婦給抬了回去。
王氏講完猶不解恨,道:「要不是顧忌著妳今年要說親了,我怎麼會就這樣放了她回去?怎麼也要追到大街上去,讓眾鄉親們幫著評評理。別以為他們家出了個讀書人就了不起。難道他們家以後一有什麼不好的事,都與我們家有關不成?」
可能是提起了剛才發生的事,她說這話的時候有些動怒。
陳氏忙給王氏續了杯茶,安撫她道:「別動怒。他們家不就是想我們家跟著一起生氣嗎?我們一動怒,就輸了。」
王氏深深地吸了幾口氣,嘴裡還喃喃地道著「不生氣、不生氣」。
郁棠汗顏,心中暗暗責怪大堂兄沒有聽她的,沒讓賣水梨的阿六去盯著李端,可轉念一想,這等事如果不讓李家知道,和錦衣夜行有什麼兩樣?
就是得讓李家知道。
就是得讓他們跳腳。
郁棠在心裡冷哼一聲,對大伯母道:「林氏倒也沒有找錯地方。他們家和我們家的恩怨,就是我去告訴顧家的。」
王氏和陳氏聽了目瞪口呆。
既然她已經從杭州城平安回來了,家中長輩不會再擔心她的安危了,她也就沒什麼好隱瞞的了。她把事情的經過一五一十地告訴了王氏和陳氏,並道:「這是我的主意。憑什麼他們李家把我們家給弄得亂七八糟的,只是給我們家賠個禮就得原諒他們家,我們家就不能也給他們家找點麻煩?」
前世,他們郁家不就是被李家害得家破人亡的嗎?如果她沒有重生,沒有前世的記憶,郁家還不是會和前世一樣被李家陷害!
郁棠冷冷地道:「我是想就這樣算了的,可那些作惡的人不會放過我們,我們越是逃避忍讓,他們就越會得寸進尺,更加作惡多端。」
陳氏聞言急得直跳腳,道:「妳這孩子,也太不懂事了!冤冤相報何時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們都好好的了,妳就別去惹這是非了。」
王氏卻和陳氏相反,她覺得郁棠這番話太對她的脾氣了。
她對陳氏道:「阿棠說得對。憑什麼我們心軟就得吃虧,他們算計別人後道了個歉,我們就得原諒他們?早知道這事是阿棠做的,我剛才和李家人吵架的時候就應該承認,就應該拉著她到大街上去找來往的鄉親們評評理──事情鬧成這樣,我們郁家縱然沒臉,他們李家更丟臉──顧家居然要推遲婚約啊!」
如今的李端能讓人高看一眼,不就是因為攀上了顧家這棵大樹嗎?要是李家沒有了顧家這個姻親,不過是出了個四品的官員,有什麼好害怕的?
「這……」陳氏隱約覺得這樣不太好,卻又被王氏說得心中鬆動,一時間不知道要說什麼了。
郁棠索性道:「姆媽,狹路相逢勇者勝。從前我就是有太多的顧忌,做這事要三思而後行,做那事要考慮周全,結果呢?」
結果她大伯父和大堂兄都遭了不幸。
如果她前世能早點從李家出來,是不是一切都會不一樣了呢?
郁棠眼中有淚。
「太太,阿棠說得對!」屋裡突然出現郁文的聲音。
眾人齊齊轉頭望去。
郁文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的,正表情嚴肅地站在屋子門口聽著她們說話。
「相公!」
「二叔!」
「阿爹!」
三人同時對著郁文打招呼。
郁文臉上露出一絲笑意,把手搭在了郁棠的肩膀上,對王氏道:「還是大嫂有見識。狼凶殘,我們就要比狼更凶殘,才能成為好的獵人。」說完,他朝著王氏深深地行了個揖禮,道:「今天多虧了大嫂相助,客氣話我就不說了,等會我讓阿棠的姆媽親自下廚燒幾個菜,您和大兄到家裡喝酒。」
自己的小叔子這樣鄭重地道謝,王氏臉色通紅,無措地擺著手,說著「二叔客氣了」。
郁文已轉頭去說陳氏:「妳以後再遇到這樣的事,只管找大嫂商量,聽大嫂的就是。」
剛才王氏懟林氏的時候陳氏已對王氏敬佩得五體投地了,此時聽郁文這麼一說,就更佩服王氏了,忙向王氏道謝。
妯娌倆彼此客氣著,郁文已虎著臉詰問郁棠:「妳怎麼這麼大的膽子,居然敢就這樣跑去杭州城?難道妳父兄都是擺設不成?這種事,妳為什麼不提前告訴我一聲?」
她不是叫上大堂兄了嘛?
郁棠見父親發脾氣,只敢在心裡暗中反駁,面上卻垂著頭,一副做錯了事的模樣。
然後郁文下一句話卻讓郁棠忍不住噗哧笑出聲來。
「早知道妳還有這鬼主意,我就應該和妳一起去的!」
眾人望向失笑的郁棠。
郁棠忙忍了笑,對父親道:「您去做什麼?難道還想親自把我們兩家的恩怨告訴顧家不成?」
郁文挑眉,「有何不可?」
陳氏聽著心頭亂跳,生怕這父女倆不管不顧地胡來一通,忙做出一副嗔怒的樣子道:「怎麼越說越離譜!背後道人家是非,還是件好事不成?」
郁棠父女不想讓陳氏擔驚受怕,齊齊閉嘴。
王氏見了,笑著在旁邊勸道:「好了、好了。總歸我們家沒有吃虧。至於別人家是喜是怒,又不是至親,與我們家有何關係?聽說裴家出錢,明天官府會在長興街辦燈會,今天大家都早點歇了,明天一道去長興街看燈會吧?」
陳氏也不是真的惱了父女倆,王氏遞了臺階過來,她自然順勢而下,笑盈盈地對王氏道:「正想約阿嫂和大伯呢,沒想到阿嫂先開了口。你們準備明天什麼時候過去?我們在哪裡碰頭?」
妯娌倆商量好了明天逛燈會的事,陳氏親自送了王氏出門。
郁文的臉就板了起來,對郁棠道:「妳隨我來。」
郁棠不敢多說,乖乖地和父親去了書房。
郁文癱坐在太師椅上,喝斥女兒道:「妳還做了些什麼?這個時候給我一一交代,我就不追究了,不然就給我抄一萬遍《孝經》去。」
那豈不是要把手都抄腫了?!
郁棠苦著臉道:「真不是有心瞞著您的,是不想把您牽扯進來,才不告訴您的。」
郁文急道:「妳不告訴我,李夫人卻找到家裡來了。還好今天妳大伯母趕了過來。要是嚇著妳姆媽了,妳準備怎麼辦?」
郁棠低頭認錯。
郁文少不得把郁棠教訓了一頓:「既然已經把這件事告訴了顧家,顧家不管怎麼對待李端,那就都是李家的事了,你們居然還派人盯著李端,想看他的笑話?結果好了,把自己給繞進去了吧!」
◎
李家那邊,林氏怒不可遏地連著砸了好幾個茶盅。「都怪那郁家,要不是他們家,我兒怎麼會受這樣的委屈?明明知道我兒初二要去拜年,做岳父、岳母的不見也就罷了,居然還讓個下人招待我兒。他們這是什麼意思?覺得我們家高攀了不成?我倒要看看,顧家準備把這門親事怎麼辦?」
李端只覺得深深的疲憊。
自從衛小山的死因暴露之後,事情就像失了控的馬車,朝著連他也不知道的方向狂奔。他背後好像有雙看不見的手,在推著他走。
不過,顧家的事真的像他母親說的那樣,會與郁家有關係嗎?
郁家不是有讀書人嗎?那郁文也素有文名,怎麼會在背後議論他們家的是非呢?
李端看著氣得嘴唇發抖的母親,想著要怎麼勸慰她幾句,抬眼卻看見表兄林覺站在窗外朝著他使眼色。
為了那幅〈松湖釣隱圖〉,林覺不僅沒有回福建過年,還想辦法找了個裝裱師父把那幅輿圖修整如新。等過了正月十五,他們就能派人去給彭家送信了。
不枉他這位表兄這段時間的辛苦。
他不動聲色地朝著林覺點了點頭,林覺會意,回了自己住的客房。李端又安慰了母親幾句,才找了個機會脫身,去和林覺碰面。
「出了什麼事?」李端一見到林覺就道,「連我母親也要瞞著。」
「女人家就是頭髮長、見識短。」林覺不以為然地道。
他的姑母也不例外。與其這個時候擔心李端在顧家受了什麼委屈,不如關心關心那幅輿圖是真是假。只要李家得了勢,顧家還捨得放棄李端這個金龜婿嗎?
女人,永遠分不清楚主次。
「我尋思著把輿圖送到彭家之前,我們得先臨摹幾幅留著才行。」林覺說了他深思熟慮後的想法,「我們得防著彭家翻臉不認人。」
到時候真有個萬一,他們還可以拿了臨摹的輿圖去找其他有實力的人家投靠。
李端一點就透。他道:「那我們先送封信給彭家,就說畫已經拿到手了,問他們怎麼把畫送過去,拖延些時日?」
這樣書信一來一往的,就能拖個十天半個月。
林覺見李端明白了自己的意思,眼中閃過欣慰之色,他壓低了聲音:「只是這輿圖?」
李端也立馬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很果斷地道:「我們兩家一家一幅。」
林覺滿意了,道:「我這就去辦。到時候我和你一起去見彭家的人。」
說來說去,還不是怕李家獨吞了彭家的好處。
李端半點聲色不露,笑著點頭,道:「理應如此!」
林覺呵呵地笑。
◎
郁家那邊,郁博晚上從鋪子回來,聽說李家有人來郁家鬧事,特意和王氏過來瞧了瞧陳氏,郁遠卻沒有同來。
郁博不滿地道:「那小子,這些天也不知道在幹什麼?早出晚歸,大過年的,碰個面都難。我要不是看著他馬上要成親了,早就逮著他一頓打了。」
過年的時候,哪家的小子不四處撒野?郁文倒沒覺得郁遠沒過來問候一聲有什麼不對,還勸郁博:「你也說他快要成親了,你往後得少說他幾句了。以後媳婦進了門,你這樣一點面子都不給他,他還能不能在妻子面前挺直胸膛了?」
郁博嘀咕了幾句,也就隨郁遠去了。
◎
翌日是正月十五,郁遠依舊不見人影,郁棠則去了馬秀娘家,只有郁博兄弟和王氏妯娌一起去逛了燈會。
郁遠還真像郁博所說,不知道在忙些什麼。
直到正月十七收了燈,正式過完了年,家家戶戶的鋪子都開了門,郁遠這才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冒了出來,興奮地告訴郁棠:「我找到妳說的那種樹了。叫沙棘。還真就像妳說的那樣,越是土質不好的地方越容易存活。」
郁棠一聽也來了興致,忙拉了郁遠到書房裡說話。
郁遠告訴她,這些日子他跟著姚三兒見了好幾撥在外面做生意的人,其中有一個叫高其的,跟著一個鹽商跑腿,曾經在西北那塊兒見過這種樹。「他還說,若是我們真心想要,他可以幫著聯繫送些樹苗過來。不過一株苗要一兩銀子,得先付訂金。」
「這麼貴!」郁棠愕然。
她原以為這樹非常便宜好打理,裴家才在山上種這種樹,然後做成蜜餞賣了賺錢的。如果一株樹苗都要一兩銀子,他們還賺什麼錢啊?
難道這其中還有什麼她不知道的蹊蹺?
郁遠聽郁棠這麼一說,頓時像被潑了一盆涼水似的,找到樹種的興奮和喜悅一下子被澆得溼透了。他像被霜打了的茄子,蔫蔫的,「那、那我們還種不種樹了?」
郁棠也拿不定主意了。
她道:「你先等等。讓我再仔細想想。」
郁棠尋思著要不要去請教裴宴,弄清楚當年裴宴怎麼會想到在他們家的山林裡種沙棘樹……
◎
沈方陪著沈善言回了臨安城。
沈善言特意請了郁文過去說話:「你說的那個樹種,我大兄有個學生在西北做官,可以幫著弄些回來。只是來往的費用不菲,只怕你還得仔細盤算盤算。」
郁文聽了心裡一跳,道:「多少錢一株?」
沈善言道:「算上來往的費用,差不多三十幾文錢一株了。」
的確很貴。
但這是郁棠要的。
他一咬牙,道:「那能不能先弄個十幾二十株回來我們試種一下?」
「這倒沒有問題。」沈善言笑道。「我乾脆讓他再給你找個懂得種沙棘樹的師父來好了,若是能成活,他也可以在這兒討份活計。」
真要種樹了,郁遠也好,郁棠也好,都不可能住在山裡,總是得請人的。
「行啊!」郁文爽快地答應了,回去就把這件事告訴了郁棠。
郁棠張口結舌。
價格怎麼相差這麼遠!難道是因為管道不同?
郁棠沒有多想,只是讓郁遠去推了那個叫高其的人,就說家中的長輩已經託人去買樹苗了。
這原本也是人之常情。郁遠沒有放在心上,和高其打了聲招呼就算把這件事翻過去了,開始天天往老宅那邊跑,丈量山林,安排春耕,不過十幾日,就晒黑了。
王氏不准他再去林子裡,道:「這開春的日頭,看著暖和,實則最晒人不過了。你馬上要娶親了,要是這個時候晒得像塊炭似的,人家相小姐說不定還以為自己相看的和嫁的不是同一個人了呢!」
郁遠傻笑,卻也不再去林子裡,一心一意地準備起婚事來。
郁棠也覺得這件事急不得,先幫著大堂兄把嫂嫂娶進門來才是當務之急。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花嬌(三)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90 |
二手中文書 |
$ 237 |
言情小說 |
$ 255 |
古代小說 |
$ 270 |
中文書 |
$ 270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花嬌(三)
郁棠發現,雖然這個裴三老爺脾氣不好了一點,
比起旁人聰明得不只一點,
但不吝予人的好意更是多了好多點!
在他的運籌帷幄下,郁家不僅如願丟出了燙手山芋,
還大賺一筆,有本錢往富業豐家之路邁進一大步。
而且,這人還面冷心熱,不管她折騰著要做什麼,
他嘴上嫌棄,可總是在關鍵處幫她一把。
她更意外察覺,原來,前世每當她走投無路之際,
這位低調到不行的裴三老爺都曾出手幫過她……
這個小姑娘就沒有消停的時候嗎?
每次問「郁小姐在做什麼」,總有新驚……奇等著他。
可裴宴還是覺得自己就喜歡看她神采奕奕的樣子,
就算她是在幸災樂禍地說著仇家的倒楣八卦也一樣。
但情況好像越來越不對勁了?
這樣的她,竟開始讓他覺得漂亮得令人有些心悸?!
商品特色
知恩,感恩,有情自有助。
原來,不只這世,在前世,在她毫無知悉時,
裴宴已給過孤苦無助的她那麼多幫助與溫暖。
作者簡介:
吱吱,女,起點女生網白金寫手,著有《以和為貴》、《好事多磨》、《庶女攻略》、《花開錦繡》等作品。
喜歡看書,宅,吃,是個一直以來都不太接地氣的人,相信愛情,相信童話,相信世間一世美好的事物。
願能帶給大家閱讀的樂趣。
章節試閱
第一章
陳氏出身耕讀世家,從小養在深閨學規矩,性格柔順。王氏則不同,她出身商賈不說,而且從小就有主見,帳務的事一點就通,當年郁棠的祖父就是瞧中她這點才給郁博求娶的。因而王氏的性格頗為爽利,自家人說話的時候喜歡直來直去的。
妯娌倆見郁棠這一副懵然的樣子,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王氏更是搶在陳氏之前快言快語地道:「妳是不是已經知道李夫人來我們家鬧事了?可惜妳回來晚了,不然就可以看看李夫人那狼狽樣了!哼!想欺負我們家,門都沒有!」
這樣潑辣的大伯母,她還是在小時候見過。後來,大伯母的話越來越少,人也越來...
陳氏出身耕讀世家,從小養在深閨學規矩,性格柔順。王氏則不同,她出身商賈不說,而且從小就有主見,帳務的事一點就通,當年郁棠的祖父就是瞧中她這點才給郁博求娶的。因而王氏的性格頗為爽利,自家人說話的時候喜歡直來直去的。
妯娌倆見郁棠這一副懵然的樣子,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王氏更是搶在陳氏之前快言快語地道:「妳是不是已經知道李夫人來我們家鬧事了?可惜妳回來晚了,不然就可以看看李夫人那狼狽樣了!哼!想欺負我們家,門都沒有!」
這樣潑辣的大伯母,她還是在小時候見過。後來,大伯母的話越來越少,人也越來...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