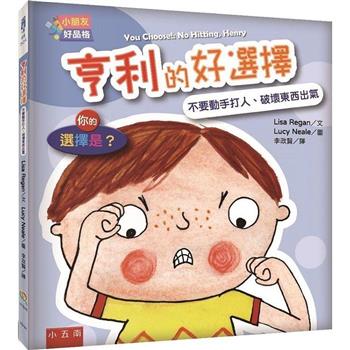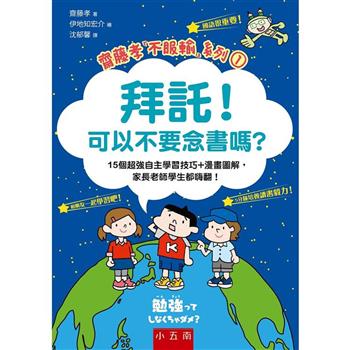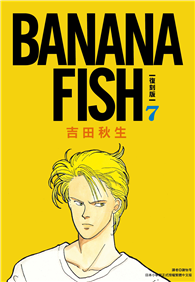引子
一九九二年,陝南由唐縣,老牛頭崗。
炎還山一大早就出了門,蹬著自行車跑了大半個縣城,給七、八家白的黑的「有關單位」送了禮──他在崗西盤了個小煤礦,資格證明不夠、手續不全、嚴重違規,不私下孝敬的話,立刻就得關閉。
不過話又說回來,這年頭,國家經濟才盤活,且「活」得有些迅猛,各項法規跟不上,就得靠人情和關係走天下。
一個上午,炎還山送出去兩、三萬,不過他非但不心疼,還美滋滋的:關係打通了,礦上的事就好辦了,媳婦林喜柔懷孕了,托人做了超音波,說是個男的。
男的哎,帶把兒的,老炎家有後了!
事業家庭雙豐收,炎還山太滿足了,回礦場的路上,他把車子蹬得歪歪扭扭、很風騷,嘴裡還哼上了鄧麗君的〈甜蜜蜜〉。
離著還遠,炎還山就看見了站在礦場門口、微凸著肚子的林喜柔。
這還得了,孕婦怎麼能瞎走動呢!炎還山慌得都沒顧得上支腳架,隨手把車子掀倒在地,大步流星迎上去:「妳怎麼來了?」
林喜柔二十七、八年紀,人如其名,面相討喜而又溫柔,她提起手裡的保溫飯盒:「礦上的大鍋飯不好吃,給你包了豬肉餃子。」
炎還山這才意識到快到飯點了,同時油然而生媳婦在身邊的自豪感:礦下那些大小光棍,或者雖有女人卻遠在老家的,可吃不上這種熱騰騰的「愛心」飯。
他小心翼翼地攙著林喜柔往礦場辦公室走:「來,來,小心走,慢慢的。」
林喜柔笑岔了氣:「我這還在哪呢,你瞎緊張什麼啊。」
辦公室裡有點亂,牆上貼著五花八門的「十佳」、「先進」之類的獎狀,都是炎還山這兩年到處活動來的。林喜柔只掃了一眼,就把目光避開了去,她其實不大喜歡這些弄虛作假的玩意,可是小姐妹們都誇,說男人這樣是腦子活、精明、懂變通。
飯盒打開,韭菜味、肉鮮味混著老陳醋的酸味四下漫溢,炎還山非常滿足地猛嗅了好幾下,立即開動。
林喜柔在桌子對面坐下,從提袋裡掏出棒針和毛線球,熟練地打上了毛衣,同時找話聊:「那個李二狗,還沒找著呢?」
炎還山吃得呼哧呼哧,答得含糊不清:「這龜孫……偷了礦上的錢,還不遠遠躲開了去?上哪找啊?」
李二狗的事,算是這段時間以來,炎還山遇到的唯一不順心的事了。
不過他想得很開,哪家礦上、哪家廠裡沒有這樣的爛人呢?好吃懶做、遲到早退不說,還盡散播謠言,說礦下頭有鬼,嚴重影響工人的工作情緒,被他狠狠訓斥了之後心生不滿,半夜撬了財務的鎖,順走了近一萬。
近一萬啊,想起來他都心疼。
林喜柔說:「真不報警啊?便宜了這種壞人了。」
炎還山答得更含糊了:「報什麼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畢竟,他這個礦上不乾淨的事太多了,不想把警察往家裡招。
林喜柔沒再吭聲,低頭織了幾行針,偶一瞥眼,發現炎還山沒再狼吞虎嚥了:他咬著筷頭,正瞧向窗外。循向看去,不遠處的坑道口上圍了一堆工人,林喜柔看了眼牆上的掛鐘:十二點半了,下礦的工人們是該上來吃午飯了。她起了個新話頭:「今天礦上大葷是什麼菜啊?羊肉?」
炎還山喃喃:「不對啊,出事了?」
林喜柔一愣,再次往窗外看去,這一次,瞧出異樣來了:往常一到飯點,這群收工的都往食堂跑,竄得比狼都快,但是現在他們三五成群地堵在坑道口,激動地嚷嚷著什麼,留神的話,都能看到被陽光照得賊亮的、噴濺出來的唾沫星子。
不會真是出事了吧?
開礦的最怕地底下出事了,而地底下出事,必然不是刮到蹭到這麼簡單,炎還山心慌慌的,筷子一擱,三步併作兩步衝出了門,隔著幾公尺遠就氣勢洶洶地吼上了:「怎麼了?怎麼了這是?」
這是他多年混出來的經驗:不管出了什麼事,哪怕死了人了,都不能怯、慌、亂,要凶、要開口就能鎮住場子。
這一吼果然立竿見影,嚷嚷聲小了很多,小組長劉三池一張煤黑的馬臉下頭透著煞白:「老、老闆,二狗子沒撒謊,下頭、下頭有鬼咧。」
沒死人啊,炎還山心裡一塊巨石落地,吼得更有氣勢了:「我日。」
林喜柔過來的時候,正聽到炎還山給一干人做無神論教育。
「書裡講得明明白白的,這個世上是沒鬼的。二狗子是文盲,你們也不認字?哪有鬼?把它叫出來我看看!」
剛進礦沒兩天的小後生長喜小心翼翼解釋:「不能叫,大日頭的,我聽說,鬼晒太陽會化成水的。」
喲,這還體貼上鬼了?炎還山氣不打一處來:「一個個嘴咧咧的,都看到了?真新鮮,鬼長什麼樣啊?」
居然真有人答。
毛旺:「長得白生生的,沒看真,嗖一下就閃沒了。」
孫貴:「會發聲,我聽到哼唧聲了。」
韓德福:「我帶下去兩香瓜,兩香瓜都沒了!」
炎還山語帶諷刺:「都做鬼了,還惦記著吃瓜?」
林喜柔心中一動,她扯了扯炎還山的衣角,把他拉到一邊:「會不會是李二狗啊?」她是六○年代生的,和炎還山一樣,接受了扎實的馬列教育,對鬼神之說向來嗤之以鼻,聽到礦下出夭蛾子,第一時間只會往人身上想。
──李二狗是半夜跑的,衣物都沒帶,據說只穿了白汗衫黑褲,「長得白生生的」,莫非就是白汗衫?坑道裡黑漆漆的,白汗衫的白委實顯眼。
──到處都找不到李二狗,就不興他是躲進了礦道?「兩香瓜都沒了」,礦下沒吃的,可不得偷嘛。
炎還山一點就透,一拍大腿:「就他,沒第二個了!」
他心裡有了數,轉過身,話更硬了:「這麼著,我跟你們下去會會這鬼。」
挖礦的多是文盲大老粗,很難跟他們講明白唯物主義,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眼見為實,眾目睽睽之下破了這「鬼」。
可惜的是沒人願意下,獎勵二十塊錢也不下。
不下也好,炎還山轉念一想,覺得自己單槍匹馬下去把李二狗給拖出來更加有氣勢,叫這幫挖礦的看看,能當礦主,手底下不是虛的──威風立起來,以後發號施令就更方便了。
他白眼送出去一圈:「都不敢是吧?等著啊,等你炎哥把它請出來晒太陽。」
人比人得死,在一干垂頭耷腦的礦工襯托下,本就長得英挺出眾的炎還山顯得更加高大威猛,林喜柔心裡美滋滋的,覺得自家男人實在是很拿得出手,直到炎還山的身影都快消失在礦道口了,才想起囑咐一句:「手別太重啊。」
炎還山早年在街頭混過一陣子,手硬腳狠,打三兩個壯漢不成問題,林喜柔怕他氣上心頭,一個收不住,把李二狗給打殘了。
大型的有實力的煤礦,上下有升降梯,坑道間進出有礦車,炎還山的礦小,一切從簡,坑洞口架設了幾組簡易滑輪,所有人用綴吊在滑輪上的猴袋上下。所謂的「猴袋」,就是麻袋底下挖兩個口子,人坐進去之後,兩條腿從破口裡垂出來,再經由滑輪一路降至洞底──因為安全係數低,全程都得蜷著身子盡量不動,看著跟傻猴似的,是以明明是兜人的袋子,偏偏叫「猴袋」。
炎還山跟坑口值班的打了聲招呼,坐著猴袋下了洞。
這礦是從上一任礦主手裡接的,二手貨,上一任挖成什麼樣,到他手裡就是什麼樣,要說有什麼特別的,那就是深,特別深。
也正是因為深,這口礦裡傳的玄乎鬼話兒遠比別的礦多,比如李二狗就造謠說這礦是十八層地獄的入口,還言之鑿鑿說看到過青面獠牙的鬼──這不鬼扯麼,要真是地獄入口,他炎還山還開什麼礦啊,賣景點門票得了,十一億中國人,管保個個都來瞧熱鬧。
下到洞底,邊上就是裝備堆,炎還山撿了把鎬頭,拎上礦燈,進了蛛網般錯綜複雜的礦道。
他對下頭的礦道不太熟,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小煤礦本就不講究繪製什麼坑道圖,而且人工挖礦隨機性太大,有時候挖著挖著覺得不妙、可能會塌,於是隨意拿木棍支一下,換個方位再挖,久而久之,就挖得狗刨豬啃般,沒眼看、也沒腦子記了。
炎還山一路吆喝:「二狗子,自己出來吧,爭取寬大處理啊。」
坑道裡特別黑,礦燈的光左晃右蕩,每次只能照亮小方桌大的一塊地方,但炎還山一點都不害怕,一來天生膽肥,二來嘛,人有什麼好怕的呢?至於鬼,這世上又哪來的鬼呢。
走了約莫一刻來鐘,炎還山吆喝得嗓子都啞了,也沒見李二狗現身認罪,他心下惱火,正想往另一條坑道去,腳下忽然踩到了什麼東西。
這東西溜滑,讓人定不住腳,炎還山猝不及防,哎喲一聲,踩著那玩意滑出幾步遠,然後仰天跌了個結實,這一記摔得他眼前發黑,礦燈的玻璃罩都摔出了好幾條裂縫。
炎還山足足花了五秒鐘才緩過勁來,他拎著礦燈四下一照,很快鎖定了罪魁禍首:是香瓜靠結蒂處的那一塊,難怪溜滑溜滑的。
媽的,哪個龜孫扔的!
炎還山罵罵咧咧,正想起身,忽地怔了一下。
就在不遠處,燈光盡頭,黯淡而又模糊的黑裡,有一雙腳,纖瘦白皙,一看就知道不是男人的腳。
不是吧,礦底下還能有女人?
炎還山下意識拎高了礦燈。
他看到黑漆漆的一團,那真是個女人,赤裸的、蜷靠在角落裡的女人,頭髮又濃又密,遮住了臉和大半個身子,藏在亂髮下的眼睛正一瞬不瞬地盯著他。
說來也怪,這眼睛除了比一般人更亮、更美、更深邃些,倒也無甚特別,但炎還山腦子裡冒出的第一個形容詞,跟亮、美、深邃都無關。
他腦子裡冒出的詞是「新的」──簇新的眼睛,沒使用過的,像嬰兒一般、剛剛被造就的。
炎還山盯著這眼睛看,他發現自己動不了了,那個女人爬過來了。
1992年9月16日/星期三/晴轉陰轉大雨
十點半了,大山還沒回來,外頭雨下那麼大,家裡就我一個人,有點怕。
中午給大山送餃子,遇到一件好笑的事:工人鬧鬧嚷嚷的,說礦下有鬼。
哪來的鬼啊,我猜多半是李二狗。
大山獨個兒下去「抓鬼」,我還挺期待的,不過再一想,未必抓得到:李二狗做了虧心事,哪敢叫大山給找著啊,聽到動靜,早躲起來了。
果然叫我給猜中了,大山白兜了一場,上來說,裡頭什麼都沒有。
十點四十五了。
礦上的事可真忙啊,大山太辛苦了,希望兒子早點出生,快快長大,這樣大山就能多個得力的幫手了。
我最近在給兒子想名字,老愛翻詞典,喜歡上一個詞兒,開拓。
開拓開拓,真好聽,開闢新天地,拓展新道路,敢叫日月換新天。
炎開,炎拓,聽上去都不錯,我真是哪個都喜歡,選不出來。
算了,讓大山選吧。
外頭有聲響,準是大山回來了,就寫到這吧。
──【林喜柔的日記,選摘】
第一章
九月中旬,江南還是流火季,「秦嶺-淮河」一線,已漸入秋涼。
晚上十時許,安開市石河縣興壩子鄉一帶,差不多已是漆黑一片,只西頭一隅有幾點光──周圍山影憧憧,風過林噪,映襯得那亮如撲跌不定的燈苗。
興壩子鄉人慣住鄉東,西頭是野地,解放前修過廟、起過祭臺,還請過巫師禳災驅鬼,後來大運動,砸燒之後便荒廢了,再後來,也不知怎麼的,這兒長出了大片的玉米,可惜品種不行,掰來只能餵豬。
這季節,玉米已經掰得差不多了,地裡只剩一人來高的枯黃秸稈,身桿細瘦,密密麻麻,風一過,嘩啦嘩啦,怪瘮人的。
那幾點光來自玉米地中央朽頹的破廟,以及廟外的越野車。
駕駛座側車窗半開,孫周挾了菸的左手搭在窗沿,正和女友喬亞打電話,因著聊到興起來不及抽,只能任菸空燒,是以每隔一會都要磕掉菸灰。
「鄉下地方,四面一個人都沒有……我跟妳說,我心頭真發毛。」
他瞥一眼周遭,忽然覺得左手露在車外很沒安全感,於是撂了菸,把手縮回來。
喬亞對這地方有耳聞:「是山區吧?我聽我爺說,那一帶解放前是匪區,殺過好多人,還鬧過鬼呢。」
孫周胳膊上冒起一片雞皮疙瘩,下意識左瞄右瞥:左邊是一片黑魆魆秸稈地,秸稈在風裡輕晃,晃出一股子陰怖森涼;右邊是廟,裡頭的光像幽微螢火,緩緩飄移。
「我有什麼辦法,聶小姐要看泥塑,人家藝術家。」
「也怪我,路上走錯道了,到得就晚,聶小姐又看入神了,我不好意思催她……」
他是跑線司機,聶小姐是雇主,走不走,什麼時候走,雇主說了算。
喬亞發牢騷:「看雕塑,怎麼不去龍門、敦煌啊,跑去鄉下……」
孫周說:「不是說了藝術家嗎,那些有名的窟,人家十來歲就全看遍了。現在就流行找這種鄉野、原生態的,觸發創作靈感。」
喬亞沒詞了,頓了頓問:「聽說她雕個像,能賣幾萬?」
孫周其實也沒數,但他裝著很懂行:「藝術能那麼便宜嗎?至少也十幾萬啊。」
喬亞感嘆了會,末了說了句:「這聶小姐膽兒可真大。」
「可不,」孫周很有感觸,「這黑燈瞎火的,又是秦巴山區,我跟妳說,我心裡都打鼓,這要是冒出幾個不法分子把我們給弄死了……」
喬亞沒好氣:「我不是說這個,我是說,她一年輕女的,敢跟你一男的,大半夜跑那麼偏的地方去──她就不怕你起色心、把她給那什麼了?」
「我拿錢辦事,有職業道德。再說了,這都認識幾天了,等於半個熟人。」
喬亞冷笑:「熟人?人家說,性犯罪一半都是熟人下的手,女人防男人,不分熟不熟。反正換了是我,絕對不敢跟一個不熟的男司機大半夜往鄉下跑,男同事、男同學都不行。」
孫周涎了臉:「那我呢,我行不行?」
喬亞也發了嗲:「你行。」
孫周心上胯下同癢,正想說兩句騷話,忽然看到車左的後視鏡裡掠過一個黑影,他嚇得一激靈,手機都掉了:「誰?」
回應他的,是風過秸稈地的嘩啦聲響。
孫周打開車門,四下看了一回,覺得那玉米地裡似乎什麼都沒有,又似乎什麼都有。
撿起手機,通話還沒斷,喬亞已經發了急:「怎麼了?誰啊?」
孫周後脊背上一陣泛冷:「不說了,我去……催催聶小姐。」
他掛了電話,小跑著往廟裡去──他雖然身高一八○,看著壯實,但那是虛壯,真出什麼事,他罩不住,更何況,還帶著這個弱不禁風的聶小姐。
廟不大,穿門過院就是正殿,早些年砸燒過,後來文保局著手修復,修復到一半,不知是缺少資金還是覺得意義不大,又放棄了。
正殿的供檯上擠擠挨挨的都是泥塑,那位聶小姐,聶九羅,著白襯衫、黑色緊身褲,正跨坐在一架可攜式鋁合金伸縮人字梯頂端,左手持手電筒,仔細打量一尊泥塑的眼眉,腕上晃著極細螺紋多圈手環,泛柔潤銀光。
廟內昏暗,手電筒的光柱裡飄著上下浮蕩的塵。
孫周還記得,傍晚到的時候,這些泥塑都還滿覆灰土,但現在她打量的這尊眉眼分明,色彩也凸顯,顯然是清理過了。他叫了聲:「聶小姐。」
聶九羅回過頭來。
她二十五、六年紀,身量苗條,一頭漆黑長髮,冷白皮。髮色是真黑,黑到發亮;皮子也是真白,瓷白冷調,質地好到搽什麼粉霜都是多餘,所以她用酡紅色的口紅──皮冷的人唇色偏淡,不搽口紅,總會透出些疲弱的意味來。
這一回頭,也同時露出那泥塑的臉,這泥塑雖殘卻美,不過美得不端莊、形似妖魅,聶九羅的瀏海低低壓著眼眉,烏黑眸子,雪膚紅唇,恰側在泥塑臉邊。兩張臉,一個活人,一個死物,一個肉胎,一個泥質,孫周晃了神,覺得聶九羅的臉比之旁側那張,更多點懾人的魅氣。他想起喬亞說的見色起意,心說:就算真有機會,我也不敢把她那什麼了。
「聶小姐,都十點多了,我們先回去吧,明天再來,這一帶治安不是很好,路況也差……」
聶九羅一點就透:「好,我拍幾張照片就走。」
拍完照片,孫周收拾好梯子什物放進後車廂,闔上車蓋的時候,他回頭看了看。
似乎有什麼聲音,嗚咽幽怨,像是女人在……啜泣,孫周被自己的聯想嚇得周身汗毛倒豎,飛快地鑽進車子。
聶九羅坐在後排,正仔細看剛才拍的照片。
孫周清了清嗓子:「聶小姐,妳有沒有聽見什麼……怪聲啊?」
聶九羅奇怪:「什麼怪聲?」
果然,孫周也猜到了不能指望她:這些搞藝術的人都太投入了,一旦沉迷起來,敲鑼打鼓都驚動不了。他岔開話題:「不是,妳是外地人,不知道……這一帶,以前叫南巴老林,土匪殺人,陰氣重……」
聶九羅說:「我知道,南巴老林嘛,以前是原始森林,從東漢開始就禁革山場,『遍山皆是海,無木不成林』,清朝的時候湧入大量流民,白蓮教變亂就是從這起的,再後來土匪盤踞,建國後才被肅清。」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梟起青壤(一)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梟起青壤(一)
秦巴山區,舊屬梁州,又稱南巴老林,
也不知為何,人跡罕至的鄉西一帶,
近日來了個小有名氣的女雕塑家聶九羅,
只見她雇請司機,訂製行程,
在陜南四處采風,且專挑僻靜處去。
好巧不巧,在一間荒廢破廟附近,
還有另一位打眼的外來客──
純白色越野霸氣拉風,車裡卻坐了隻毛絨鴨子,
而這位高大耐看的車主拖著可疑的行李箱,
大概是與她路線重疊了,動不動兩人就再次碰上。
她有胎裡帶出來的本事,迫於債務,
不得不以勞力償還,上不了岸;
他表面看似風光,名下產業眾多,奉公守法,
實則是在為虎作倀,身不由己。
他們兩人的初遇,實在談不上愉快,
後續,又會引發什麼樣的連鎖反應呢?
商品特色
◎奇詭懸疑,部部精妙──身兼小說巨匠、編劇大手的尾魚老師,新作《梟起青壤》再次融匯古今,帶領讀者抽絲剝繭,解鎖奇聞異事!
◎本書改編之同名電視劇,已於2024年春火熱開拍,敬請期待!🎬
◎她和他不打不相識,沒承想,這一場相遇,竟還能溯源至上古時期?!
◎前塵諸事紛繁如迷霧,線索又要往何處尋覓?他們皆將所求藏於心底深處,最後,是否能如青壤結穗,開花見果……
◎隨書附贈封面圖明信片。
詭情大師尾魚最新作品,同名電視劇火熱開拍中!
冷情富二代╳新銳雕塑家
有刀有狗走青壤,鬼手打鞭亮珠光──
史料記載,這片土地莽野林深,顆粒難收,
卻有一種凶獸,似乎只在此處,才能孕育而生。
作者簡介:
尾魚
熱衷一切奇思怪想的軼聞,相信世界的玄妙大過眼睛,熱愛旅行,尤喜探險,身體跨越不了的險境,就是筆下故事開始的地方。
章節試閱
引子
一九九二年,陝南由唐縣,老牛頭崗。
炎還山一大早就出了門,蹬著自行車跑了大半個縣城,給七、八家白的黑的「有關單位」送了禮──他在崗西盤了個小煤礦,資格證明不夠、手續不全、嚴重違規,不私下孝敬的話,立刻就得關閉。
不過話又說回來,這年頭,國家經濟才盤活,且「活」得有些迅猛,各項法規跟不上,就得靠人情和關係走天下。
一個上午,炎還山送出去兩、三萬,不過他非但不心疼,還美滋滋的:關係打通了,礦上的事就好辦了,媳婦林喜柔懷孕了,托人做了超音波,說是個男的。
男的哎,帶把兒的,老炎家有後了!
事業家...
一九九二年,陝南由唐縣,老牛頭崗。
炎還山一大早就出了門,蹬著自行車跑了大半個縣城,給七、八家白的黑的「有關單位」送了禮──他在崗西盤了個小煤礦,資格證明不夠、手續不全、嚴重違規,不私下孝敬的話,立刻就得關閉。
不過話又說回來,這年頭,國家經濟才盤活,且「活」得有些迅猛,各項法規跟不上,就得靠人情和關係走天下。
一個上午,炎還山送出去兩、三萬,不過他非但不心疼,還美滋滋的:關係打通了,礦上的事就好辦了,媳婦林喜柔懷孕了,托人做了超音波,說是個男的。
男的哎,帶把兒的,老炎家有後了!
事業家...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