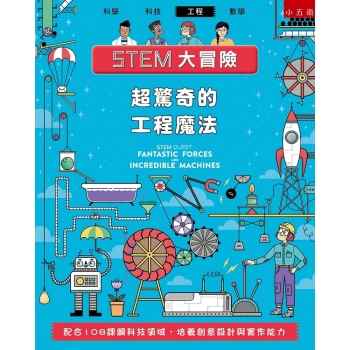穿越鬼斧神工的金人門,秦時鋪就的夜光石,
在兩千多年來散發著微光,幽幽引領來者走入地下,
自遠古時期便結下的血仇,這最後一役,
竟是由地梟叫陣,約定雙方在澗水邊進行決戰。
然而,抵達地下的兩方人馬還未來得及碰頭,
變故陡生,他們分別遭到有序的猛烈圍攻,
炎拓與聶九羅一路逃竄,被長著白瞳的敵人緊咬不放,
情勢危急下,聶九羅瘋刀聶二的身分再也無法掩藏,
她只能選擇透支己身,為所有人斷後。
纏頭軍,纏頭鬼,黑裡別逢,白裡莫見──
身周餘音猶自嫋嫋,地底深處澗水狂號,
炎拓幾經險阻,終於又趕赴至聶九羅身邊,
他們都找到了牽掛的人,但是,
失去的,終究早已徹底失去……
本書特色
改編電視劇已殺青,詭情大師尾魚新作感動收官!
冷情富二代╳新銳雕塑家
恍如隔世,恍然如夢,陰兵過道,陰陽相隔……
她折了一生的星,像是都在此刻落了下來。
那個小院子曾等回了他,將來也能等回聶九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