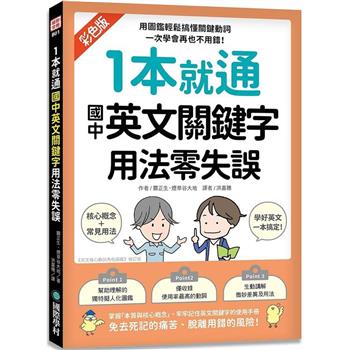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雖及時阻止魔教造成師門致命災禍,
但還沒等蔡昭將整件事想明白,又傳來壞消息──
數個門派在參加完祭典的回程途中,遭魔教襲殺!
而就在蔡昭見到安然無事的父親,正自慶幸的隔天,
父親竟離奇失蹤,留下空蕩的客棧與滿地屍體,
且從種種跡象來看,只會是熟人下的手……
她的姑姑十五歲已名動江湖,如今她卻只想保護家人,
生平第一次,她獨自做了選擇。
擔心至親安危,蔡昭決定主動出擊。
沒想到在與常寧的追查過程中,
發現傳說中能以假亂真的「易身大法」重現江湖。
這下麻煩大了!
除了身旁這個已知的冒牌世兄常寧,
青闕宗中還有誰是假冒者?又有誰可信?
此術號稱除死無法可破,
她的推測、指認,要如何取信眾人,力挽狂瀾?
本書特色
{關心則亂}《知否》、《星漢燦爛》作者首部武俠大作,
同名電視劇即將殺青!
詭道潛行真亦假,俠心臨照假亦真。
怎會這樣?本應全心信賴的師門變得處處可疑,
而一路相伴、助她追索真相的卻是這個冒牌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