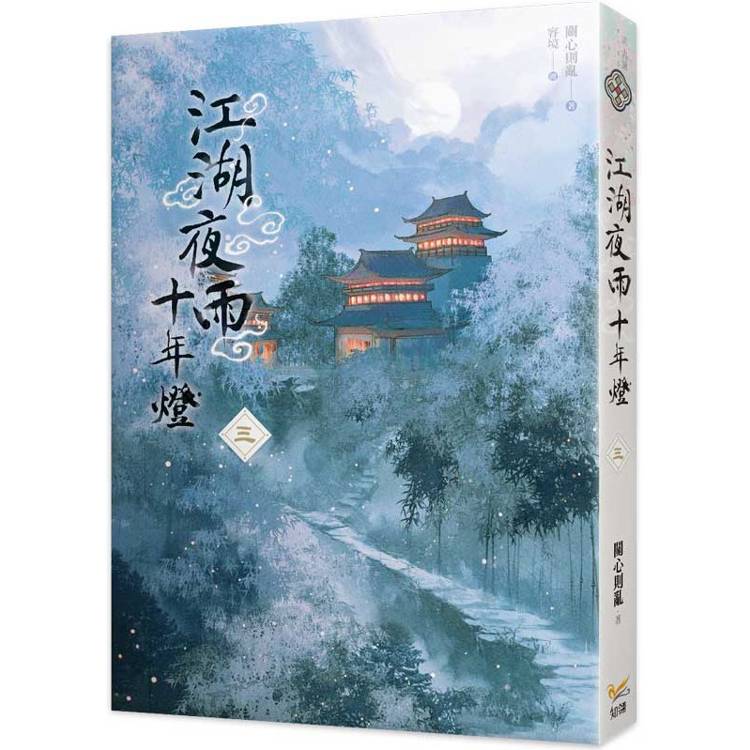蔡昭萬萬沒想到,一場雪山尋藥之行,
最後竟是這般收場。
什麼正邪不兩立,利欲薰心之下只有狼狽為奸!
反倒是身旁這個慕清晏,雖是魔教少君,
卻又是援救雪獸幼崽,又是不顧生死助她脫困救人。
過往她聽江湖,只覺暢快淋漓、熱血豪邁,
可當她入了江湖,當那些「故事」落到了實處,
她其實很感激,有他伴著自己一路毅然前行……
取得雪鱗龍涎後,易身大法之亂順利弭平,
不過似有幕後黑手仍隱伏暗處,對北宸六派虎視眈眈?
可想到慕清晏放下自身復位中興大計,
遠赴雪山,只為護她周全,
而今卻傳來魔教內部情勢詭譎、人馬蠢動的消息,
蔡昭決意先去助「孤零零」的慕清晏一臂之力。
但當她一路提心吊膽,冒險殺進敵軍陣地,
再見時,這廝居然──翻臉了?!
本書特色
{關心則亂}《知否》、《星漢燦爛》作者首部武俠大作,
同名電視劇正式殺青!
天道循環,因果自成;
善惡有報,不平當鳴。
為善作惡,最終總該有個說法。
天理昭昭,她蔡昭既知道了,又怎能視而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