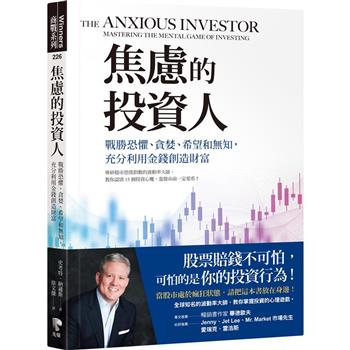一個青年生命的夭亡
開啟了通往遠古詛咒之門
但解謎的代價,是否生死兩字了得?
一切都起因於一筆語焉不詳的文字記載。一對來自東台灣的阿美族姊妹,一個來自高山的布農族與鄒族混血青年,以及一個賽夏族的都市原住民,四個年輕人在科學昌明的二十一世紀,共同追查一起向天湖畔的離奇死亡事件,卻在不知不覺間接近遠古詛咒的核心,曝露在無情的死亡陰影之下。詛咒彷彿攜手前來,牢牢綁縛著四顆青春之心,直到十二年後,那些關於遠古與當代的傳說,依舊是道近乎無解的人生難題……
作者簡介:
Nakao Eki Pacidal
花蓮太巴塱部落(Tafalong)阿美族人。曾翻譯《公司男女》、《地球寫了十億年的日記》、《西班牙人在台灣》等學術或科普書籍。目前為荷蘭萊登大學歷史學博士候選人,研究主題為原住民角度的台灣史觀。此外兼職寫作、翻譯、繪畫並參與原住民運動。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孫大川(卑南族)
考試院委員浦忠成(鄒族):
這是試圖運用原住民族神話傳說、儀式、禁忌、記憶素材重構/再創敘事情境的作品。族群圖像、記憶與文化內涵,毫無滯礙的跟現在的時空連結,似真卻假/如假又真。由使用的題材、敘事的結構、行文運辭與思考的脈絡以觀,作者已然超軼現階段原住民作家慣常說故事或描述情狀的手法。
國立東華大學台灣系教授康培德:
《絕島之咒》是虛構的小說,背後有著對現實的反映,也有歷史文化的結構包袱。作者取材台灣原住民數族的口傳故事,改寫成整個故事詛咒的框架,之後四個原住民族青年,就在這個詛咒的結構內發展他們的人生故事,反映著1970年代出生的作者對自己身負的原住民族文化的思考。
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教授童元昭:
書中主角騎著單車,或搭飛機跨越既定的領域,書中人物或傳說故事直接、間接包括了多數的原住民族,非原住民的人物僅有少數幾人。里美與海樹兒在信中以日文通心意,與Key則以英文溝通。小說建構了一個以原住民為主體的世界,帶來類似於當年台語搖滾的新穎眼光,原住民與世界直接接軌,不需要經過其他語言、人群的中介。
【推薦序一】
解咒、伴咒之旅
Pasuya poiconü 浦忠成 (鄒族)
咒,原意是禱告、毒罵,或驅鬼除邪的口訣;在Nakao這部小說則是強調在某種情況下有些人受到命定的或後天的制約、束縛而難以掙脫一種宿命,復與詛咒有關。它是由族群、血緣、寄望、因緣、際遇、憧憬、執著促成,而由某一詞語、數詞、型態、顏色予以定住,注定要讓人在其牽涉的範疇掙扎、匍匐、翻滾,身體的傷痕不計,更痛的是難以言宣、中夜獨嘗的苦楚,甚而喪命。小說中的幾個角色原本要一起去探尋、解密一樁死亡的意外,卻不期然察覺在一己所屬的古老傳說、事件中,已經在各自的身體、命運植入難以脫卸的咒體。嘗試解開某個人遭遇的咒鎖,卻逐一發現各自都有先天或自取的咒,相互糾纏、牽扯,惟其過程中又有不時出現的人性溫潤與相濡以沫,從而在探尋答案、嘗試脫困中,逐漸體悟人生、人性的真相。
場景由花蓮壽豐的志學村開始拉出,揭開序幕的是就讀東華大學研究所的阿美族馬太鞍的女生高洛洛與布農、鄒族混血的男生阿浪到春上村宿會面,討論論文牽涉的洪水故事。不久,阿浪被發現陳屍在苗栗賽夏族祭場旁的向天湖畔。高洛洛與表妹里美、阿浪的弟弟海樹兒及賽夏族的芎於是展開阿浪死因的調查。阿浪的意外死亡讓幾個試圖調查真相的四人由鄒族洪水故事中持弓遠走的maya、賽夏族與矮人、邵族追逐白鹿,繼而遷住拉魯島等傳說情節裡試圖解謎,終而未能找到任何蛛絲馬跡,卻赫然發現,調戲賽夏婦女的矮人遭設計滅族而衍生的忿怨,遠古的忿怨竟持續施展無以終止的懲罰、報復,阿浪之死只是開端。
然而由此開始,四人的關係與命運緊緊牽繫。高洛洛一直不能忘情於曾經對她很好的阿浪,於是不再鑽研巫術,而以其他四平八穩的論題獲得碩士學位;之後想以流傳東部的黃金密藏深山傳說繼續攻讀博士,於是萬榮太魯閣族的阿維帶領她入山探訪,高洛洛卻因尋路摔成嚴重腳傷,阿維辛苦將她揹回,經此一事,加上荒木教授的開示,高洛洛開始放下名字與身體的執念,打開心門,終於接納阿維。
初見即互有好感的海樹兒、里美,順理成章的成為情侶,卻在海樹兒帶著里美回家稟告父母時發現,里美竟然是父親外遇時生下的孩子。已然相愛的兩人,卻是兄妹血親,這是兩人難以掙脫的詛咒。傷心離台赴日的海樹兒,到京都繼續深造,決心從事戲劇工作,之後認識同樣在日本求學的魯凱族人夏瑪,兩人結婚,卻因夏瑪難產去世,又讓海樹兒面對生命孤獨。里美曾有多人追求,而條件非常傑出的排灣族裔美國人Key熱烈表白,兩人並曾到蘭嶼共度假期,最後卻沒有能夠結為連理。沉穩、冷靜又體貼的芎,未及完成大學植物系的學業就離校當兵,接著貸款以芎作為品牌創業,以其熟悉的植物知識設計家具、飾品、奢侈品,很快就開拓出事業的天空;事業有成後,他慷慨地幫助始終敬重他的海樹兒以及里兒,甚至幫助部落的產業,但獨特的性向讓他決定一生獨身,這也算是他的生命之咒困。至於荒木教授、阿維、Key不是咒圈中人,卻都適時出現,以言詞、行動支持與轉換咒圈中人的陷溺。沉浸戲劇的海樹兒、走入平凡家庭生活的高洛洛、商界得意的芎、自我放逐於南太平洋島嶼的里美,都在生活與時間的淬鍊下,有了一番新的體悟,咒的束縛於斯解除。結尾,芎往京都拜望已經走到生命盡頭的荒木教授,而里美也將造訪出雲。至於後來如何?作者只留下山吹花海的景象。
這是試圖運用原住民族神話傳說、儀式、禁忌、記憶素材重構/再創敘事情境的作品;誠如作者自言:這是一本小說,是個虛構的故事。不過,阿美族/馬太鞍/太巴塱/加里洞/壽豐/巫術、太魯閣/萬榮/賽夏族/矮人/矮靈祭/芎/向天湖/南庄/獅潭、鄒族/洪水/玉山/maya/分手之弓/日本/和社、布農族/邵族/日月潭/拉魯島等族群圖像、記憶與文化內涵,毫無滯礙的跟現在時空中的東華大學、台灣大學(植物系、戲劇所、日文系)、論文、春上村樹、《舞、舞、舞》、春上村宿(花蓮壽豐志學一旅館)、遠企、東大教授、人類學、考古學、語言學、京都、出雲寺、山吹連結,藉著咒的線索與人物的穿梭,交織成樸朔迷離、似真卻假/如假又真的虛幻/真實、部落/都會、原/漢混融的情境。由使用的題材、敘事的結構、行文運辭與思考的脈絡以觀,作者已然超軼現階段原住民作家慣常說故事或描述情狀的手法,冀望以點睛式的傳說情節遞出原住民族文化經驗與智慧的吉光片羽,卻又隱藏不住她其實熟悉都會與勇闖學術的特質與雄心;而最令人驚嘆的是情節扭轉之聳奇,如情侶竟是兄妹、摯愛不能長守、親人有難言之隱,全然出人意表,卻也透盡人性。儘管小說中人物、牽涉極多,其中隱約似有作者Nakao影子。坦白說,這部小說要沒有一定的先修常識還真不容易讀呢!
印象中的Nakao Eki Pacidal是聰敏而具才情、膽識的阿美族女子,偶而在某些不期而遇的場合,總會提出讓人摸不著頭緒或高難度的問題或是見解,我知道她自有一套自己的思索進路,不勞他人置喙與解答。聽聞前幾年到哈佛念了碩士回來,不久驚見書坊已經陳列她翻譯並出版的質量俱豐的學術著作。而今又在荷蘭萊登大學深造之暇,還能從容提筆『攪亂』文學一下,這就是她的高明之處!有幸首先閱讀這部精采的長篇小說,在讚賞Nakao以文學素人姿態敢於突破窠臼、忌諱,為原住民族文學另闢蹊徑之際,我很樂意寫下這粗糙的序文推薦之。2014.7.23麥德姆颱風襲臺之日書就
【推薦序二】
被詛咒的福爾摩莎?
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教授康培德
2014年的台灣,我們除了目睹政府官員的「鬼島」事件餘波蕩漾,也經歷了新生代「黑島」青年(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的行動洗禮;如今,又來個遭詛咒的「絕島」,不禁要問,這個島國發生了什麼事?
《絕島之咒》這本小說,與「鬼島」、「黑島」一樣,在黨國復辟的背景下,於今年出版問世,呈現在大眾眼前。不同的是,《絕島之咒》是虛構的小說;不過,虛構的背後,有著對現實的反映。更不同的是,小說中有更長時期的歷史文化的結構包袱。
作者取材台灣原住民數族的口傳故事,改寫成整個故事詛咒的框架,之後故事的主角,也就是四個原住民族青年,就在這個詛咒的結構內發展他們的人生故事。
小說的四名主角,反映著1970年代出生的作者對自己身負的原住民族文化的思考。這些原住民族青年主角們,不論有無部落生活的經驗,都與他們的長輩不同,具有相當的「當代性」。他們受過高等教育、熟悉部落以外的世界,有能力與台灣主流社會打交道,甚至可以在國外生活,獲得相當的成功。這樣的小說內容,顯然來自新一代原住民族的生活經驗,這也表示一個新世代的原住民族小說書寫型態正在萌芽。
不過,這個新的原住民族世代,顯然是一個夾在傳統與現代之間,不無迷惘的世代。故事主角們遇上現代科學無法解釋的難題,每個人身上都背負著不同的詛咒,儘管他們都想在母體文化裡求得解答,但原住民族文化裡詛咒和巫術的傳統一去不返之後,這些年輕人也只能各自尋求出路。這樣的情節,正是原住民族在當代世界裡生存的寫照。
小說另一個值得注意之處,是故事裡刻畫的當代原住民族文化。小說主角分屬數個不同的語族,因探究友人死亡的迷團而彼此結為至交好友。透過小說中這幾名青年所呈現的社會關係,是年輕一代的「泛台灣原住民族」人際網絡與認同,並夾雜著日本文化元素,反映出五十年日本統治在台灣原住民族文化裡留下的痕跡。故事中不僅出現日本人荒木先生,也有取著日本名字的原住民,具有日本建物風情的原住民部落,主角之一為了躲避來自「絕島」的詛咒,甚至避走日本。
小說揉和了追蹤遠古詛咒之謎的懸疑情節,以及多數小說都難免碰觸的愛情故事。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小說裡的愛情故事,是一個亂倫的困境,內情其實比表象複雜。亂倫並非文學裡的新鮮題材,但小說花了相當篇幅,描寫兄妹間在「要」與「不要」掙扎的戀情,暗示著文化上的兩難抉擇。小說裡將這個文化上的兩難,透過一位旁觀的局外人、日本教授之口一語道破:「亂倫在現代的社會裡不被接受,但在遠古時代,卻是人類血脈延續的唯一手段。」這句話等於明白的告訴讀者:這對兄妹對彼此愛情的選擇,就等於是在「接受現況」和「重新開始」之間的選擇。用亂倫這麼極端的情節來表達這一點,小說想表達出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的延續和重生,所要付出的代價有多麼巨大。
其實,在「接受現況」和「重新開始」之間掙扎的,不只是台灣原住民,台灣全國人民也面對著類似的問題。或許在讀小說之餘,我們也可以想想,維繫這島嶼生存的代價到底有多大?重重困難是否有如詛咒?我們到底要如何抉擇?
【推薦序三】
咒作為生機和愛而釋然
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童元昭
第一次知道 Nakao 是在一場研討會上,她清晰的表達出跳脫學科規範的獨特觀點。我又看到Nakao畫的畫。再來是寫歷史論文、會畫畫的Nakao寫小說了,還只是一系列的第一部而已。
從一開始,書中幾位主要人物的族裔背景、活動空間,便動搖了一般人所認為原住民與土地之間刻板的連結。每一個人都在路途上,或者曾經離開家,書中人物不斷的穿越空間的界線,去了加里洞、信義鄉和社、南庄、台北、京都、蘭嶼,以及復活節島。在新的環境中,不同的人遇合,甚至出現新的族裔身分,里美是阿美族母親與布農族父親所孕育的阿農族。族裔身分雖然有官方的認定,但在生活往來中、外貌上並不容易一目了然。作者塑造出了不矮的排灣族、不黑的魯凱族與不常笑的阿美族等。
即使書中主角騎著單車,或搭飛機跨越既定的領域,書中人物或傳說故事直接、間接出現包括了多數的原住民族,而非原住民的人物僅僅有日本教授、東華教授與客家餐廳老闆等少數幾人。里美與海樹兒兩人在信中以日文通心意,而她與Key則以英文溝通。小說建構了一個以原住民為主體的世界,這個全面的、嶄新的安排,帶來類似於當年台語搖滾的新穎眼光,原住民與世界直接接軌,不需要經過其他語言、人群的中介。
不只是經驗上, 原住民與世界連動,文化生活也有普世的面向。書一開頭集中在矮靈的傳說,似乎很古老,但作者又從神話傳說的細節比對中跳出來,帶進當代種族屠殺的觀點,將充滿特定文化意義的傳說,與人類歷史上未曾間斷的現象
連結起來。而里美與海樹兒兄妹之間的愛意,也呼應了許多創始神話中第一對夫妻的原型。
我第一次看這書時是半夜,矮人的詛咒帶著綿延不絕的恨,令人背脊發涼,雖然作者接連又提到名字的詛咒、黃金之咒等,但當芎對植物設計的專注也被里美看做是一種咒時,咒的神祕氛圍就退散了,浮現的是可以化解的執念。芎擔負起矮人消逝的歷史,藉著植物的形式在四處引入生命;高洛洛面對了失去父母的幼年,追求簡單的家庭幸福;而受困於兄妹戀情的里美,則遠到太平洋東端的復活節島,在不見盡頭的大洋的包圍中,尋求平靜。
Nakao一直跳脫既有的範疇與規範,書中原住民人物的流動性與普世面向,以及非刻板印象的族裔刻劃等,也都不落入習慣的期待。舊有的詛咒在個人意念的轉換下,產生了新的意義,成為生機,成為愛而釋然。太平洋或許因為它的廣闊與流動顯得不受限制,提供了想像一個更好世界的源頭。那裡島嶼的居民也困於他們的詛咒,在其中也試圖掙脫。視既有為阻礙,嘗試新的可能,不斷超越不也是每一個人都有的力量?
【作者語】
這是一本小說,是個虛構的故事,故事裡隱藏著一個當代台灣原住民寫作者的歷史觀,以及作為一名生活在「文明世界」的原住民,對原住民文化未來的看法。這個故事開放式的結局,其實是向讀者提問:在那樣極端的兩難裡,究竟如何抉擇?讀者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大概就是對台灣原住民文化未來的期待或想像吧。
名人推薦: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孫大川(卑南族)
考試院委員浦忠成(鄒族):
這是試圖運用原住民族神話傳說、儀式、禁忌、記憶素材重構/再創敘事情境的作品。族群圖像、記憶與文化內涵,毫無滯礙的跟現在的時空連結,似真卻假/如假又真。由使用的題材、敘事的結構、行文運辭與思考的脈絡以觀,作者已然超軼現階段原住民作家慣常說故事或描述情狀的手法。
國立東華大學台灣系教授康培德:
《絕島之咒》是虛構的小說,背後有著對現實的反映,也有歷史文化的結構包袱。作者取材台灣原住民數族的口傳故事,改寫成整個故事詛...
章節試閱
第二編 第一回
四月是雨的季節。台大校園裡正稀稀落落的下著不用撐傘也淋不濕的雨。在椰林大道口不遠處,一個穿著白色短袖T-shirt和牛仔布荷葉邊短裙的少女,站在開滿細密白花的流蘇樹下,抬頭望著這細長形的花朵,呆呆的出神。
「Rimi,在看什麼呢?」背後突然有個男生的聲音傳來。
里美轉過頭去,是她已經等了一陣子的海樹兒。比起四年前剛認識的時候,海樹兒又長高了一些,站在旁邊的里美顯得個子更小了。海樹兒越過里美的肩膀,伸手去摸流蘇花上的雨珠,對里美笑了笑:「真漂亮,是不是?」
「嗯,流蘇真的很漂亮,聽說有個別名叫做四月雪。」
「哈,四月雪。四月雨都下不完了,現在又要下雪。」
「Nīchan,今天找我有什麼特別的事嗎?」
「今天⋯⋯」海樹兒嘻嘻一笑,「今天要請你吃晚餐。我已經訂好餐廳位子了,現在就過去吧。」
「為什麼要請我吃飯?該不是要我替你做什麼事吧?」
「怎麼會、怎麼會呢!」海樹兒笑著,拉著里美就走,「我們慢慢走過去,到的時候剛好可以入座。我可是算得很準哪。」
「就這樣淋著雨走過去呀?」
「沒聽過老歌嗎?I’m singing in the rain, just singing in the rain...」海樹兒唱著,竟然學起Gene Kelly在椰林大道上跳起舞來,只是他的動作亂七八糟,手上也沒有雨傘,里美忍不住「嗤」的笑出來。
里美看著海樹兒,啊,沒想到短短四年的時間裡,一切竟然有這麼大的變化。十六歲那一年,表姊高洛洛的研究所同學阿浪在向天湖意外死亡,後來她們認識了阿浪的弟弟海樹兒和海樹兒的學長芎,四人就此展開了一段阿浪死亡事件的調查之旅,只是事情的收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高洛洛放棄了她一向以來立志研究的馬太鞍巫術傳統,休學了整整一年,之後才為自己訂下新的研究題目,也獲得指導教授的同意,之後專注在課業上,在今年年初順利拿到學位了,只是還沒有決定接下來的動向。一直是個日本迷的里美,在高二那年聽從高洛洛的建議,轉學到台北,立志要考上跟海樹兒一樣的台大日文系,憑著她的聰明和專注,竟也如願以償了。海樹兒則是在日文系畢業以後選擇了唸台大戲劇所。「在現代的社會裡,巫師的體質或許在劇場裡最能獲得無害的發揮吧。」海樹兒這樣說。
他們當中最奇怪的或許就是芎了。芎連植物系都沒有唸完就去當兵,之後竟然將方向轉了一百八十度,去辦了創業貸款,開公司做起生意來了。他利用植物系學來的一些知識,專門研發一些圍繞著植物取材的產品,從家具、一般飾品、奢侈品到以植物為主軸的各種設計,幾乎無所不包,他以自己的姓「芎」來當作品牌,把生意做到日本去,頗受日本客戶的好評。
因為都在台北的關係,里美、海樹兒和芎經常碰面。自從上了大學以後,里美和海樹兒同在一個校園內,光是走在路上遇到的機會就不少。里美的日文系同學對於經常跟她走在一起的這位學長大感興趣,經常私下盤問她,「你們到底是什麼關係呀?」、「你都叫他nīchan耶,好親密哪」、「學長很帥呢,你不要的話就讓給我嘛」,等等,不過里美總是一笑置之。她還記得四年前高洛洛勸她「好好把握」海樹兒的時候,她自己說過一切要隨緣的話。在十六歲那一腳還在孩子的世界裡,一腳卻已經踏入成年的年紀,阿浪之死所帶來的一切經驗給了她很大的衝擊,使她對人生有了全新的看法。這世界上沒有任何一件事可以強求,如果不是水到渠成的話,努力也只是誤用人生而已。
兩人走到海樹兒預訂的餐廳時,本來就很小的雨已經完全停了,只有地面還有些濕漉漉的。里美抬頭一看,是一家新開的餐廳,看來內部裝潢相當新穎,燈光明亮,從外面看進去,屋內似乎到處都是植物,好像溫室一般。
兩人才一進門,就看到西裝筆挺的芎坐在裡面靠窗的一桌向他們招手。
「Senpai!」里美還是維持著四年前對芎的稱呼,「怎麼連你也在啊?今天到底有什麼事呢?」
「哈,你自己不知道啊?今天是你生日,請你吃飯哪。選在這邊,因為這家餐廳有一部分的設計是我公司做的,請你們來看看。今天我買單啦,你們兩個愛怎麼吃就怎麼吃吧。」自從當了生意人以後,芎就經常將笑容掛在臉上,再也不像以前那樣老是面無表情,眼神也緩和多了,不像四年前那般銳利,令人看了不安。
「啊?今天是我生日嗎?」里美呆了一下,這才想起今天是四月十號,確實是自己的生日沒錯。她環顧了一下這家餐廳,果然設計得十分別緻,穹形的玻璃屋頂上搭著透明的架子,不知道是什麼藤蔓植物從上面垂掛下來,搭配著吊得高高低低錯落有致的燈,製造出奇異的光影效果,確實很有芎的風格。
「Senpai真是厲害呀,什麼樣的設計都想得出來呢。」里美讚嘆的說。
「哎,做生意是最無聊的,整天就是面對一些鳥事。這世上的北七很多,偏偏都是你的客戶,那這世上的天兵呢,又經常是你的同事。無奈啦。」
「學長不適合跟一般人打交道。」海樹兒開玩笑的說,「學長太特立獨行了,做生意豈不是找自己麻煩嗎?」
「哼,說得輕鬆哪,我不做生意,你們幾個哪天有個三長兩短的時候,誰去籌錢救你們呀?」
三人說得哈哈大笑,吃了相當輕鬆愉快的一餐。晚餐將要結束時,芎和海樹兒分別拿了禮物出來,讓里美大感意外。「請吃飯就夠了,怎麼還送禮物啊?」
海樹兒和芎對望了一眼。「Rimi,你頭昏啦?你不知道你今天滿二十歲嗎?」
「嘎?」里美呆了一下。是啊,今天可不是二十歲的生日嗎,怎麼竟然忘得一乾二淨了,看來是太專注在課業上了吧。
「拆禮物吧。」芎說著,把兩人的禮物都推到里美面前。
芎的禮物是個扁長形的盒子,包著看來很高貴的包裝紙,上面還紮著緞帶。打開一看,是一條粉紅灰色的絲巾,顏色和質料都非常高雅特別。
「Senpai花了多少錢哪!」里美有點吃驚,「這樣的絲巾很貴吧!」
「你管他,學長有的是錢啦!」海樹兒說著用手肘推了一下芎,連芎也忍不住笑了:「你放心啦,到時候也少不了你的。」
海樹兒的禮物是個小小的盒子,看來應該是首飾一類的東西。里美打開一看,是一對非常細緻的金耳環,做成花的樣子。
「認得出來這是什麼花嗎?」海樹兒問。
「嗯,好像在哪裡看到過哪,可是想不太起來。」
「這是yamabuki,是春之花。」
「啊,就是山吹啊!」里美眼睛一亮,「nīchan,這是真金嗎?這可是比山吹色還要亮麗不知道多少倍了!怎麼給我這麼貴重的禮物啊!」
「生日快樂啊,Rimi,二十歲了呢!」海樹兒看著里美,滿眼都是笑意,卻又伸手把里美的頭髮抓亂了,「什麼時候才要留個女孩髮型呢?」
「我這樣不好嗎?」里美摸摸自己的頭髮,「我喜歡短髮嘛。」
「好,好得很!」芎插嘴進來,「你就是剃光頭,你Haisul nīchan也覺得好⋯⋯」
「學長!」
芎哈哈大笑,向服務生招手。「我買單啦,另外還有事。兩位請自便,慢慢走回去,椰林大道上還多得是杜鵑花瓣可以排字呢!」
里美收拾了東西,正要起身時手機響了,她拿出來一看,是高洛洛打來的。
「Nēchan!」里美接了電話,興高采烈的說,「你打來得剛好,我才剛跟Haisul nīchan和senpai吃晚餐呢!你要不要跟他們說話?」
「不用了。」電話那端高洛洛的聲音聽起來沒有什麼不高興,但也說不上有什麼高興的感覺,「就是打來祝你生日快樂的,二十歲了,恭喜你呀。最近一切都好嗎?」
「都好都好。」里美一邊講電話,一邊向芎揮手道別,跟著海樹兒出了餐廳,「你呢?舅舅、舅媽都好嗎?」
「大家都很好。那⋯⋯,下次你回家我們再聊吧。幫我跟他們兩個問好。再見啦。」說著高洛洛竟然就掛斷了電話。
里美登時愣住了,「怎麼這樣?Nēchan沒頭沒尾的,講了幾句就掛掉了啊。」
海樹兒想了一下,「你上次回家是寒假吧?春假也沒回去。要不要最近回去一趟?她現在或許正在迷惑接下來的路。你不在身邊,她沒人可講,回去陪她幾天也好。」
里美點點頭。「那乾脆翹課一周好了。」
「我跟你一起去。」海樹兒說,「我也好久沒去馬太鞍了。」里美低頭笑了笑,沒說什麼。海樹兒抬頭一看,一彎新月高掛在雨後無雲的天空,簡直就是他的心情寫照。他低頭看看走在身邊的里美,心裡暗想,四年前看著她入睡的那一夜彷彿昨日,怎麼才一轉眼,她就已經二十歲了啊。
###
三天後,里美和海樹兒回到馬太鞍,想要給高洛洛一個驚喜,卻很意外的從高洛洛的叔叔薩布那裡聽說,她前一天就收拾了登山背包,說要到西邊的山裡走走,還找了一個太魯閣族的朋友當嚮導,大概總要去個四、五天才會回來吧。
「太魯閣族的嚮導?」里美莫名其妙的說,「nēchan哪裡認識太魯閣族的嚮導?從來沒聽她說過呀。」
「所謂嚮導,是指有高山嚮導證的那種人嗎?」海樹兒問。
「這我就不太清楚了。不過那年輕人到家裡來接高洛洛的,說是叫做阿維,住在萬榮。看起來很實在的年輕人,說到山裡的事也很專業的樣子。我以為是高洛洛唸研究所做田調的時候認識的朋友,所以沒有多問。」
「Nēchan做田調時認識的朋友⋯⋯」里美想了一下,「嗯,也不是沒有可能。後來nēchan把題目完全大改,變成萬榮這一帶太魯閣族認同變遷的問題了,或許有訪問到這樣的人也不一定。不過阿維⋯⋯,真的是沒有聽nēchan說過這個人呢。」然後里美又轉頭去問薩布:「舅舅,nēchan有說她為什麼要去山裡嗎?」
「啊,這倒是有提到。她說去調查一下山裡的傳說,看看是不是未來以那個做為博士研究的題目。」「Nēchan要唸博士?」里美相當驚訝,「我以為她不想再唸了呢!」
「要唸博士的話,nēchan是絕對有那個聰明的,只是她的性格⋯⋯」海樹兒說到一半,想到自己正站在高洛洛的叔叔面前,連忙住了口。
「哎,海樹兒,你說的沒有錯啊,我對高洛洛還是很不放心哪。」說著他轉向里美,「這幾年你不在,她越來越古怪了,論文寫得辛苦,心事又好像很多,我跟你舅媽都不敢問她什麼。倒是她有時候去找你媽媽,大概她跟你媽媽比較談得來。」
里美回頭看著海樹兒:「Nīchan,怎麼樣?反正都回來了,我們去加里洞找我媽媽問問看吧?」
「是啊是啊,你們去問問秀川吧。」薩布說,「不然我跟你舅媽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你們騎高洛洛的機車去吧,我拿鑰匙給你們。」
梅雨將至的季節從馬太鞍騎車往加里洞去,又是一番完全不同的風情。過了太巴塱以後,田野變得開闊了,但路也變窄了。再過了產陶土的阿多莫,氣氛更是寂寥,但春天的田野卻十分青翠。海樹兒一邊騎車,一邊想著四年前的暴風雨之夜,自己怎樣千辛萬苦的騎單車撐過這一段泥濘之路,當時雨水澆灌,他連眼睛都快睜不開了,還冷得牙關直打顫。現在卻是大不相同了,春風溫和又帶著水氣,還有里美環抱著他的腰坐在後面。他一邊騎車一邊忍不住微笑,里美隱約從後視鏡裡看到他的表情,心裡大概有數,嘴角也不禁有點上揚,卻也怕被海樹兒看見,連忙轉頭去看田野風景。
騎了半天車,總算到了加里洞的家裡,偏偏校舍裡也沒有人影。里美打了電話給媽媽,才知道她今天把手工飾品帶去花蓮賣,恐怕傍晚才能回到加里洞。
「哎呀!」里美把手機往沙發上一扔,順勢就躺倒在上面,懶洋洋的望著天花板。「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呀,要找的人全部都不在!」
海樹兒在沙發旁邊的地板坐了下來,右肘靠在沙發邊上,右手撐著頭,側看著里美,「隨遇而安吧。反正晚一點秀川阿姨就回來了啊。就算沒見到nēchan,至少回來看過你媽了。回家永遠都不會白跑一趟的。」
「也是。」里美轉過頭去看海樹兒,兩人眼光對上,又是這麼近的距離,各自都有點臉紅,也不知道要說什麼。里美連忙從沙發上坐起來,去自己的背包裡拿了一本書出來。「Nīchan,閒著沒事,你教我唸書好嗎?我讀這個好幾天了,有些地方怎麼看就是不懂呢。」
海樹兒把書接過一看,竟然是森鷗外的短篇小說集。「哎,你怎麼現在就唸Mori Ougai?這對你來說不會太難了嗎?」
「難一點比較好,進步才會快一些吧。」里美說。
「Rimi的野心很大啊。」海樹兒微笑著說。
「也沒有,其實就是對日本文化非常感興趣而已,因為被取了日本名字嘛。」
「對了,你阿公阿媽呢?都沒聽你提過。他們給你媽媽也取了日本名字。秀川,這不是台灣人會取的漢名啊,應該是Hidegawa吧。」
「呃,我的阿公阿媽很早就過世了,我都沒見過,媽媽也沒有提。也許媽媽是因為自己取的是日本名,所以也給我取日本名吧。我不知道爸爸是誰,沒辦法知道我爸爸對我的名字有沒有參加意見。」
「嗯,以前取日本名的真的很多。我爸爸也是啊,叫做Hideyama。」
「耶?Hideyama?秀山嗎?這跟我媽媽的名字好像兄妹一樣啊!」
「這麼一說倒真的是呢。不過我媽媽就不是了,她的就是傳統的鄒族名字。」
「哎,nīchan,好羨慕你啊,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誰。就算沒辦法見到爸爸,知道他的名字也好啊。有個名字,至少給我一點想像的依據。」
「你很想找到你爸爸,嗯?」海樹兒望著里美那充滿期望的臉,「那,我來幫你找他好嗎?」
里美的眼睛裡閃過一絲光彩,但隨即又暗淡下去。「往哪裡去找?媽媽什麼都不肯告訴我,根本沒有線索⋯⋯。」
海樹兒哈哈大笑,習慣性的伸手把里美的短髮抓得亂七八糟。
「Rimi,你忘記了我有巫師的體質啊!」
「巫師的體質⋯⋯。」里美喃喃重覆了一遍。這個詞彙在她腦中喚起許多記憶,使她想起了只見過一面的海樹兒的哥哥阿浪,和那些冒著生命危險追查傳說線索的日子。她看著海樹兒開朗的笑容,也想跟著笑,想要像漫畫裡的角色一樣興致高昂的說,「你一定要幫我找到爸爸喔!」但她卻笑不出來,此時掠過腦海的,不知怎麼的竟是高洛洛那略顯憂鬱的臉。
「Nēchan去山裡追什麼傳說呢?」里美想著,突然間不安起來。傳說,不知道何時起,她竟然有點害怕聽到這個名詞了。
第二編 第一回
四月是雨的季節。台大校園裡正稀稀落落的下著不用撐傘也淋不濕的雨。在椰林大道口不遠處,一個穿著白色短袖T-shirt和牛仔布荷葉邊短裙的少女,站在開滿細密白花的流蘇樹下,抬頭望著這細長形的花朵,呆呆的出神。
「Rimi,在看什麼呢?」背後突然有個男生的聲音傳來。
里美轉過頭去,是她已經等了一陣子的海樹兒。比起四年前剛認識的時候,海樹兒又長高了一些,站在旁邊的里美顯得個子更小了。海樹兒越過里美的肩膀,伸手去摸流蘇花上的雨珠,對里美笑了笑:「真漂亮,是不是?」
「嗯,流蘇真的很漂亮,聽說有個別名叫...
目錄
推薦序一 解咒、伴咒之旅/浦忠成
推薦序二 被詛咒的福爾摩莎?/康培德
推薦序三 咒作為生機和愛而釋然/童元昭
第一編 絕島之咒
第一回
第二回
第三回
第四回
第五回
第六回
第七回
第八回
第九回
第十回
第十一回
第十二回
第十三回
第二編 山吹花
第一回
第二回
第三回
第四回
第五回
第六回
第七回
第八回
第九回
第十回
第十一回
第三編 放逐
第一回
第二回
第三回
第四回
第五回
第六回
第七回
第八回
第九回
第十回
第十一回
推薦序一 解咒、伴咒之旅/浦忠成
推薦序二 被詛咒的福爾摩莎?/康培德
推薦序三 咒作為生機和愛而釋然/童元昭
第一編 絕島之咒
第一回
第二回
第三回
第四回
第五回
第六回
第七回
第八回
第九回
第十回
第十一回
第十二回
第十三回
第二編 山吹花
第一回
第二回
第三回
第四回
第五回
第六回
第七回
第八回
第九回
第十回
第十一回
第三編 放逐
第一回
第二回
第三回
第四回
第五回
第六回
第七回
第八回
第九回
第十回
第十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