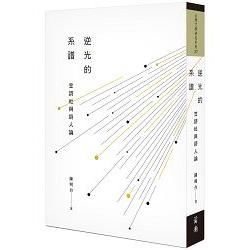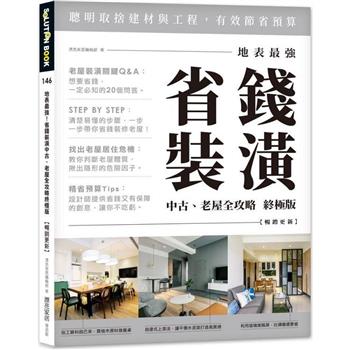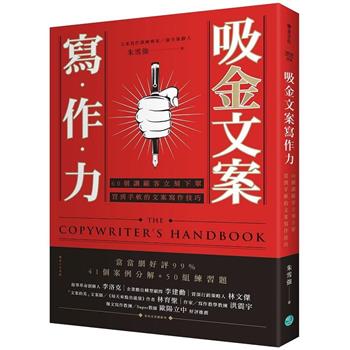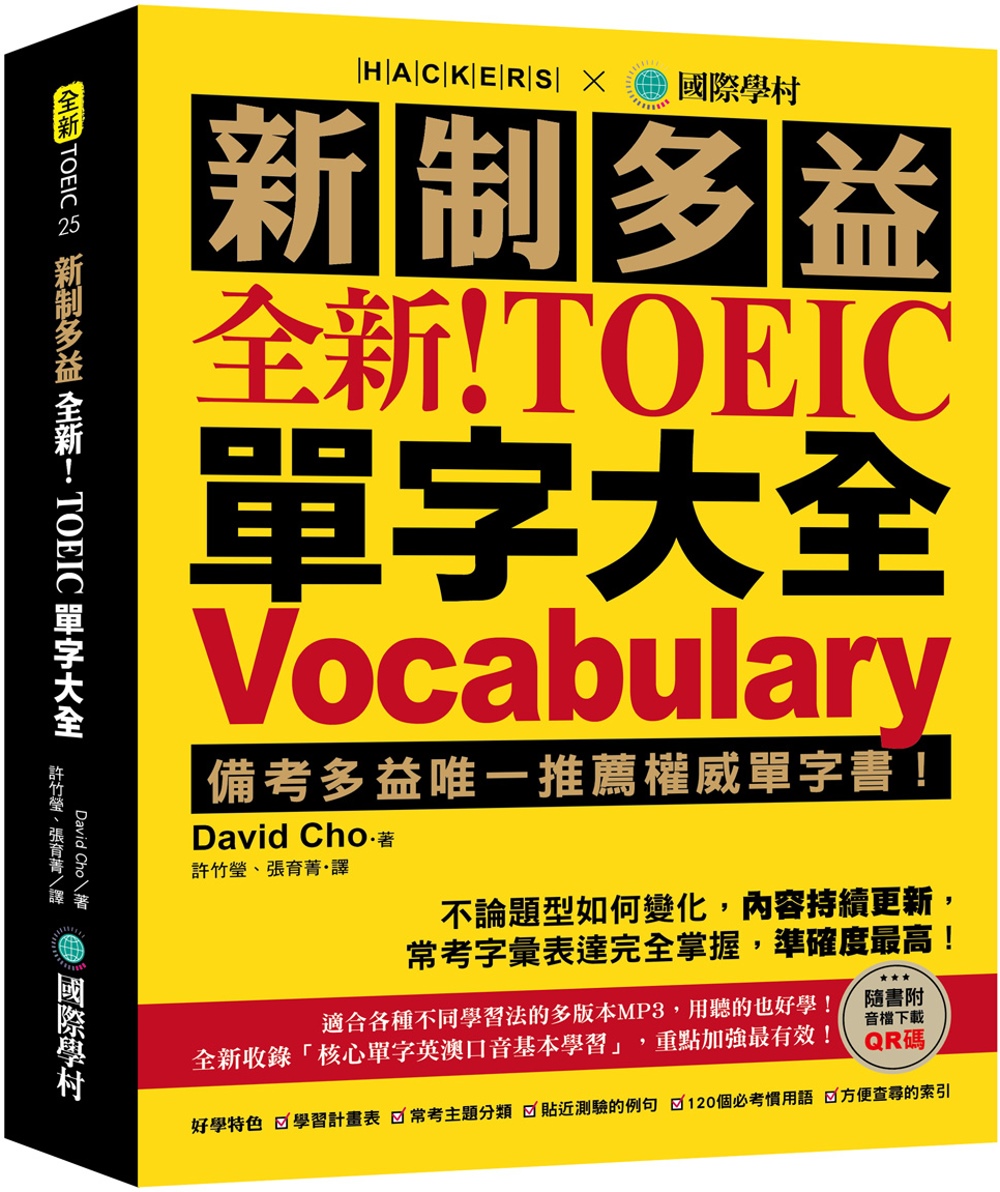一九六四年,笠詩社以「回歸本土」的詩學主張,聚集了戰前出生的前行代以及戰後世代詩人,開啟臺灣新詩的一頁歷史。五十年來,致力引介世界詩思潮,並孕育許多極富代表性的本土詩人,在臺灣文學史上,「笠」已是本土詩學與文化運動的輝煌印記。
本書作者陳明台多年來以「笠」詩人與台灣文學研究者雙重身份,積極參與現代詩創作與論評,也對「笠」詩社與笠詩人進行長期大量而深入的研究,一方面鉤勒出「笠」詩社的發展歷程,另一方面則精巧捕捉「笠」詩人各自獨特的詩藝發展軸線,如何形構出「笠」詩社之時代共相。評論之間,帶有詩人對「詩觀」的基本認識與展現。
本書即為陳明台歷年相關論述之集結,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笠詩社論」,論述笠詩社自成立迄今所標榜的詩精神、發展的共同傾向、臺灣主體意識的立場,以及笠詩人群共通不移的理念內涵。第二部分為「笠詩人論」,以世代特質區分,突顯在集團理念當中的詩人本質,針對巫永福、陳千武、詹冰、錦連、白萩、杜國清、李魁賢、趙天儀、岩上、李敏勇、拾虹、陳鴻森、曾貴海、江自得、鄭烱明等笠詩人的創作特色加以分析,具有史料意義,對詩社與詩人研究亦具備重要參考價值。
作者簡介:
陳明台
1948年生於臺中豐原,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學、碩士,日本東京教育大學文學研究所東洋史學組碩士,筑波大學歷史人類研究所東洋史學組博士課程修畢,是戰後出生「笠」詩人。曾分別於1969、1991年獲「青年新詩人獎」與「巫永福評論獎」。
曾任臺灣兒童文學學會理事、臺灣現代詩人協會常務理事、臺灣筆會理事、中正大學臺文所副教授、淡江大學日文系講師及副教授、東吳大學中文系及靜宜大學人文科兼任教授。
著有詩集《孤獨的位置》、《遙遠的鄉愁》、《風景畫》;評論集《心境與風景》、《臺灣文學研究論集》、《抒情的變貌──文學評論集》、《強韌的精神──臺灣文學研究論集2》等,編有《桓夫詩評論資料選集》、《陳千武全集》12冊、《鄭烱明集》、《陳鴻森集》、《臺中市文學史初編》、《美麗的世界》等,以及譯著多種。
章節試閱
鄉愁論—臺灣現代詩人的故鄉憧憬與歷史意識
一
詩人總有兩個故鄉,一個是他所歸屬的,一個是他真正生存的⋯⋯
這是一位出名的評論家在他的一篇評論裡開頭的一段,對於故鄉的概念,這段話提示了兩個層面的界定,第一個層面「他所歸屬的」可以說是比較狹義,確定而具體,限制了存在的空間而設定的。第二個層面「他真正生存的」可以說是比較泛泛的說法,曖昧而精神的,不拘束於時空座標而設定的。如果說前者是外在的指陳,則後者可以說是內面的呈示。例如我們通常說的「生長的地方的故鄉」和「心中憧憬的故鄉」可以用來加以區分和說明。值得注意的是,這位評論家在他論文的終結,將故鄉與歷史的意識、根源的形象做了連結而加以強調。
鄉愁這一概念則是基於故鄉的概念而發生的。鄉愁的意味,一般以為是指在異鄉、異域產生的思念故鄉的情緒。往往鄉愁與地平線會被聯想在一起。當然在廣泛的所謂「事物的鄉愁」的意味之外,狹義的鄉愁應該只限於故鄉的意識來表現。
縱然如此,除了限制於「生長的地方的故鄉」發生的鄉愁意識(亦即狹義的說法),鄉愁的意味應該可以有所延伸而產生較大的暗喻。其一是喪失了故鄉的意識,不只是遠離了故鄉,而是被流放,被迫永遠失去故鄉而產生的鄉愁意識,或者是對於誕生的根源持有暗鬱、黑漆漆的感覺、沒有了故鄉的意識等等。其二是鄉愁作為誕生的根源象徵,作為人發祥源地,由此而產生「生的憧憬」或藉此連接生的鄉愁意識。這種憧憬即使立基於自身活著的時空座標,而能充分感覺時,也可能發生,可以擴大而具有一般共通的性格。例如以大地為母性的象徵,而連結母性與故鄉憧憬為一體,又如對於自然(風物)持有特殊的憧憬。其三是鄉愁與歷史意識,經由故鄉的憧憬,引發對於以時空為座標、自己所背負的歷史淵源追蹤的心情,或者對於綿延不斷的傳統尊崇、親切感、省察等等,亦即經由對於自身所背負之傳統與歷史的凝視而產生的鄉愁意識。
不管以何種方式將個人內部的世界與故鄉憧憬、歷史意識加以結合,鄉愁作為永恆而具有共通性的人存在的象徵,應該是由於最後它可以和人的根源意識相連結這一點,認識根源的意識與探索鄉愁的意識,應該是一脈相通的,透過對於生的憧憬、喪失了故鄉的意識,或者歷史、傳統的凝視而希冀回歸之根源,尋覓自身根源之所在與造型。
二
臺灣現代詩人的鄉愁意識、故鄉憧憬,可以說是與臺灣歷史背景息息相關的。在戰前臺灣新詩人的作品中,已可看出他們濃厚的鄉愁意識的流露。不同於古詩人往往只基於流寓他鄉而作鄉愁之吟味,他們的鄉愁意識是具有更深層次的,喪失了故鄉的心情作為基調而抒發的。也就是故國不在,故鄉喪失的自身的立場才是他們根本的出發點,基於此而渴望搜尋、探索作為他們生之根源的鄉愁,而產生了故鄉的憧憬。
微笑流露 混沌未明的 微笑
嬰兒說:我是從哪兒誕生的?
慈愛的母親 有力的抱著嬰兒說:
在媽媽的夢裡 美麗的結晶就是你
你誕生之前 媽媽曾向天空翱翔的鷲鳥
和暗夜的天空閃爍的星星 祈禱過
祈禱讓你讓我的嬰兒 誕生在這美麗的世界
⋯⋯
泛泛著驚奇的表情
母親也微笑著說:
這兒就是美麗的世界啊 這是你還陌生的美麗的世界
微風悄悄地吹過密林 金黃的夕陽染紅了西天
好香的桂花盛開著 也有彩色的蝴蝶飛來飛去
沒有比這兒更美的世界吧
⋯⋯
稍微顫抖著聲音 母親又說:
你的父親和祖父,都曾經渴望著這美麗世界的來臨
但在美麗的世界奮鬥而死
⋯⋯
要守護這塊祖父的土地啊
在不久的那天 吾兒啊
不要害怕 這就是誕生在美麗的世界的你要負起的唯一使命⋯⋯
—張冬芳〈美麗的世界〉,陳千武譯
以上是詩人張冬芳的作品〈美麗的世界〉中的數段。以嬰兒與母親的對話來表現的這篇作品,實在是典型的鄉愁詩。在這首詩裡,作為誕生的源頭的母親,和作為誕生的對象的嬰兒,在思考著人生根源的問題。包括了對誕生世界(故鄉)的憧憬,誕生的世界裡美與醜的形象,誕生的根源,連結於歷史意識的父親與祖父的奮鬥,乃至未來的自身世界的遠景、想像與描繪。以最原始、無垢
的母親與嬰兒的感情交流作貫穿的線索,表達了詩人對於自己的生存熱愛,對鄉愁無限的憧憬,其中有探索自身根源的渴欲而直接深入連結於詩人內部的世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持有生存於殖民地現狀的立場與省察,而以浪漫的詩情加以表現,真摯而令人感動。
相對的,詩人郭水潭則有〈故鄉之歌〉:
懷念的故鄉
故鄉的 許多來歷
⋯⋯
今天 該向那些廢墟告別
正順著新的政風 給故鄉
添上新的風景 要展開了
⋯⋯
今天 該遺忘所有的神話吧
乘上時潮 在我的故鄉
新的信仰 就要誕生—
這首詩是在時代、歷史產生新的變化的瞬間,也就是從喪失的故鄉意識感受到回歸故鄉、新生的心情之際,微妙地表達了詩人焦灼、期盼的心境。比較張氏的作品,詩人更著眼於古老與新生對比的歷史、傳承意識,而且更具有理念的呈示。假如說,同樣是以「喪失了故鄉」的鄉愁意識作基調,張冬芳是連結於對自身「生的憧憬」,郭水潭則是另一個典型,力圖和歷史意識相結合。
三
在戰後,上述基於喪失了故鄉,而延伸出來的故鄉憧憬與歷史意識,作為兩個典型的表現,也成為底流,被臺灣現代詩人所承續、衍伸而發展。
首先,我們來考察第一世代的臺灣現代詩人的故鄉憧憬與歷史意識。
所謂第一世代的詩人們,在時間上而言,他們大抵是戰中成長的世代,或者親身經歷了戰爭,或者在殖民地(日本統治)時期已具有成熟的思考、判斷力,正值青春期,而且同時經驗過殖民以及戰後新時代來臨這兩個截然不同的歷史階段。所謂「跨越語言的一代」,毋寧說是陷落在語言的谷間,從事掙扎、思考而作價值判斷、凝視時代的一代。因此,這一世代詩人們的鄉愁意識,在根本上可以遙遙承接戰前前行代新詩人喪失了故鄉的心情,而以對「生的憧憬」與「歷史意識」兩種典型來歸納。但是,我們卻不宜忽視他們的被殖民體驗、戰爭體驗,以及迎接歷史變化、新時代來臨,透過對於新時代生活、精神經驗而呈示出來的不同的特質。
譬如說,對於戰爭的體驗,詹冰有〈船載著墓地航行〉:
嚴肅地待死的人們啊
現在你們嚼出生命的滋味吧
現在你們領悟人生的真諦吧
那麼 解脫情感的引力
摒棄一切 告別一切
如同祖先曾經做過的一樣
如同子孫將來要做的一樣
含著新的眼淚
帶著微笑跳進新的世界吧
⋯⋯
這首詩表現了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八日乘船渡過東海回歸故鄉的焦灼心境,有死的緊迫經驗,再生的渴欲,等於是個人歷史性的內部世界的揭露,而這種似乎是個人的一段歷史,卻無限地擴大成為變化中時代的現實經驗。桓夫則有〈信鴿〉一詩:
埋設在南洋
我底死,我忘記帶回來
⋯⋯
終於,我把我底死隱藏在密林的一隅
我悠然地活著
⋯⋯
一直到不義的軍閥投降
我回到了—祖國
我才想起
我底死,我忘記了帶回來
埋設在南洋島嶼的那唯一的我底死啊
在這首詩中,詩人宣告了他一歷史階段的死,以及回歸於根源的再生,而戰爭中埋設在南洋島嶼的「那唯一的我底死」成為作者思想的骨肉,成為他活生生的歷史,經常會復甦當是不言可喻。不管詹冰或桓夫的死的體驗的背後,都有回歸於新的歷史,鮮烈、焦灼的感覺和心情,面臨祖國(故鄉)的渴欲與期待。
詹冰對於故鄉的感情,也可以從他對自身誕生根源的憧憬與生命傳承的意識兩方面來追蹤。在〈那首歌〉一詩中:
初次 那首歌
由乳房中聽見
如電晶體收音機的樂音
那首歌似是乳液所唱出的歌
母親的
⋯⋯
只要 聽見那首歌
縱令在月球的死火山砂漠上
我也要像仙人掌般生活
⋯⋯我也要張開寶石般的花朵
在這兒,詩人表達了對生命根源的母體的依附與憧憬,而在另一首作品〈鹿港遊〉中,則有其對自身歷史的執著和熱愛。可以說詹冰的鄉愁,透過詩經常呈現了明朗、晶瑩的形象,充滿了生機與活力。
桓夫對於故鄉的憧憬,同樣可以從他對自身生命的根源的探尋與歷史意識雙方面來加以理解。然而他的鄉愁意識,毋寧說是陰鬱的,沉重而努力地在尋求與「喪失了故鄉」的連帶感。譬如作為他的詩的基本原型之一的〈雨中行〉即是一例:
被摔於地上的無數的蜘蛛
都來一個翻筋斗,表示一次反抗的姿勢
而以悲哀的斑蚊,印上我的衣服和臉
我已沾染苦鬥的痕跡於一身
母親啊,我焦灼思家
思慕妳溫柔的手,拭去
纏繞我煩惱的雨絲—
這首詩中,母親的形象若加以擴大,成為人共同的根源之象徵時,詩人尋求依附,回歸根源的思考當可以充分地被感受。另外如〈野鹿〉一詩,以故鄉山河,原始自然(玉山)為憧憬的對象,連結其意象與血、戰爭、死亡、破滅,雖然在詩人心中有著對故鄉風土十分清晰的印象,但是因野鹿的死亡卻顯得曖昧而難以捉摸,完全缺乏生機。根本上,桓夫的故鄉、鄉愁意識可以說是重疊了喪失(死去)的鄉愁和新生(再生)的鄉愁,而在其隙縫之間閃閃爍爍,亮光般的存在。
而從桓夫的曖昧的鄉愁感覺,及對於尋覓自身根源的執著(如〈禱告〉、〈網〉、〈童年的詩〉等作品所表現),可以顯見他對於誕生根源的形象,是通過自身內部世界的感受,加以過濾、把握的。因而介乎兩個不同歷史階段、生存時代的體驗,終究成為一種印證、對照,產生批評的角度,使得他日後發展出來的以民俗歷史為題材的鄉土、現實詩,就充滿了批判的性格。〈咀嚼〉有
對於吃的傳統文化的批判,《媽祖的纏足》有對於宗教信仰,現實人生態度的省察與批判,這成為他詩中的一大特徵。
四
其他同屬於跨越語言一代的詩人,如錦連可以說是沒入自身內部而投射外界物象,努力在探索自身的根源和現實狀況中的處境,如〈挖掘〉一詩:
許久,許久
在體內的血液裡我們尋找著祖先們的影子
白晝和夜 在我們畢竟是一個夜
對我們 他們的臉孔和體臭是如此陌生
如今
這龜裂的生存底寂寥是我們唯一的實感
⋯⋯
站在存在的河邊 我們仍執拗地挖掘著
一如我們的祖先 我們仍執拗在等待著
⋯⋯
這麼久?這麼久為什麼
我們總是碰不到水
在流失的過程中將腐爛一切的 那種水
⋯⋯
我們祇有挖掘
我們祇有執拗的挖掘
一如我們的祖先 不許流淚
我們可以看出錦連的鄉愁乃是源於一種「喪失的,找不到的」歷史意識,「一如我們的祖先」以及反覆著「執拗的挖掘」,即顯示了自虐式的、緊緊地追尋暗闇,不存在的故鄉,根源的思慮與忘我,因而有著「陌生」、「生存的寂寥」的實感。夜和祖先的影子實有深遠的象徵意味。
而不管是否透過母體、故鄉的風土或祖先的影子,努力於連結詩人自身內部世界與現實、歷史、生,上述詩人的表現,大體上是借諸他們過去的歷史體驗,重疊於物或事的形象加以造型、構成。除了這種方式之外,如吳瀛濤氏的〈鹿港鄉情〉、〈過火〉等純粹地、下意識地以歷史民俗為題材,呈示了現象描寫與記述,如陳秀喜的〈我的筆〉,具有殖民地人民的抵抗意識,也含有一種
歷史的省察與理解。又如杜潘芳格的〈平安戲〉是奠基於殖民地體驗,而意圖表達民族的性格,多少帶有批判的意味。同樣地,巫永福的〈泥土〉:
泥土有埋葬父親的香味
泥土有埋葬母親的香味
潘芳格氏的〈相思樹〉:
或許我的子孫也將會被你迷住吧
像今天,我再三再四地看著你
我也是
誕生在島上的
一棵女人樹
都具有回顧自身生之根源所在而熱烈去擁抱,一般人極能共感的「鄉愁」情緒。
五
不同於跨越語言的世代,大抵在戰爭中期或晚期渡過童年,所謂戰後的中堅世代臺灣詩人,或多或少地,也切身體會了戰亂流離,然而他們卻沒有前輩詩人們深切強烈的死的體驗,變換歷史的痛苦掙扎。他們在戰後,置身於一個全新的歷史階段(國民政府的接收、支配臺灣),由此,他們是立基於中國和故鄉臺灣的承接點而出發的。
基於這樣的歷史背景,他們應該是不曾背負了前一代詩人們暗鬱、喪失依憑的故鄉的感覺,也沒有暗闇、曖昧的故鄉意識。他們詩中的鄉愁意識因而潛向個人內部,從各自生的立場、體驗,去確認、掌握自身生的根源。他們或透過歷史意識、時空意識,或透過附著於自身誕生的土地、土俗的精神而展開追蹤。他們的鄉愁意識是較為泛泛的,具有人間共通、世界共通的主題。
這一世代詩人的鄉愁意識的探討,可以白萩、許達然、林宗源、非馬、杜國清、李魁賢、趙天儀等為對象。
白萩的鄉愁意識的發現,大抵可以從他的《天空象徵》詩集中的作品來考察。在這一時期中,他寫了許多有關根源、土地、天空為主題的作品。而根、土地、天空諸媒介,均是詩人在思考其生與存在之際,賦有深意的對象。
在〈路有千條,樹有千根〉一詩中,白萩如此地寫著:
路有千條條條在呼喚著我
樹有千根根根在呼喚著我
但來時的路
已在風沙中埋葬
源生的根
已腐爛
在這擾擾的世界之內
祇剩我一個
一個
路作為生的象徵,同時也作為破滅、腐爛的根源,「一個我」的斷了根、孤兒的自覺,可以顯示白萩的「生的憧憬」不存在,有的只是「生的敗北意識」,有的只是否定根源的唯我獨行的孤寂感。
在〈母親〉一詩中:
夕陽已斜斜
一個年青的少婦站在那邊
抱著一束玫瑰
露出胸前的奶子
「乖兒,乖兒
不要哭不要哭」
媽媽有的是奶汁
沒有嘴巴的玫瑰
一個年青的少婦站在那邊
乖兒,乖兒
潔白的奶子斑斑紅
沒有嘴巴卻有毒刺
抱著一束玫瑰
看著它在枯在死
也顯示詩人對於誕生根源的母體依附的不存在,藉枯死而襯托破滅的風土、現實的苛酷,詩人是站在一個「個我」去凝視、去對應,徹底地斷絕了傷感與聯繫。
白萩這種以個我昂然對應生與現實狀況的存在意識,在確認自身生的根源之際,衍伸而為兩種型態。一種是經由上述的否定、敗北感、孤寂感而斷絕與生、現實的依存關係,這提出根源不在的疑問。一種則擴展為人對於時間、空間無限的鄉愁。如〈天空〉一詩中有「天空不是老爹/老爹已不是天空」喪失了根源的結論。另一首〈天空〉中則有「他艱難的舉槍朝著天空,將天空射殺」,射殺了作為自身依存的象徵的存在天空的結局。都具有以獨立的「個我」來否定生的根源的意味。
其實,這樣的方式也未嘗不可以解釋為一種逆說,透過對於破滅、敗壞的根源的描述去確認自身的存在的辯證。至於白萩對人生的鄉愁,如〈雁〉一首:
在黑色的大地與奧藍而沒有底部的天空之間
前途是一條地平線
逗引著我們
我們將緩緩地在追逐中死去,死去如夕陽不知覺的冷去。仍然要飛行
在這兒,天空依舊出現,但天空已不只是個我寄託依存之處,而且是永久存在、浩瀚的時空,人如同雁一般向著無涯的地平線,追逐死去,仍然不停地飛行,自我對比於無限的時空,產生了無限的孤寂與鄉愁。
鄉愁論—臺灣現代詩人的故鄉憧憬與歷史意識
一
詩人總有兩個故鄉,一個是他所歸屬的,一個是他真正生存的⋯⋯
這是一位出名的評論家在他的一篇評論裡開頭的一段,對於故鄉的概念,這段話提示了兩個層面的界定,第一個層面「他所歸屬的」可以說是比較狹義,確定而具體,限制了存在的空間而設定的。第二個層面「他真正生存的」可以說是比較泛泛的說法,曖昧而精神的,不拘束於時空座標而設定的。如果說前者是外在的指陳,則後者可以說是內面的呈示。例如我們通常說的「生長的地方的故鄉」和「心中憧憬的故鄉」可以用來加以區分和...
作者序
晃盪在逆光中的記憶
陳明台
這本書的出版,對我而言,可以說是遲來的快慰。早在一九八○年代末期,我已經為本書書名《逆光的系譜》作了定調。偶然讀到的一本書中的內文的一段:「……逆光的時代,站在逆光的位置,傑出的文學者昂然地挺直身子,在此起彼落的黑暗的陰影包圍之中,提起筆,不斷地發出他們微弱的卻是帶有反逆的強有力的聲音……」這一段文字至今日仍然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裡,未曾忘懷。
我的青壯期的二十年間,一九六○至一九八○年代,臺灣可以說是處於一個逆光的時代,對於本土文學家而言,沒有閃耀的光譜照射他們倔壯的身影,秉持著意志和對於自身土地的關懷,他們各自努力不懈地記錄下時代的狀況中個人的體悟、思索與省察,那是一個受到拘束的時代,他們有許多是不曾妥協地想盡方法記述下足以提供給後人的文學證言。說是一種困厄中的掙扎,也是一種時代狀況帶來的千載難逢的機遇。
我的文學發展成長期正好遇到這一機緣,因緣際會,也是「一期一會」才有的契機與轉折。一九六○年代末期到一九七○年代初期的文學成長期邂逅了一些優秀的本土文學指導者,和幾位同輩的文學追求者,讓我受益良多,由於這些人的衝撞、切磋,才奠定了我邁向本土文學的良好基石。一九七○年代中期到一九八○年代初期的留日生涯,也是我文學生命中的一個轉捩點。我接觸到的思想、文學和狀況讓我有更大的開悟和超越的潛能,而晃盪在逆光時代之中的種種政治、社會、文化層面的記憶也蘊植了我內面的創作質素與理念,建立比較強而有力的自我省視和自我追尋的信心,這一直是我從事文學創作、評論、教學、閱讀批評強韌的支持和堅固支柱。不斷地成為我文學追求的動能,促成源源不斷的脈流。
我在《笠》詩刊與詩社成立之前,就對它有所理解、關懷與熱情參與,那也是一種晃盪在逆光中難忘的記憶和體驗,這本書全部的論述篇章都是由於這一機緣交會的產物、成果。
這本書包括了兩個重要的部分,其一是笠詩社論,論述笠詩社的共同傾向、精神意識與詩人共通不移的理念,其中〈鄉愁論〉一篇完成最早,對笠詩社存在的重要精神根據,臺灣主體意識,現實狀況的批評精神,以「故鄉憧憬」此一概念來加以發揮和展開論述。另外的篇章則從文學交流與世代特色來加以探討,闡明笠詩社的共同體詩人的精神和本質。其二,笠的詩人論,則以世代的特質區分,並從突顯個人詩本質與精神的視野來加以論述與思考。這兩部分的篇章包括了一九八二年以降到二○○五年為止的長期間創作的評論,比較縱橫自由的論略,以及學術研究論文,多數在學術研究會上發表,有固定的格式規則,稍有差別的方式構成。
今日回顧這些篇章,引起我個人的許多省思與感觸。時過境遷,笠詩社與詩人的構成已大有不同,精神和主張的掌握也顯凌亂,傑出的詩人已然存在不多,令人百感交集。然而本書仍具有資料保存,提供不同主張與觀點的意味,這也是它所以問世見諸天日的意味吧。
代序的〈誠實的發言〉一篇發表於《臺灣文藝》雜誌一百期,從省思狀況與創作意念出發,今日仍具極大意義,故以此為序言。
謝謝前衛出版社慨允出版本書,也謝謝鄭清鴻兄的盡心盡力促成出版。
晃盪在逆光中的記憶
陳明台
這本書的出版,對我而言,可以說是遲來的快慰。早在一九八○年代末期,我已經為本書書名《逆光的系譜》作了定調。偶然讀到的一本書中的內文的一段:「……逆光的時代,站在逆光的位置,傑出的文學者昂然地挺直身子,在此起彼落的黑暗的陰影包圍之中,提起筆,不斷地發出他們微弱的卻是帶有反逆的強有力的聲音……」這一段文字至今日仍然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裡,未曾忘懷。
我的青壯期的二十年間,一九六○至一九八○年代,臺灣可以說是處於一個逆光的時代,對於本土文學家而言,沒有閃耀的光譜照射他...
目錄
自序 誠實的發言
Ⅰ 逆光的系譜——笠詩社論
鄉愁論——臺灣現代詩人的故鄉憧憬與歷史意識
綿延不絕的詩脈——笠的系譜與風貌
清音依舊繚繞——解散後銀鈴會同人的走向
世代的傳承,風格的形成——笠詩社的少壯派詩人論
論臺灣現代詩的橫的移植——從風車詩社到笠詩社
笠詩人與日本前衛思潮
Ⅱ 批評和想像——笠詩人論(一)
強韌的精神——巫永福論
發生的事,發生的文學——陳千武論(一)
計算的美學——詹冰論
詩、夢、歷史與現實——陳千武論(二)
硬質而清澈的抒情——錦連論
Ⅲ 抒情和即景—笠詩人論(二)
凜烈的現實精神——白萩論
美的狩獵者——杜國清論
風景鮮明的詩——論李魁賢的旅遊詩
寫實的旗手——趙天儀論
濃郁的鄉土情——岩上的詩
Ⅳ 暗喻和現實—笠詩人論(三)
鎮魂之歌——李敏勇的詩
飄泊之歌——拾虹的詩
悲愴的命運、苛酷的現實——陳鴻森論
冷澈而熾烈,理性又感性——江自得、曾貴海、鄭烱明醫生詩人論
後 記 晃盪在逆光中的記憶
附錄一 哀愁、虛幻與無常——論陳明台的詩/寒渝
附錄二 陳明台著作目錄
自序 誠實的發言
Ⅰ 逆光的系譜——笠詩社論
鄉愁論——臺灣現代詩人的故鄉憧憬與歷史意識
綿延不絕的詩脈——笠的系譜與風貌
清音依舊繚繞——解散後銀鈴會同人的走向
世代的傳承,風格的形成——笠詩社的少壯派詩人論
論臺灣現代詩的橫的移植——從風車詩社到笠詩社
笠詩人與日本前衛思潮
Ⅱ 批評和想像——笠詩人論(一)
強韌的精神——巫永福論
發生的事,發生的文學——陳千武論(一)
計算的美學——詹冰論
詩、夢、歷史與現實——陳千武論(二)
硬質而清澈的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