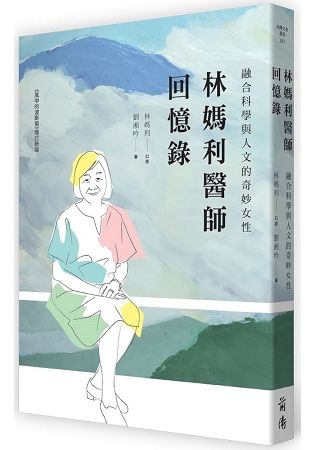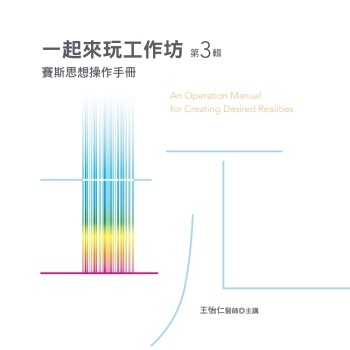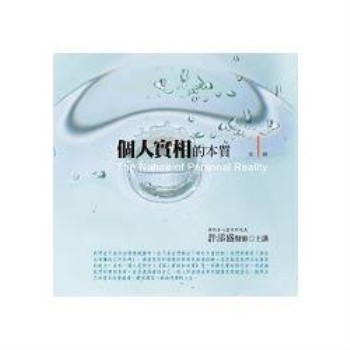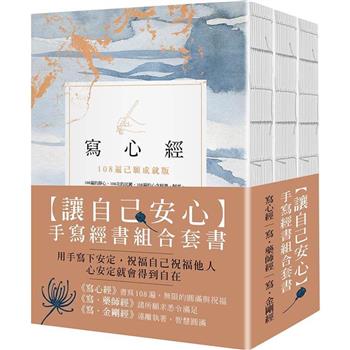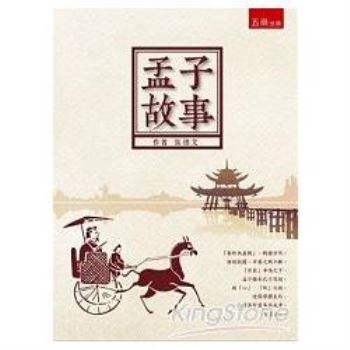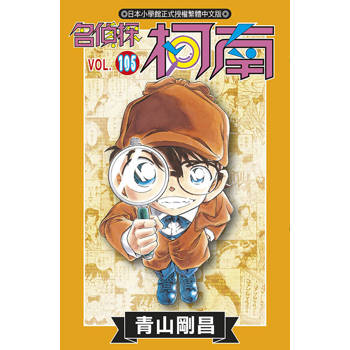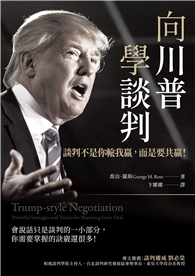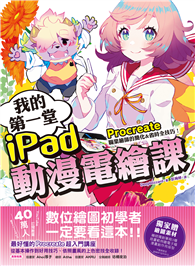投身血液工作
一九八一年,媽利回到台灣。在做了決定之後,她曾先返台一趟,主要是為了工作的事。她原先想到台大醫院做血庫的工作,找林國信主任,但得到的答覆是「沒有缺」。「其實我聽到的說法是:因為我『不是台大的』,不夠資格,所以不歡迎我。」媽利可以選擇回台大病理科,但那時她所敬愛的林文士人老師已經過世,倒是當年曾屢次質問媽利「為什麼不回高醫?」的侯先生歡迎她回去。物換星移,生命似乎像媽利扮出一個嘲諷的笑臉。但她不想回台大病理科。
因為如此,在台大醫院待了十幾年的媽利,才開始思考「台大」以外的選擇。馬偕醫院當時的吳再成院長要媽利到馬偕看看,「我那時是部定副教授,當時馬偕還沒有副教授。」吳院長的延攬,加上朱醫師的鼓勵(薪水比台大醫院高),媽利於是決定:好吧,我來做做看。
由於十幾年的專業與慣性,初到馬偕的媽利還是表明想做病理(血液病理),但由於病理科林雲南主任的反對,媽利並無法如願,而只好做檢驗科;當時最沒人想做也不會做的就是「血庫」,又為了原技術主任周龍國先生的不退讓,新來的檢驗科林媽利主任於是接下了這個冷門的工作。
雖然後來專注在血庫相關研究工作的媽利,成為台灣血液政策、國人血型研究的重要人物,也從而使她在台灣、甚至世界的醫學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但在當時,不能做自己最擅長的病理,只能在檢驗科負責血庫,對媽利不啻是一大挫折;她感到迷惘,甚至懷疑自己在醫院中的意義何在?
還好在美國受訓時學了血庫,雖然一開始猶疑、不安,但在逆境中努力,一直不是媽利陌生的事。這個嬌小的女人常常如此:一邊質疑自己,一邊奮勇向前。
當時馬偕的血庫可謂「家徒四壁」,除了一個醫檢師外,「只有一張桌子、一個冰箱、一台顯微鏡和一台離心機。」顯微鏡是和檢驗大、小便共用的,媽利說:「當時血庫是和urine stool(尿液糞便檢驗)一起作業,血庫除了一台專放血袋的冰箱外,什麼都沒有。」
在這種情況下,媽利常用高醫時期杜聰明校長的話來鼓勵自己,「以前他常常說:做研究是不是一定要有很好的設備呢?他的答案是不一定需要。他認為很多偉大的研究,都是在很差的環境中做出來的,像居禮夫人和發現細菌的Koch。他這些話在那段時間真的給我很大的鼓勵。直到現在有些人碰到我還會說:他真是想不通,當年在馬偕醫院那樣的環境下,我怎麼能待那麼久,而且做了那麼多研究?」媽利說:「事實上,的確有許多研究並不需要很多或很好的設備。」
什麼都沒有的時候,就從最基本的開始。
媽利從編寫作業手冊、教血庫工作人員如何正確地搖動試管、做交叉試驗……做起。在她的建議下,醫院添購了一台當時台灣沒幾家醫院有的「血液交換機」,有了機器,當然也要訓練工作人員操作這台機器。
最寂寞的地方、最棒的夥伴
一九八○年代初,台灣醫院裡的血液來源、輸血狀況,是現在的台灣人難以想像的;那時,沒有隨處可見的捐血車,捐血的觀念極不普及,一般人深信「捐血有損自身健康」,醫院裡需要的血液,絕大多數由「血牛」(靠賣血維生、謀取利益的人)供給,抽血、驗血的流程沒有統一標準外,血液來自「販血為生」的血牛,品質亦堪慮。「那時很多醫院都固定養著一些『血牛』,需要血的時候只有靠他們;甚至還要常常看『血牛』的臉色呢!」也因為輸血來源混亂,當時B肝帶原率相當高,不少病人因輸血造成感染。這些基本的問題,明明白白擺在眼前,媽利當然就有一個看似遙不可及的夢想:要讓台灣的輸血作業「跟上美國的標準」。一切只等時機來到。
一九八三年,媽利加入「國際輸血學會」,成為會員。當時衛生署也有意革新台灣亂無章法的供血系統,於是邀請當時紐約血液中心主任Dr. Aaron Kellner前來檢驗台灣的捐血機構(當時是「中華民國捐血運動協會」)及醫院的血庫。Kellner後來寫了一篇內容洋洋灑灑的建議書給衛生署,這成為日後台灣血液政策的藍本。
「Dr. Kellner提出了很重要的建議,第一,他建議整個國家的血液政策應由政府制定,且由一個捐血系統有計畫地提供及調配全國所需要的用血,血液來源必須全部來自捐血,以提高血液的品質,且須充分提供整個台灣所需要的血。第二,要做研究。他認為台灣有這麼多材料,應該要做相關的研究。第三,辦理全國有關輸血工作人員的在職訓練……。」
八月,衛生署召開「第一屆血液科技研討會」,並邀請多位國外的輸血專家與會,美國紅血球血型專家李昌林教授也是受邀貴賓之一,他卻不幸在會議結束當天中風病倒,幾天後病逝榮總。這件遺憾的事,讓媽利當時就決心翻譯李昌林教授所著、成為美國臨床病理的工具書中有關輸血醫學的文章,以做為紀念。幾年後這個心願結合自己的研究與發現,媽利所著的︽輸血醫學︾一書,成為台灣第一本關於輸血醫學的專書,至今仍是大多數醫學院學生的教科書。
當時的衛生署長許子秋,是媽利高醫時的老師,兩人自高醫後近二十年沒見,在血液科技研討會中重逢。許子秋知道媽利去美國學了血庫,也感受到她對健全捐、輸血系統的熱血與使命感,於是次年派她公費赴歐洲一個月,考察先進國家的捐供血系統及血液事業,這也是媽利此後在台灣血液政策及制度建立發揮功能與影響的開始—雖然她的身分一直是一名私立醫院的醫師。
在馬偕檢驗科的研究工作也同時進行著。在這個原本非常寂寞、孤立的地方,先是有一位全力支持她的同仁楊定一,在他口中,媽利是一個「最棒的老闆」,因為媽利是個充分授權、充分信任的好上司,兩人共事十幾年,媽利全心做研究工作,楊先生負責管理、行政,相輔相成,楊先生對媽利十分感佩,媽利也說:「他幫了我很多忙。」
另一位「上帝派來的工作夥伴」,是愛爾蘭籍的免疫血液學家鮑博瑞(Richard E. Broadberry, FIMLS)。鮑博瑞曾於一九七九年赴花蓮門諾醫院服務,之後回英國。在一次禱告中,他清楚地感應到上帝呼召他再度到台灣的馬偕醫院服務,於是一九八三年,一位不可多得的好朋友兼好同事「從天而降」,和媽利前後共事共十二年。鮑博瑞不但是媽利研究工作方面最好的夥伴,兩人共同完成了多項血型研究計畫;在遇到困難的時候(不管是工作上還是生活上),兩人也常一起禱告、互相打氣度過難關。
台灣當時的供血亂象
現在輸血,是所謂的「血液成分治療」,捐來的血將其中的紅血球、血漿、血小板分開,病人若貧血缺少紅血球,只要輸給他紅血球就好了;但在當年設備與人力都不足的情形下,沒有「血液成分治療」的觀念與作法,於是病人若需要血,「醫院就抽血牛的血,然後把整袋血(所謂的全血)輸給病人。」媽利說:「沒有人知道全台灣的醫院有沒有按部就班做各種檢查?品質又如何?」這些在當時都完全沒有評鑑或檢查機制。「我們的血庫的工作主要就是抽血—抽血牛的血。房間裡常常是一堆血牛等在那裡。當時有個大學醫院更是血牛當家,據說有時候晚上是血牛在幫忙做交叉試驗、抽血……。有些血牛這個醫院賣完又跑到另一個醫院,弄得血很稀,有時候血牛的血比病人還稀,這樣的血我們還是抽,因為血源不足。有的醫院甚至於養血牛,給他們住的地方。」
那時捐血中心隸屬於「捐血運動協會」,由內政部管理,是黨營機構,有些職位在當時是酬庸性質的職缺,其中大多數人員都是自「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退休的長官。捐血中心當時有一位陳凌海總幹事相當努力,他拜託媽利去幫忙,於是從一九八三年到八六年,媽利每個禮拜跑一趟台北捐血中心幫忙他們改善作業,「像抽血時的消毒、血紅素的測定等;也教他們免疫血液學及如何解決血型問題。」此外,最怕在眾人面前說話的媽利也成為「捐血運動宣傳大使」,常上電視、媒體宣導關於捐血的觀念,如:捐血不會有害健康;血液是無價的,不應買賣,只能贈與;捐血一袋救人一命……等。有一段時間,媽利是「薇薇夫人」電視節目的常客,定期上電視向國人宣導關於血液的正確、進步觀念,各種演講、座談更多不可數。
那時台灣共有十個名為「紅十字會血液銀行」的組織,分布在台灣十所醫院中,其實就是有價供血──血牛的供血站。「我去國外參加會議時,告訴人家我們的『紅十字會血液銀行』提供的血是血牛的血,大家都驚訝得張大了嘴巴。」媽利笑說:「先進國家沒有這種事情,他們都是捐血制,也是由紅十字會主辦。台灣那時候很亂。」透過捐、輸血可能傳染的疾病不少,尤其是令世人聞之色變的AIDS──「還好台灣提早了一點把捐血系統、血液政策建立起來了,否則真是不堪設想!像中國就很慘,他們就是因為捐血系統、血液政策沒有先做起來。」
在Kellner來台考察並提出建言後,隨後衛生署召開的「第一屆血液科技研討會」及其他相關會議中,Kellner的意見受到廣泛的重視與討論,也鼓舞了媽利。媽利寫信給Kellner,報告之後台灣在血液政策方面的進展與工作,也感謝他給台灣的指導與建言。那年九月媽利去美國看兒子,順道也去了Kellner所任職的「紐約血液中心」參觀。
媽利也開始以「輸血學會」的名義在馬偕醫院做全台灣醫檢師的在職訓練工作,「輸血學會」至今仍然持續這項訓練工作。一九八七年,媽利和幾名志同道合的醫師孫建峰、李正華成立「中華民國輸血學會」,會員也成為這項全國性、長時間的在職訓練計畫的義工。這項工作在剛開始時並沒有專用經費或頭銜職稱,媽利說:「我們這個團隊好像沒有人要搶什麼功勞、出什麼名。從一開始我和鮑先生只是抱著服務的心態,做該做的事。」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林媽利醫師回憶錄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50 |
二手中文書 |
$ 210 |
台灣人物 |
$ 237 |
醫療傳記 |
$ 264 |
中文書 |
$ 264 |
醫界人物傳記 |
$ 270 |
醫療傳記 |
$ 270 |
社會人文 |
$ 270 |
Social Sciences |
$ 270 |
歷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林媽利醫師回憶錄
《風中的波斯菊》增訂新版
融合科學與人文的奇妙女性──林媽利醫師最新傳記
林媽利,台灣醫學史上不可忽略的重要角色,她是台灣血液醫學的開拓者,台灣的血液政策、血型研究、捐血系統,她都占有一席之地。
從有價供血,到健全的捐血體制,她的研究成果,拯救了台灣各地的病人,影響深遠;她鑽研台灣人血液,試圖以科學證據解開台灣各族群的血緣、基因之謎,即使身陷政治鬥爭,她仍勇敢堅持,不做任何無謂的辯解。
其實,林媽利醫師的一生並不順遂,貧血、乳癌、肺病,各種疾病糾纏她的身體;離婚、失憶,不愉快的情緒籠罩她的心靈。這些困境未曾擊垮這位嬌小的女性。
「如果我們無法超越過去的不幸,我們就看不到藍天白雲、以及路邊小花的美麗。」在人生的試煉中,她終究綻放精彩,貢獻己學、造福眾人。她就像是一朵柔弱又堅毅的波斯菊,溫柔謙遜地搖曳在風裡。
作者簡介:
林媽利
高雄醫學院、台灣大學病理研究所畢業。長期從事輸血醫學之研究,是台灣輸血醫學能躍上國際舞台的重要推手。現為馬偕紀念醫院輸血醫學研究中心主任。
曾協助衛生署(現衛福部)的國家血液政策,主導建立台灣捐血系統及健全醫療院所的輸血作業,因而被稱為「台灣血液之母」。近年致力於基因研究,對台灣的族群做全面性的探究及分析。著有《輸血醫學》、《我們流著不同的血液》(前衛出版)等書。
劉湘吟
政大廣電系畢業,自由文字工作者,曾任職《新觀念》雜誌多年。2009年5月至2012年7月隻身赴中國山區擔任志工老師,先後於陝西南部、雲南西北部及甘肅南部三處偏遠山區小學支教,實踐「公益旅行」結合「深度旅行」的夢想。
著有《老師不要走》、《多一公斤的旅程》、《風中的波斯菊:林媽利的生命故事》等。
TOP
章節試閱
投身血液工作
一九八一年,媽利回到台灣。在做了決定之後,她曾先返台一趟,主要是為了工作的事。她原先想到台大醫院做血庫的工作,找林國信主任,但得到的答覆是「沒有缺」。「其實我聽到的說法是:因為我『不是台大的』,不夠資格,所以不歡迎我。」媽利可以選擇回台大病理科,但那時她所敬愛的林文士人老師已經過世,倒是當年曾屢次質問媽利「為什麼不回高醫?」的侯先生歡迎她回去。物換星移,生命似乎像媽利扮出一個嘲諷的笑臉。但她不想回台大病理科。
因為如此,在台大醫院待了十幾年的媽利,才開始思考「台大」以外的選擇。馬偕...
一九八一年,媽利回到台灣。在做了決定之後,她曾先返台一趟,主要是為了工作的事。她原先想到台大醫院做血庫的工作,找林國信主任,但得到的答覆是「沒有缺」。「其實我聽到的說法是:因為我『不是台大的』,不夠資格,所以不歡迎我。」媽利可以選擇回台大病理科,但那時她所敬愛的林文士人老師已經過世,倒是當年曾屢次質問媽利「為什麼不回高醫?」的侯先生歡迎她回去。物換星移,生命似乎像媽利扮出一個嘲諷的笑臉。但她不想回台大病理科。
因為如此,在台大醫院待了十幾年的媽利,才開始思考「台大」以外的選擇。馬偕...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一條幽微而清晰的命運路徑 劉湘吟
在《風中的波斯菊》出版(二○○四年)後的十幾年來,和林媽利醫生見過許多次面︰陽明山上像住在森林裡的家,淡水能看到美麗彩霞和遼闊景致的家,在她的畫展……。她的笑容依然那麼溫暖、迷人,仍然在聰慧嫻雅中不失一份赤子般的率真、頑皮;令我驚訝的是,年近八旬的她仍然在馬偕醫院工作,與一群工作同仁不斷有新的研究發現回饋給社會,還出版了另一本書──《我們流著不同的血液》;她仍然在抗病,但同時也在學習新的繪畫方式,甚至創作更多了,還開了個人畫展及受邀參展。實在難以想像一個人怎麼...
在《風中的波斯菊》出版(二○○四年)後的十幾年來,和林媽利醫生見過許多次面︰陽明山上像住在森林裡的家,淡水能看到美麗彩霞和遼闊景致的家,在她的畫展……。她的笑容依然那麼溫暖、迷人,仍然在聰慧嫻雅中不失一份赤子般的率真、頑皮;令我驚訝的是,年近八旬的她仍然在馬偕醫院工作,與一群工作同仁不斷有新的研究發現回饋給社會,還出版了另一本書──《我們流著不同的血液》;她仍然在抗病,但同時也在學習新的繪畫方式,甚至創作更多了,還開了個人畫展及受邀參展。實在難以想像一個人怎麼...
»看全部
TOP
目錄
推薦序 喜悅的林媽利 Harold Gunson
推薦序 輸血醫學的拓荒者 遠山 博
自 序 希望與感謝 林媽利
作者序 一條幽微而清晰的命運路徑 劉湘吟
序 章 蜚聲國際的「台灣輸血醫學之母」
輯 一 我的父親母親
輯 二 多采多姿、苦樂交雜的成長時光
輯 三 步上習醫之路
輯 四 暗無天日的女醫師生活
輯 五 迷失的一代、混亂的美國生活
輯 六 全心全意投身台灣的輸血醫學
輯 七 中央公園裡的台灣母親
輯 八 神把最好的賞賜給我
輯 九 愛沒有國界
輯 十 不...
推薦序 輸血醫學的拓荒者 遠山 博
自 序 希望與感謝 林媽利
作者序 一條幽微而清晰的命運路徑 劉湘吟
序 章 蜚聲國際的「台灣輸血醫學之母」
輯 一 我的父親母親
輯 二 多采多姿、苦樂交雜的成長時光
輯 三 步上習醫之路
輯 四 暗無天日的女醫師生活
輯 五 迷失的一代、混亂的美國生活
輯 六 全心全意投身台灣的輸血醫學
輯 七 中央公園裡的台灣母親
輯 八 神把最好的賞賜給我
輯 九 愛沒有國界
輯 十 不...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林媽利口述/劉湘吟著
- 出版社: 前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9-20 ISBN/ISSN:978957801825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72頁 開數:15×21公分
- 類別: 中文書> 醫學保健> 醫界人物傳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