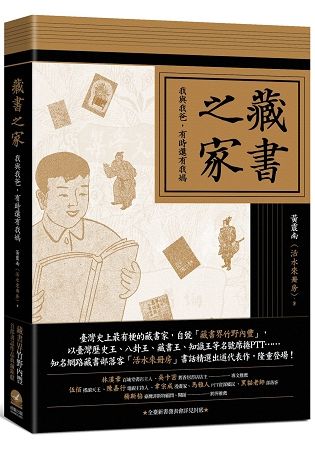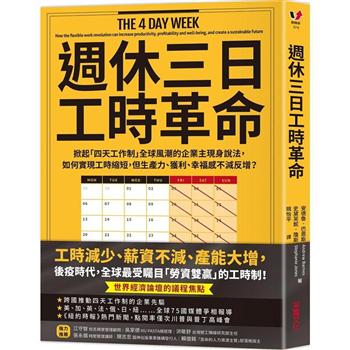序
我與黃家父子的交誼
人生逆旅,千帆看盡。經營舊書店大半生,雖說客人即是友人,然而數十年書友來去,或凋零寥落,或移居海外,或興趣移易,能夠稱上交往一生而志趣不移者,寥寥可數。其中黃哲永君,則是我人生中,氣味相投且情誼永存的摯友。
民國六十三年,我在臺南部隊服役,擔任營部訓練官。當時我對臺灣文史有極大的興趣,每逢休假返北,必至三民書局購買《臺灣風物》雜誌。然而該誌在書店只能零售,蒐集工作費時費力,我遂按《臺灣風物》廣告,寫信給王詩琅編輯,表明亟欲購買《臺灣風物》自創刊號起至今的合訂本,這筆金額是當時我任職軍官的數月薪水。可惜書沒買成,當時庫存最舊只有第十七卷以後之合訂本,然而王編輯託鄭喜夫先生回信通知我這個消息,卻成為我與黃哲永兄結識的契機。
黃哲永兄大我一歲,在嘉南地區年少即有文名,自高中起便撰寫各地文史紀錄,投稿報章雜誌。又與林文龍君為莫逆交,輒聯袂訪查各地古蹟,抄寫碑文,甚至從荒煙蔓草間,挖掘、清整無名墓碑,只求一睹百年前的歷史紀錄。當時黃、林二兄行旅至霧峰萊園,自萊園內所存石碑中尋得連雅堂詩,乃當時文獻未曾刊錄者;黃兄便將抄得之詩文,寄與正在編輯《雅堂先生集外集》的鄭喜夫,作為補充。鄭喜夫約略同時收到哲永兄與我的來信,得知我們年齡相仿,便從中引介,成為筆友。
六十三年底,我與黃兄正式通信,當時黃兄身在金門從軍,初來信時內文熱情異常,儼然老友一般;爾後才知道當時軍中通信,保密條款甚嚴,不得私交筆友,他故作熟識,乃避人耳目,不讓長官察知我等乃未曾謀面之初交也。然而通信不久,誠知古云傾蓋如故,實在不假。某次黃兄提及他們正在讀報載易君左《六十年滄桑》、高拜石《古春風樓瑣記》等,我大驚曰吾輩焉得更有此人,蓋因那也是我每日必追的報紙專欄。三個年方二十出頭、學歷平凡的青年,對於文藝、舊事、掌故卻有如此驚人相似的愛好,使得我們通信之初,便確信覓得知音,惺惺相惜。
黃兄退伍之後,與文龍輾轉於中部各地工廠打工,也結交了一批彰化文友,有邱素綢、楊龍潭、張儷美、馬水金等;經由黃林二兄引介,我也與中部諸友來往甚密。六十五年我退伍後,每逢端午,必到鹿港與這群文友聚會,是時大家不過二十來歲,志趣投合、年少氣盛,相聚時尋幽探勝、把酒言歡、比文弄墨、徹夜不眠,是我年輕歲月中不能抹滅的回憶。
這群文友大多假擊缽詩人大會相聚,我雖不熱衷此道,然而也經常南下參加詩會與哲永兄等見面,亦經常至嘉義宿於黃家。猶記黃兄結婚時,我從臺北坐了大半天的車,輾轉來到黃家為他祝賀。黃兄婚後,由於其夫人素綢亦是中部文友,與我早已熟識,並不見外,亦竭誠歡迎我至嘉義叨擾。因此這段期間,我南下嘉義多次,與黃兄來往密切,若在他家架上看見什麼好書,黃兄盡皆慷慨相送。他騎摩托車載我至上班的畜殖場,讓我見識豬舍風情;下班後又相載至雲嘉各地舊書攤、古董店尋寶,北港紀老師、李國隆、土庫楊仔等處,都曾留下我倆足跡。亦曾趁中部聚會時,至劉峰松開的舊書店開眼界;偶爾哲永兄北上,我們攀登觀音山,晚間宿於寒舍,他在架上看見垂涎已久的珍本,我也應允相贈,或彼此開玩笑稱為「無期限租借」。我與黃兄到對方家裡,看見喜歡的書籍都能儘管拿走;對於志同道合到比親兄弟還親的朋友,已經不是朋友,而是能無償交流、交換的兄弟。
從服役到退伍,這麼多年時間,除了偶爾見面,我與黃兄一直保持大約每星期通一封信的頻率,累積數量相當可觀,通信內容從生活瑣事到文壇祕辛,無所不包。由於我寓處臺北,資訊流通較快,往往負責介紹黃兄延伸閱讀的任務,例如我知他對於燈謎有興趣,便介紹他讀《自立晚報》,留意燈謎專欄。我在重慶南路舊書攤得知有哪些黨外雜誌被禁,便通知他趕緊掃貨。這段密切通信的時間,大約持續了四、五年,直到黃兄家中設置電話後,才改以電話聯繫。
不久後,過年時我至嘉義住宿黃家,七手八腳抱了尚在襁褓中的黃兄公子,心中為哲永兄感到欣慰。然而由於負起家庭的重擔,黃兄與我的聯繫便無法如同先前還是青年時那樣頻繁了;隔幾年,百城堂舊書店正式開張,我也被書店業務綁住,無法隨時南下聚會,一年中相見次數才減為個位數。值得一提的是,我開店之初,黃兄也寄來數箱蘭記書局流出的書籍、文獻資助,其中蘭記老闆親手攝影的一批蘭花、李香蘭相片相當珍貴,是長銷商品。當時我與哲永兄都稱不上收藏家,黃兄捐贈數箱書籍,可謂是大手筆;對創業初期,並沒有貨底的我而言,不啻是及時甘霖。
林文龍兄任職於臺灣省文獻會,常有機會出差至臺北,因此與我見面機會較多。哲永兄鮮有要事北上,因此一年大約只能到店裡一兩次,就這樣來過幾次,陪伴黃兄來的公子震南也日漸長大,叫我「漢章叔叔」了。哲永兄來到店裡,取出一千塊塞給震南,只交待「到光華地下街逛一圈,愛買什麼書就買,把錢花完」,這個出生數月時就被我抱過的嬰孩,已經是個國中生,不負使命地出去,兩小時後,提了五六家書店的提袋回來,說把錢剛好用完。
這樣聽人叫「漢章叔叔」叫了幾年,震南負笈外地,哲永兄也無法帶他來了。又經數年,一個夏日午後,百城堂的門被推開,來到北部工作的震南重回到店裡了,他已是成年人,大約是哲永兄與我相識時的年紀。震南克紹箕裘,對於臺灣文史、舊書有相當濃厚的興趣,因此也就成為店裡的常客,對店裡任何事物都充滿好奇,經常指著一張海報、一幅字畫、一本舊書、一件文房,問起來歷,然後我們話匣子就打開了一下午。近年來震南在網路上嘗試寫網誌,長期活躍於網路的愛書人皆驚疑這號憑空冒出的藏家是誰。有一次同業booker 到我店裡閒聊,講起有這個人物,我聽了之後便肯定是震南,遂將我與哲永的交誼簡略交待,booker 回去後在網路寫出,這個「藏鏡人」的身分才曝光。
今日震南網誌的文章要集結成書,雖然字裡行間插科打諢、假不正經,然而其披露的文獻、相片,有些確實是極為罕見的,成為截今為止研究者僅見的資料;而其愛好舊書、文史的熱情,與我認識的哲永兄並無二致。
我與哲永兄、文龍兄三人都沒有顯赫學歷,而今哲永兄在收藏、學術、教育、文史界皆有輝煌成績;文龍兄則在臺灣文獻的研究、收集上聞名全臺;我則安守一家舊書店,雖無堂皇頭銜,卻經眼無數稀珍文獻古籍,自得其樂。當年的三兄弟,廁身於私人工廠做苦工時,誰也想不到今日能各佔一片天,在喜愛的舊書和文史方面發揮所長。我視震南就如同看見年輕時期的哲永兄,也期待他能夠以本書作為起點,在舊書文獻的收藏與整理上,繼續精進。
林漢章(百城堂書店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