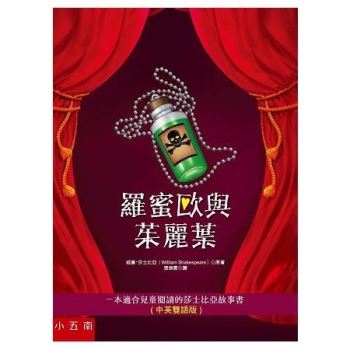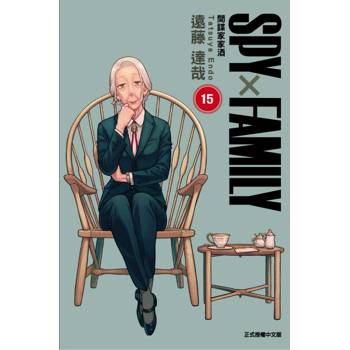我死了嗎?但為什麼你的凝視,還是讓我有「心跳」的感覺……
狂銷直逼70萬冊、話題日劇「改造野豬妹」原著作者醞釀4年最新力作!
日本亞馬遜網路書店讀者★★★★★感動好評!
即使所有人都忘了妳,我也忘不了妳的笑容。
因為妳的出現,我才明白,愛,能讓人為對方付出所有……
在別人眼中,這大概是恐怖的「靈異事件」,但從我第一次遇見妳那天開始,我就決心要守護妳了。
握住妳冰冷的手,看見妳眼神中的無助。
就算只有一次也好,請讓我緊緊擁抱妳!
讓我對妳說出心底的那句話……
一睜開眼睛,我的世界只剩下一片荒蕪,失去所有的觸覺和聽覺,連形體也徹底消失,你卻修補了我的孤單和寂寞。
就算只有一次也好,好想緊緊擁抱你!
讓你聽聽我心動的聲音……
作者簡介
白岩玄
一九八三年生於京都。高中畢業後曾赴英國留學,回國後,於大阪設計師專門學校畢業。
二○○四年,以小說《改造野豬》出道,不但銷量直逼七十萬冊,並被改編成熱門電視劇「改造野豬妹」,更榮獲「日本文藝賞」,以及入圍日本文壇最高榮譽「芥川賞」,成為該屆最年輕的入圍者。
白岩玄擅長運用新人類的語言,文筆詼諧卻具有淡淡的詩意。他的作品多以青春世代為背景,寫出年輕男女成長中的徬徨與迷惘,十分受到年輕讀者的喜愛與好評。
譯者簡介
連雪雅
一九八三年生,畢業於淡江大學應用日語系。喜愛閱讀,熱愛翻譯工作,譯有實用書《不出糗!54個優雅用餐秘訣》、《不失禮!45個聰明送禮秘訣》、《烤焦麵包》系列繪本、旅遊書《一個人的京都漫步手帖》、《旅行從我的房間開始》等。


 2010/07/14
2010/07/14 2010/06/21
2010/0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