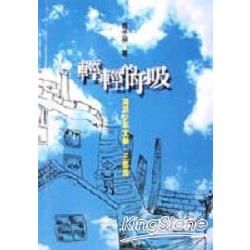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輕輕的呼吸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輕輕的呼吸
主 題
作者梅子涵追憶年少時的自己,追憶年少時的記憶,在耳畔輕輕地訴說著,年華似水的歲月。
內容簡介
《輕輕的呼吸》是海派少年文學三部曲的末了,卻可以是我們對於上海文學認識的開始。
在書中,我們看見童年時的、文革時的、大學時……各時期的梅子涵,看見他對於時代的想法,看見他小時候的記憶,看見他和外婆的真情流露……細緻的感情,一一呈現。
上個世紀的上海,上個世紀的感情,上個世紀的風景,是一段你我未必經歷過的時空,但是我們可以從此書中,去細細體會當時的情境及故事。
特色說明
作者梅子涵對過去的回憶,雖然是一種淡淡的筆觸,卻描寫出真實深刻的感情。每篇散文後面都有他的註腳,這是最大的特色,因為在梅式文字的表露之下,我們可以看出梅子涵對於寫作的想法及觀點,是一種簡單、平實中,卻不失真性情的筆法。
繪者洪波,上海人,留歐的他,作品呈現細膩的歐式的畫風,但是因為他的成長背景,使他在本質上仍舊保存著上海的特色,更顯露出文字中上海的風韻。
商品資料
- 作者: 梅子涵
- 出版社: 小魯 出版日期:2001-05-01 ISBN/ISSN:9578211686
- 語言:繁體中文 注音:內文含注音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192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