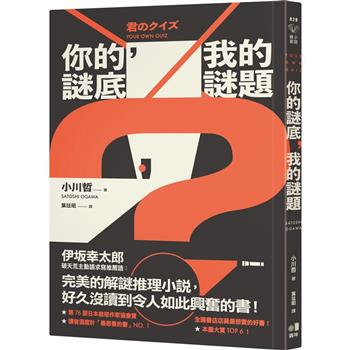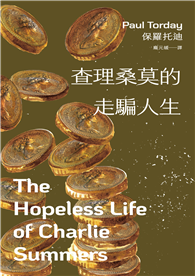我總覺得自己的心靈猶如一顆水滴,和其他的許多水滴聚成了一條河流,這條河流時急時緩,但它總是不停的流動,經過高山、田園、荒野、森林、沙漠、村莊、城鎮……之後回歸大海,然後為下一次人生的旅程做另一番的醞釀。
小時候外婆家巷口的臭水溝裡有的是停滯不動的死水,那發出惡臭的水是永遠也回不到大海的。有一次我在溝邊玩,一不小心掉了進去,渾身的臭味讓外婆怎麼洗也洗不去。舅舅和阿姨們為此事笑了好多年才漸漸淡忘。但是那死水的臭味卻成了我一生的警惕。我常常想,一灘水在一個地方停滯久了會變成死水,那麼人呢?在一個地方「呆」久了,他是否成為行屍走肉呢?至少我一定會的。往往,如果我在一個地方或環境裡超過了應待的時間,那死水開始發酵的味道便開始從我的皮膚侵入,然後坐立難安、氣血開始阻塞、食不知味、手腳冰冷、面色蒼白、兩眼無神。這般的病情發作了幾次之後,我也就久病成良醫,明白了病因,原來該動身的時候到了!
與其說我是一個旅行者,到不如說我是一個流浪者來得貼切。因為從一開始我就沒有什麼雄心大志,從沒想過要去哪裡那裡,打從懂事,命運就開始為我灌注流浪的血液,從高雄的外婆家搬到台北,台北到約旦,約旦到台灣,台灣到沙烏地,沙烏地到英國,英國到舊金山。十九歲那年,我又隨著命運回到台灣。在台灣碰到了和我一生四處漂泊的彼得,我們兩個一起去了一次泰國後,發現我們倆是最好的流浪拍檔,於是我們開始一起流浪了。我發覺這時我長大了,從此不再是命運一昧地帶著我,而我也開始帶著命運一起走。
彼得和我一樣從小就開始流浪的生涯,出生在加拿大落磯山派的他,小學的時候便和家人搬到新幾內亞,後來又到澳洲,十六歲時便背起行囊到巴黎。歐洲遊遍後,便在瑞士住下來,和三、五個好友夏天蓋房子,冬天下雪前便如候鳥般往南方遷移。他們一群人步行,搭便車,坐公車,經過義大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最後在印度棲息,如此往往返返地過了八個寒暑。我問他──為什麼是印度?他說了很多:那裡的生活費用低,旅費花得慢、那裡的氣候溫暖、那裡有許多有意思的東西、那裡有深遠的歷史、那裡有許多有意思的人!那裡是一個屬於靈性的世界!
與印度的約會果然震撼了我的心靈。那土地上的靈性,不但幫助我了解到許多我在別處了解不到的東西,亦幫我指引了心靈的方向。
回想外婆村裡的阿公老阿婆們總是在傍晚時拿出矮凳,順著自己的回憶說出大陸上的經歷,從人、鬼到狐仙、精靈。我們小蘿蔔頭都一個個聽得津津有味,直到家人喊了也不願意回去!綴著繁星的天空成了我們的屋頂,從這些來自中國各省的爺爺、婆婆口中,我們不但聽到了數不清的故事,也感受到了無限豐盛的感情,那些回憶中的故事勾畫出了村中每個人對自己家鄉每一草、每一木、每一靈、每一魂的思念,那些故事參雜著他們動人心魄的感情。他們沒有去管措辭,他們有的甚至口齒不清,結結巴巴,但是我們愛聽!愛聽的不僅是那些我們從沒見到的人和事,也是他們那沒有說出的感情!後來我才了解,原來對我們這些毛頭說故事,成了他們不得不做的事情,不做,對不起他們家鄉的情和靈,對不起我們這些迷糊的小鬼,也對不起他們自己的心靈!
這些故事隨著成長漸漸變得模糊,但是老人們對生命那倔強的感情卻早已在我身上烙了印。暗地裡,我知道我的骨子裡一直流著村子裡老人們那說故事的血液,畢竟外婆也是每天說故事的阿婆們之一。
印度的旅程讓我體會了村中老人們要說出那些故事的心情。於是,說出這段我在印度的故事,成了我不得不做的事情。暗地裡,我明白,寫出在那土地上所遇到的故事,才對得起那時和我相遇的人們和心靈,對得起想聽到的人們,並對得起自己的感情!
拖了那麼多年才將它寫出來,是因為那時年輕,即使有許多經歷,也無法將一個古老的國度所帶的氣息描繪出來,經過多年的沉澱,現在我終於知道如何自然地讓這些故事裡的生命和讀者的心靈契合,讓大家的精神與我們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