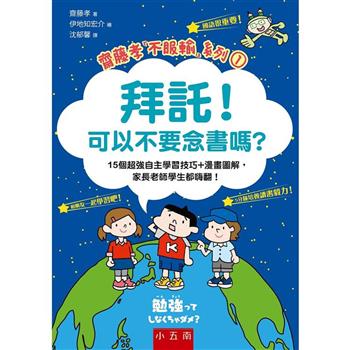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飲食男女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30 |
二手中文書 |
$ 158 |
文化研究 |
$ 176 |
文化研究 |
$ 180 |
社會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飲食男女
自喻「饞宗大師」的沈宏非先生是目前活躍於中國報刊的新銳專欄作家,長期任職於媒體的他,對任何事物都有一套獨特的見解與觀察。從「美食」中看人性、看生活,甚至是男女關係,信手拈來,無不美食滿目,還妙趣橫生,不僅滿足了精神上的味蕾,也豐富了視覺上的食慾。 本書特別選出沈宏非先生發表於美食專欄上,近60篇的「美味」文章,喜愛與美食「來點關係」的老饕們,不容錯過!
商品資料
- 作者: 沈宏非
- 出版社: 大旗出版 出版日期:2006-11-01 ISBN/ISSN:9578219571
-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88頁
- 類別: 中文書> 社會科學> 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