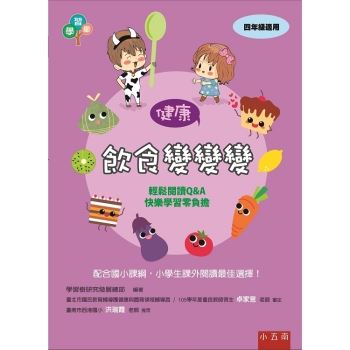此書,最初的標題只有「回到史坦尼斯拉夫斯基」。這也是書中一個篇章的標題,是書中最長,寫作時間最久的一篇,也是最初開始動筆的一篇。
那是五年多前,看到《表演藝術》月刊有一個「回到劇場」的專題,看了後就寫了這篇的初稿。後來也接續地寫了其他幾篇。去年吧,《表演藝術》製作了兩期的回顧二十世紀戲劇的專輯,討論了許多問題,但是,不知何故,裡頭卻沒有關於表演的討論,然而,過往一個世紀裡,從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體系開始到果陀斯基,產生了眾多的表演實踐和理論,這個現象是以往世紀中所沒有的現象,而且這些實踐和論述對演員的關注與探討的深度,也是前所未見。
我不清楚為什麼是在小劇場運動那麼多年之後,才驚覺到我們對演員問題的缺乏關注,也不明白一個回顧,竟然對繁多的表演美學不置一詞。我們也找不到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著作,或是其他的表演理論的書籍。空白或是迴避?這個空白與迴避的現象,對照於劇場中高唱著「身體」的現象,讓事情顯得弔詭和難解。
我想是這些促使我去書寫史坦尼斯拉夫斯基,這個現代表演實踐的源頭,和相關連的幾個現代戲劇工作者對表演的想法。而似乎,從一開頭,我就無意只將表演和演員的問題定位為一種職業,一種所謂的專業。而是試圖從較本源的意義上去說明演員的問題。這並非我個人的想法,而是這些現代戲劇開創者對演員這一問題的根本看法。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說得很清楚,他所要尋找的根本不是什麼演員,而是人:「我的目的是使你們把自己重新創造成活生生的人。」這遠非僅是寫實主義戲劇,史氏在他處提過:「演員是那個想在自己身上創造出另一種生命,另一種比圍繞在我們現實生活更加深刻和美好的生命的人。」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這個命題,這個對追求一個新的人的命題,難道不使我們想起波特萊爾所說的「現代人」:「現代性,並不是一個與現在當下的關係而已,它更是人和其自身有待建立的一種關係形式……現代人是那個企圖發明、製造出他自己的人。」
現代表演美學和其實踐為這樣一個「現代人」和「現代性」中重要的「主體性」課題,提供了一個具體的實踐和技術,一個人如何去觀察、詮釋人和人如何去製作人的技術和思考的場域。也是在此,演員問題才與政治社會問題相遭遇,就如同也是俄國戲劇家艾夫瑞諾夫所說的「戲劇性�是一種迫使人改變他自己和改變他所處身其中的世界的本能。而戲劇之本質難道不就建立在它違犯、顛覆由自然、國家和社會所加諸的種種既成規範的能力之上?」
我想許多在劇場中努力的工作者都會贊成上面艾夫瑞諾夫的想法,然而在種種討論顛覆與收編的問題時,我們是否遺忘了技術的問題?一個「如何」的問題。布雷希特曾說過他的戲劇是一個「哲學」的戲劇,「哲學」,是依照馬克思所定義的那個「能改變世界」,而不是那個去解釋世界,的哲學。而對於改變世界的技術問題,布雷希特說,不是在於如實地描述世界,而是建立在於能「將世界描述為可被改變的」的敘事能力。這又回到了波特萊爾,他說:「使其改觀並非是對現實的取消,而是在現實的真相和自由的運作之間進行一場艱難的遊戲�對現代性的姿態來說,現在的崇高價值是無法與對現在、當下的激烈想像相分離的,是在不取消現在,並將它如實地掌握的同時,將它想像成它所不是的樣子,來使其能有所改觀。」從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布雷希特、莫雷諾和波瓦乃至於果陀斯基、亞陶,都在實踐著這個「艱難的遊戲」,讓人和生活本身成為一種技藝。而亞陶這位有現代戲劇酒神之稱,從體認到「真的,我說,我,我尚未出生」,後必須經歷過二十三年,包括九年精神療養院的「艱難遊戲」後,他才得以寫道:「我,安東尼.亞陶,我是我的父親,我是我的母親和我自己。」這「艱難的遊戲」不是什麼別的,而是如亞陶所說的,去「發明自己」、「發明生活」。
此書以「回到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為題,其所要說的,也同時是一個回到「寫-實」的想法,一個很可能未被深思就過早地被我們所拋棄的路線;基進地回到「寫-實」,在那個如何「如實地掌握現實,而又同時能將現實描述為可被改變」的命題下去思索「戲劇」這面「特殊的鏡子」與世界的映照-書寫關係。已故的法國當代導演維特茲(A.Vitez)曾強調過,如果沒有理解史坦尼斯拉夫斯基,那我們不但無法認識梅耶荷德也無法理解布雷希特。而我們也會吃驚於果陀斯基的如此回憶:「我的全部關於戲劇的基礎知識,全是來自於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我相信在史坦尼斯拉夫斯基那裡存在著能開啟所有創造性大門的鑰匙。」在我們錯誤地將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與「認同作用」劃上等號時,布雷希特卻站出來替他辯護:「史坦尼斯拉夫斯基之所以強調認同作用僅僅是因為他憎惡那些為了討好迷惑觀眾的演員」,而「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現實主義是鬥爭性質的,因為他是個革命者,他摧毀對更迭不已的現實的錯誤表述,並代之以如實正確的表述。」並推崇史氏晚期的「形體動作理論,很可能即是他為建立一個新的戲劇最具意義的貢獻。」這些現代戲劇的開創者,無一敢或忘史氏的影響和債務。然而,我們卻將史坦尼斯拉夫斯基「遺忘化」、「心理學化」,將梅耶荷德「風格化」,將布雷希特「陌生化」,將果陀斯基「神聖化」�我想,我們遠遠尚未離開「現代」,而是應該基進地「回到現代」。
如果我們還有什麼猶豫,請看看李察爾德(T.Richards)這位果陀斯基的傳承者的話:「當我還是一位年輕的演員時,我曾經自問:這些寫實的表演技法真的是必要的嗎?我第一次讀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書時,覺得十分厭煩。然而,這種想法是文藝青年業餘式的想法。�演員的藝術,不是非得局限於寫實的情境之中不可。但是往往,演員藝術的層次與質越是高,他就越是深入於寫實的基礎之中,和越能進入常態之外的領域:那個純粹驅力的活生生的流動之中。�但是,要讓演員的藝術達到此一高度必須將其基礎建立在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寫實表演之上,而且為了朝向另一個更高的層次,認識此一基礎更是絕對必要的。」而「寫-實」可以把我們引向何方呢?與布雷希特同樣讚揚「抄襲」美學的電影導演高達這樣說:「我和布雷希特一樣,也在尋找寫實主義。」
希望此書或能有助於我們以一個積極、不迴避的態度來面對現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