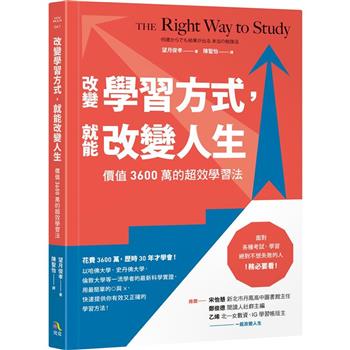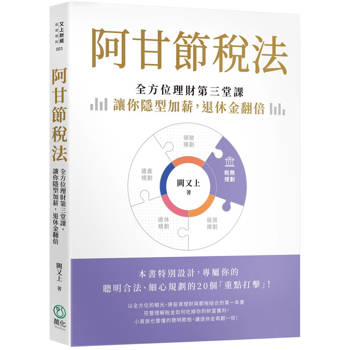人生得意須盡歡
在我奇異的一生當中,那算是最狂亂的一年了。在時序進入倒數的最後幾秒,我的身邊充斥著人們的呼嘯聲。至於我,大概就是暴風中心的燈塔;混亂的煽動者了。
那是一九九六年的除夕夜,芝加哥海軍碼頭擠滿數千名打扮怪異的人們。他們仰頭看著我,希望我會和他們一起度過這一年一度、意義非凡的時刻。從他們極度興奮的嘶吼聲及瘋狂的舉止看來,似乎非常贊賞我一身昂貴的行頭。我打扮的像是媚惑人心的埃及豔后克麗奧佩卓(Cleopatra),頭戴金色的古羅馬武士頭盔;臉上戴著一副四旬齋時遊行用的面具;脖子上是珠寶項鍊;身披一件飾有金色和紫色金屬片、閃閃發亮的斗篷;在我的私處用了一面盾牌遮掩;腳踩綴有蕾絲花邊的金漆舞鞋。我的腳毛剃了,臉上的妝完美至極。我的笑容誇張的如同門外滿載三十個朋友的超大型旅遊巴士上頭的每一個人。
所以說囉,我怎麼可能不高興呢?幾年以前,我還不知道自己是否會活到一九九七年,更不曾想過生命還有再度燦爛的可能。在我漂泊有如船員的球員生涯中,曾經度過毫無歡樂、非常糟糕的除夕夜。我還記得不止一次獨自一人在昏暗的房間內瞇起眼睛,透過破舊的黑白電視機看著時代廣場上的大彩球飄落,心裡卻納悶:這除夕夜的倒數計時是代表著嶄新的開始,或只是又一年一成不變的苦悶日子?。
當你度過了好幾年空虛痛苦的日子,你將會竭盡所能地歡慶得來不易的大好時光。因為如此,我為了這個節日砸下八萬塊錢,並從西雅圖請來「燭盒樂團」(這是我最喜愛的樂團之一)來增添派對的娛樂效果。這也是為什麼我租下安柏士德大飯店的兩層樓,邀請我全國各地的朋友齊來狂歡;並且租來一輛旅遊巴士,上頭載滿各種美酒,以履行我和爵士樂手的約定。這更是為什麼我翻遍芝加哥地區的戲劇服裝店,只為尋找我心目中理想的斗篷,並花一萬塊錢訂做。
人內心的平靜與滿足感,是無法以價錢衡量的。所以,這個除夕夜的鋪張花費並沒有讓我猶豫或退縮。當我俯視樓下裝飾華麗的舞池——旋轉的燈光映射在巨大的柱子上;各色的氣球裝飾在天花板;人群擁擠著準備在倒數時用力嘶吼出震動屋瓦的歡樂——我知道我將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刻。當聚光燈打在我的身上時,我總算搶到麥克風,耳朵裡只聽到我自己的聲音、人群的狂吼聲、和我持續的心跳聲。我們開始倒數計時的時候並沒有看著時鐘,但是有什麼關係呢!那已經不重要了,新的一年已經到來。
這是我的人生。
「我們現在有二十秒的時間,」我聽見自己這麼說。
「開始……十九,十八,十七,十六,十五,十四……」我停下來,聽著我的聽眾們全心全意,不願歇止地放聲倒數。「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哪——哪!芝加哥,新年快樂!咿噢啦!」氣球飄落下來,「燭盒」也已就位,準備要用最高分貝的音量吵醒整個芝加哥。「我知道你們全是為了看我而來到這裡,」我對著麥克風大喊「但是你們覺得『燭盒』如何?」當彼得•克利特舞動著他的身體和吉他,凱文•馬汀唱起「簡單的體認」時,我扔下麥克風,跳下舞台和朋友們一起狂歡。一九九七的狂亂就此拉起序幕。
我的人生故事,盡是些簡單不過、微不足道的事。我有太多的故事可以分享,雖然結果很單純,但是學習的過程卻是一團混亂。我花了三十二年的時間尋找自我,甚至到現在,三十六歲的年紀,我仍舊每天一點一滴地在學習。
我希望其他人不必再經歷這些:過去我在追尋自我的過程中所遭遇的痛苦、不快、和迷惘。我希望不再有人像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必須度過糟糕的除夕夜。
在達拉斯的橡樹崖區貧民窟長大,我所知道的新年不過是一個人們動用槍火或使用暴力的藉口,他媽的不顧後果。換句話說,新年和其餘的日子幾乎沒啥兩樣。我在童年時期看到不少人死掉,更荒謬地是,大都是因為他們實在是投錯了胎、生長在貧民窟、而且生不逢時。話說回來,在那個時候,似乎所有的時辰都是錯誤的時辰。誰知道你是否能安然捱到新年?更別說能否能僥倖存活到明日了。
對那些在過去就已經認識我的人來說,是絕對沒有辦法想像,現在的我能帶領三千多人,一起為一九九六年倒數。過去的我,是全世界最害羞、最沒用的東西,非常害怕跟任何人交談,甚至包括熟識的人。我沉浸在自己編織的幻想世界中,不讓其他人參與。同住貧民窟的人們和我交談,大部分的時候只是想捉弄我,或譏諷地告訴我,我的長相是多麼的可笑。大大的耳朵和塌陷的鼻子,再加上瘦皮猴似的削瘦身材,我猜想我是真的長得很奇怪。任憑他們侮蔑,我只是置之不理,全心投注在我喜愛的事情上。然而這些侮辱在我內心造成很大的傷害,只是當時我實在太過害羞和膽怯而不知如何反擊。在貧民窟,向來會有幾個倒楣鬼會受到無情的恥笑,而我 ,總會是其中的一個。
話說回來 ,當時我從來沒有機會和女孩子上床,就算我手中握有一疊百元美鈔,也引不起妓女的興趣。我實在太醜、太害羞、太閉塞了,因此,這樣的好事從不會落到我的身上。為了讓自己好過一些,我在十七歲時和三個朋友定訂了一項條約:我們三個出入都必須在一起,就我們三個哥兒們,不准和女孩子約會。這項約定一直持續了好幾年,但若我們之中有人面臨墜入情網的境地,這約定便提早取消。那時的我也不喝酒,因此我並不參加鎮上喧鬧的宴會或酒會。我將所有的心事藏在心底,終日沉默不語。事實上,似乎也沒有人對我的想法感興趣。我的母親雪麗(Shir1y)忙於工作;而我的兩個妹妹,黛博拉(Debra)和金(Kim),卻已經是籃球選手。至於我,不過是約會止步公約的成員,長相可笑的丹尼斯。
令人感到害怕的是,我對那段日子的記憶是少之又少。我想,我會有那麼多模糊的或是遺忘的記憶,是因為對我來說,回想那段日子實在太痛苦了。它們並不全然是悲慘的回憶。我也享受過美好時光,但是和我現在所經驗的充滿迷人魅力的生活相比,兩種美好的感覺是非常不相同的。在我十七歲那年,我想盡辦法弄到了一輛老舊的蒙地卡羅。這輛車是我的喜悅和驕傲。我加入蒙地卡羅俱樂部,和一群業餘人士在麥當勞的停車場或類似的地點聚會,並且開著我們的愛車兜風。上百輛蒙地卡羅一同在達拉斯的大街小巷呼嘯地穿梭奔馳,尋找刺激和新鮮事兒。我並不真正知道自己在尋找什麼,只知道我還在尋找。生活不應該是這樣侷促受限制的,就是不該如此。一定還有其他的東西等著我去發掘。
我在十七歲那個年紀,是用一種迥異於現在的有利「位置」來看這個世界。至少,我十七歲時就比現在矮多了。高中畢業時,我只有五呎十一吋,比起現在的身高,足足少了有九吋。受大家歡迎的孩子或是運動選手總是瞧不起我。在我的腦袋裡裝滿了許許多多的大夢想,可是它們卻被拘禁在我瘦小的身軀裡。我渴望張開翅膀和天上的老鷹一起振翅高飛,但是事實生活中,我卻像是垃圾場裡,和其他流浪狗一起在垃圾堆中覓食的髒狗。
那段日子,我也和許多人一樣,曾經有過許多夢想,夢想成為引人注目的焦點,受到許多人的關心注意。但是,那些夢想在現實生活中似乎是遙不可及,因此,我從來也不曾當真。大部分的時間,我只是一天過一天。生命中最主要的目標大概就是不被現實擊垮了。我抓住任何可以使自己快樂的機會,試著不被不長眼睛的子彈打到,大部分時間便是用來思考下一餐吃什麼了。
日子似乎就這樣過了。而我,大概是要照著這樣一成不變的循環過一輩子吧;否則直到我死了,或因犯罪被關,又或染上毒癮,才有可能脫離這樣的生活。幸好我接觸到宗教,聖靈的光輝照耀我、警醒我、保護我,將我拉離了這樣的命運。突然有一天,我開始長高……長高,長高,再長高。我從來不曾希望自己長得更高些,或者應該說,不曾對長高這件事懷有太大的希望。然而就在這個時候,我彷彿感應到來自上帝的告誡:你將會經歷一段探索自我的歷程,而不再終日蹉跎生命。並且,籃球將會成為你步向成功的工具,因為你擁有傲人的身高。
所以,在毫無選擇的情況下,我開始打球;而我,也開始綻放生命的花朵。
籃球場是第一個讓我在表現自我時,感覺舒服自在的地方;是第一個我不會怯懦或感到沒有歸屬感的地方。我開始吸引到人們的目光與關注,老實說,我喜歡這樣受到注意的感覺——雖然我還不知道如何回應人們的關注。
因為籃球,我進入奧克拉荷馬的都蘭隊(Durant),為西南奧克拉荷馬州立大學效力,也因此認識了我最要好的朋友卜萊恩•理奇(Bryne Rich),和另外一位一輩子的好兄弟比爾•潘茲(Bi11 PenZ)。我和卜萊恩的家人住在靠近波奇多的地區。我們三人在許多人的眼裡,或許是非常不協調……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禁區撒野:NBA籃板王羅德曼自傳 Part Ⅱ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99 |
中文書 |
$ 299 |
運動 |
$ 306 |
運動名人 |
$ 306 |
運動休閒 |
$ 306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禁區撒野:NBA籃板王羅德曼自傳 Part Ⅱ
★ 繼《紐約時報》暢銷榜冠軍《盡情使壞》後,籃板王羅德曼最新力作!
★ 本書獲美國亞馬遜 4 顆星好評!
小蟲羅德曼是八○年代以來,唯一一個曾分別輔佐兩支球隊拿下NBA總冠軍的球員。他曾經差一點自殺,一夜頓悟後,開始以另一種人生觀生活,經世駭俗、引人非議,儘管如此,羅德曼所散發出的吸引力總比他的壞男孩形象或他染成的領帶的頭髮更深、更受歡迎,在球場上的表現也突飛猛進,連拿六屆籃板王,很可能成為始終無法進入籃球名人堂的一代巨星。
《禁區撒野》是暢銷書《盡情使壞》的續集,羅德曼在這本書中更大膽的暴露他進入NBA之後從性到毒品到搖滾樂等一切事物的獨特看法,他變得撒野使壞的原因。他憎惡任何形式的偏執,避免使用違禁藥物,他也常常會執著的以極端方式去面對裁判來捍衛他的權利。又為什麼他總是夜夜狂歡的生活,規律的作息反而導致表現奇差……;你想知道小蟲為何有打死不退的求勝意志力嗎?為什麼他總是想盡辦法激怒對手?外表叛逆的他竟篤信輪迴與因果報應,羅德曼究竟還有多少令你瞠目結舌的行徑,就等您來揭密了。
作者簡介:
丹尼斯.羅德曼(Dennis Rodman)
前美國NBA著名籃球運動員,以擅長爭搶籃板球及出色的防守著稱,擁有「籃板王」的美譽,也因為防守時像蠕蟲一般扭動身體並黏在對手身上,被球迷戲稱為「小蟲」(The Worm)。主要位置是大前鋒,雖然僅有201公分的身高,但他憑藉著驚人的意志、紮實的卡位動作、準確的籃板球及防守預判能力、以及強大的侵略性,使他成為頂尖的籃板手兼防守者。在球場內外,羅德曼各種具爭議性的舉動令他備受矚目。2011年羅德曼的底特律活塞10號球衣退休,同年入選奈史密斯籃球名人紀念堂。
章節試閱
人生得意須盡歡
在我奇異的一生當中,那算是最狂亂的一年了。在時序進入倒數的最後幾秒,我的身邊充斥著人們的呼嘯聲。至於我,大概就是暴風中心的燈塔;混亂的煽動者了。
那是一九九六年的除夕夜,芝加哥海軍碼頭擠滿數千名打扮怪異的人們。他們仰頭看著我,希望我會和他們一起度過這一年一度、意義非凡的時刻。從他們極度興奮的嘶吼聲及瘋狂的舉止看來,似乎非常贊賞我一身昂貴的行頭。我打扮的像是媚惑人心的埃及豔后克麗奧佩卓(Cleopatra),頭戴金色的古羅馬武士頭盔;臉上戴著一副四旬齋時遊行用的面具;脖子上是珠寶項鍊...
在我奇異的一生當中,那算是最狂亂的一年了。在時序進入倒數的最後幾秒,我的身邊充斥著人們的呼嘯聲。至於我,大概就是暴風中心的燈塔;混亂的煽動者了。
那是一九九六年的除夕夜,芝加哥海軍碼頭擠滿數千名打扮怪異的人們。他們仰頭看著我,希望我會和他們一起度過這一年一度、意義非凡的時刻。從他們極度興奮的嘶吼聲及瘋狂的舉止看來,似乎非常贊賞我一身昂貴的行頭。我打扮的像是媚惑人心的埃及豔后克麗奧佩卓(Cleopatra),頭戴金色的古羅馬武士頭盔;臉上戴著一副四旬齋時遊行用的面具;脖子上是珠寶項鍊...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1. 人生得意須盡歡
2. 為什麼小蟲愛作怪
3. 跟著感覺走
4. 決不出賣自己
5. 不時脫軌一下
6. 性事一籮筐
7. 小蟲徹夜未眠
8. 對毒品說「不!」
9. 羅德曼說名人八卦
10. 戲弄對手
11. 雌雄同體
12. 信、望、愛
13. 法律難擋特權
14. 自由
15. 不虛此生
2. 為什麼小蟲愛作怪
3. 跟著感覺走
4. 決不出賣自己
5. 不時脫軌一下
6. 性事一籮筐
7. 小蟲徹夜未眠
8. 對毒品說「不!」
9. 羅德曼說名人八卦
10. 戲弄對手
11. 雌雄同體
12. 信、望、愛
13. 法律難擋特權
14. 自由
15. 不虛此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