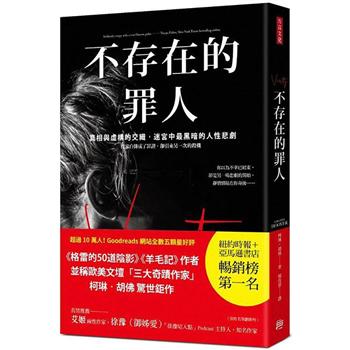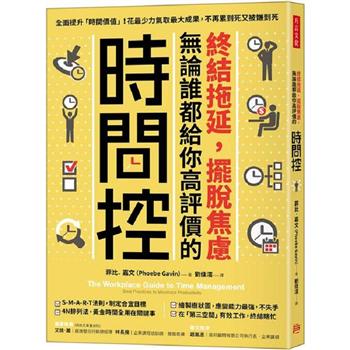★ 世界知名作家喬斯坦.賈德之作!
★ 美國亞馬遜4顆星好評!
你是誰?我是誰?
誰是作者?誰是故事的主角?
誰才是故事的主宰?是誰在說故事?這又是誰的故事?
這一切……到底有沒有答案?
早熟的賈德有著過於活躍的想像力,在他的內心世界中,除了天馬行空的幻想外,還有一個別人看不到的朋友——小米人。這個戴著綠色氈帽,手持竹杖子的小矮人,不時驅使、鼓動賈德去做某些事情。小米人是敵?是友?是邪?是正?為了維持生計,賈德運用他豐富的想像力,賣點子給作家,讓他們寫出一本又一本暢銷的故事。這些千奇百怪匪夷所思的故事,是想像力下的產物,還是真實世界的反映?是賈德的幻想,還是他的生命經驗?
這本書是賈德將一個奇妙的故事編織在一起,內容描述馬戲團團主尋找失散多年的女兒。在一連串的巧合下,女孩成為馬戲團中有名的空中飛人,不幸在一次表演意外中,不慎摔斷了脖子,團主驅前彎下腰時,他注意到女孩脖子上有琥珀的護身符,這是他十六年前,親身女兒被洪流沖走時所配戴的飾品,雖然找到自己的女兒,卻也同時再一次失去她。書中,賈德不斷穿叉著幾則小故事,每篇故事都是發人醒思、耐人尋味,他再一次運用魔幻手法,藉由成人童話的形式,在想像與現實間遊走,讓讀者可以經由本書對於生命不斷地探索與省思。
作者簡介:
喬斯坦‧賈德(Jostein Gaarder)
挪威世界級的作家,西元一九五二年出生於挪威首都奧斯陸,大學時主修哲學、神學以及文學,曾擔任文學與哲學教師,自一九八六年出版第一本創作以來,已成為當代最重要的北歐作家。
賈德擅長以對話形式述說故事,能將高深的哲理以簡潔、明快的筆調融入小說情境,他最著名的小說《蘇菲的世界》享譽全球,被翻譯為四十多種語言,全球銷售量超過三千萬本。他的作品動人心弦,啟發無數讀者對於個人生命、於歷史中的定位以及浩瀚宇宙的探討。
賈德除致力於文學創作,啟發讀者對於生命的省思外,對於公益事業亦不遺餘力。他於一九九七年創立「蘇菲基金會」,每年頒發十萬美金的「蘇菲獎」,鼓勵能以創新方式對環境發展提出另類方案或將之付諸實行的個人或機構。
【得獎紀錄】
1990年《紙牌的祕密》獲得「挪威兒童及青少年評論協會獎」和「文化科學事務部文學獎」,並當選為該年度兒童及青少年最佳讀物。
1991年《蘇菲的世界》獲得挪威宋雅‧赫格曼那斯(Sonja Hagemanns)童書獎。
1993年《蘇菲的世界》、《紙牌的祕密》、《伊麗沙白的祕密》同時獲得學校圖書館員協會獎。《蘇菲的世界》獲得德國時報週刊(Die Zeit)的文學獎。《西西莉亞的世界》獲得挪威暢銷書獎,同時提名柏瑞格獎(Brage)。
1994年《蘇菲的世界》獲得德國青少年文學獎。
1995年《蘇菲的世界》獲得義大利邦卡瑞拉獎(Bancarella)及菲萊以阿諾獎(Flaiano),在台灣則獲選為台灣中國時報開卷版95年度十大好書,並獲得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
【歷年作品】
喬斯坦‧賈德自的作品深受讀者喜愛,名列各國暢銷書排行榜,並且榮獲無數獎項的肯定,其重要作品如下:
1986《賈德談人生》(The Diagnosis and Other Stories)
1987《沒有肚臍的小孩》(The Children from Sukhavati)
1988《青蛙城堡》(The Frog Castle)
1990《紙牌的祕密》(The Solitaire Mystery)
1991《蘇菲的世界》(Sophie's World)
1992《伊麗沙白的祕密》(The Christmas Mystery)
1993《西西莉亞的世界》(Through a Glass, Darkly)
1996《我從外星來》(又名《喂,有人在嗎?》)(Hello? Is Anybody There?)
1996《主教的情人》(Vita Brevis)
1999《瑪雅》(Maya)
2001《馬戲團的女兒》(The Ringmaster's Daughter)
2003《橘子少女》(The Orange Maid)
譯者簡介:
江麗美
台中人,中山大學外文系畢,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新聞暨大眾傳播學院碩士。曾任美語中心教師、美國舊金山太平洋電視公司記者與編譯、民眾日報編譯等職。譯作包括《生與死》、《耶穌談生活》、《街頭律師》、《馬里多瑪》、《瑪雅》、《有效壓力管理》等書。
章節試閱
沛德小蜘蛛
我認為我的童年是快樂的。我的母親卻不這麼想。沛德在上學之前,她就已經得知他並不合群。
我媽媽第一次被通知到校懇談,去的是日間托兒所。我會整個早上坐在那兒觀看別的小朋友玩耍。但我並不覺得不好。看著他們如此興高采烈地活著,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許多小孩都覺得看活生生的貓、金絲雀或倉鼠很好玩;我也是,不過旁觀活生生的小孩更是有趣。這時候,是我在控制他們,是我來決定他們該做什麼或說什麼。他們自己並不曉得有這回事,托兒所的老師也渾然不察。有時候我發燒了,就得待在家裡聽股票行情。這時候,日間托兒所裡毫無動靜。孩子們無所事事,只是穿穿脫脫他們的運動服,穿穿脫脫。我並不羨慕他們。我想他們連早上十一點的點心都沒得吃。
我只有在星期日能見到我的父親。我們一道去看馬戲團。馬戲團其實還不錯,但我一回到家,就會開始計畫自己開個馬戲團。那會好得多。那是在我開始學習寫作之前的事,但我會在腦袋裡組成一個自己最喜歡的馬戲團。一點問題都沒有。我也會畫馬戲團,不光是那大頂棚和座位而已,還有所有的動物和演出者。這很難的。我對繪畫並不在行。我在開始上學之前許久,便放棄畫畫了。
我坐在大地毯上一動也不動,我媽媽問了我好幾次在想些什麼。我說我在玩馬戲團,這是真的。她問我們是不是該玩點別的。
「那個坐在高空鞦韆上的女孩叫做潘尼娜.瑪尼娜,」我說,「她是馬戲團團主的女兒。但是馬戲團裡面沒有人知道這件事,連她,或團主都不知道。」
我媽媽凝神聽著,她把收音機聲音關小了,我繼續說道;「有一天她從鞦韆上掉下來,脖子扭傷了。那是最後一場的表演,當時城裡已經再也沒有人要買票看馬戲。團主彎下腰看那個可憐的女孩,這時候他看見她脖子上有一條細細的項鍊。項鍊上有個琥珀的小裝飾品,那裡面有一隻活在好幾百萬年前的蜘蛛。團主看到這個,才明白原來潘尼娜.瑪尼娜就是他自己的女兒,因為在她出生那天,他就為她買了這個罕見的琥珀飾品。」
「所以至少他知道他有個女兒。」我媽媽插嘴道。
「但他以為她已經被淹死了,」我解釋說,「你知道,團主的女兒在一歲半的時候,掉到阿可爾河裡去了。那時候她只是普普通通的安莉絲。之後團主就不曉得她還活著了。」
我媽媽睜大了眼睛。她看來似乎不怎麼相信我的故事,所以我說道;「但是很幸運,有個命相師自己一個人住在河邊的一輛粉紅色篷車裡,她把團主的女兒從那冰冷的水裡救了出來,從那以後女孩就和這個命相師一同住在那輛篷車裡。」
媽媽點起了一根香煙。她站在那兒玩著一件緊身戲服自娛。「她們真的住在一輛篷車裡嗎?」
我點點頭。「團主的女兒從一出生就住在馬戲團的聯結卡車裡。所以要她住在一棟現代的公寓房子裡,她會覺得更奇怪。那位命相師根本不知道那小女孩叫什麼名字,所以把她取名做潘尼娜.瑪尼娜,她一直到今天都還叫這名字。」
「可是她又是怎麼回到馬戲團裡的呢?」媽媽問道。
「她長大了啊,」我說,「這很容易了解的。然後她就用她自己的兩條腿走到馬戲團裡。那也一點都不難啊。這些事情都發生在她癱瘓以前!」
「但是她根本就不記得她爸爸是個馬戲團團主啊!」我媽媽發出抗議。
我真覺得失望極了。這不是第一次我媽媽讓我覺得失望了;她有時候真的很笨。
「我們早就說過這個了,」我說,「我告訴過你,她不知道她是馬戲團團主的女兒,團主也不知道這件事。他從她一歲半後就沒再見到她,當然也就不認得他女兒了。
我媽媽覺得這個部分我應該重想一遍,但是沒有這個必要。「自從命相師一開始把團主的女兒從河裡救起來,她就瞪著她的水晶球,預言這個小女孩會變成一個很有名的馬戲團演員,所以有一天,這女孩就用自己的兩隻腳走到馬戲團裡去了。一個真正的命相師在她的水晶球裡看到的一切都會成真。這就是為什麼命相師給了女孩一個馬戲團樣的名字,為了安全起見,也教了她一些空中盪鞦韆的把戲。」
我媽媽把她的香煙按熄在綠色鋼琴上的一個煙灰缸裡。「但是為什麼命相師需耍去救她……?」
我插嘴道︰「潘尼娜.瑪尼娜剛到馬戲團展示她的能力時,立刻就被錄取了,不久她就和艾伯特(Abbott)跟卡斯特羅(Costello)一樣有名。但馬戲團團主還是不知道那是他女兒。如果他知道,當然就不會允許她去做那一大堆鞦韆上的特技了。」
「好吧,我輸了,」我媽媽說,「我們是不是該去公園裡散散步呢?」
但我繼續說︰「那個命相師的水晶球還告訴她,潘尼娜.瑪尼娜會在馬戲團扭傷她的脖子,你知道一個真正的預言是沒有辦法扭轉的。所以她把她所有的家當都收拾好,到瑞典去了。」
我媽媽到廚房去拿個東西。現在她站在鋼琴前面,手上拿顆大甘藍菜。我可以肯定那絕對不是什麼水晶球。
「她為什麼到瑞典去?」她一臉迷惘地問我。
我想了一會。「那麼潘尼娜.瑪尼娜在扭到脖子,再也不能自己照顧自己之後那個馬戲團團主和命相師就不用為了她該去和誰住在一起吵來吵去啊。」我說。
「那個命相師知道馬戲團團主是女孩的爸爸嗎?」我媽媽問。
「潘尼娜.瑪尼娜要去馬戲團的時候,她才知道的」我解釋道,「一直到那時候,水晶球才告訴她,女孩會在扭到脖子之後,和她的爸爸團圓,那麼這位老太太就可以開她的篷車到瑞典去。她覺得潘尼娜.瑪尼娜可以和她爸爸團圓是很棒的,但是她得扭到脖子他才會認出她來,這就不太妙了。」
我覺得有點為難,不曉得該怎麼繼續下去。不是因為很難說,正好相反,而就只是因為有太多可能的發展可以選擇。「現在潘尼娜.瑪尼娜在馬戲團裡,坐在輪椅上賣棉花糖,」我說,「那是一種很特殊的棉花糖,它會讓大家看小丑表演的時候,笑得太厲害而喘不過氣來。有一回,有個男孩真的喘不過氣來。他覺得那個小丑會讓他發笑實在很好玩!但是不能呼吸就不那麼好玩了。」
這其實就是潘尼娜.瑪尼娜故事的結尾。我已經開始說那個因為笑得太厲害而不能呼吸的男孩的故事。還有好多其他馬戲團的演員要考慮進去。我對這整個馬戲團都有責任的。
我媽媽並不明白這個問題。「我想潘尼娜.瑪尼娜也有個媽媽囉?」她說。
「沒有,」我說,(或者更正確的說,我想我是尖叫出來的)「她其實已經死了!」
然後我就開始哭了。我也許哭了一整個小時。一如以往,是我媽媽來安慰我。我不是因為故事很哀傷才哭起來的。我會哭,是因為我被自己的想像力嚇到了。我也很怕那個帶著小竹杖的小矮人。他在我說故事的時候,一直坐在那個圓圓的波斯椅墊上……
沛德小蜘蛛
我認為我的童年是快樂的。我的母親卻不這麼想。沛德在上學之前,她就已經得知他並不合群。
我媽媽第一次被通知到校懇談,去的是日間托兒所。我會整個早上坐在那兒觀看別的小朋友玩耍。但我並不覺得不好。看著他們如此興高采烈地活著,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許多小孩都覺得看活生生的貓、金絲雀或倉鼠很好玩;我也是,不過旁觀活生生的小孩更是有趣。這時候,是我在控制他們,是我來決定他們該做什麼或說什麼。他們自己並不曉得有這回事,托兒所的老師也渾然不察。有時候我發燒了,就得待在家裡聽股票行情。這時候,日間托兒所裡...
作者序
序幕
我的大腦翻騰著。隨時都有千百種新的點子冒出來。它們就是如此這般源源不絕。
程度上的控制思潮也許還有可能,但是要停止思想就未免強人所難。我的腦袋裡漲滿了點子,我無從解決它們,唯有新的想法將舊的驅逐出境。我無法把它們分開。
我很少能記得自己的思想。在我還沒來得及安於某個靈感前,它通常就已經融化於更新的意念,而後者也同樣具有善變的特色,我總是必須努力將它保存起來,免得受到像火山熔岩般持續流動的思維的吞噬……。
我的腦子裡再度充滿了聲音。我覺得、它們像是一大群騷動不安的精靈陰魂不散,用我的腦細胞在彼此交談。我無法平靜地安頓它們全部,有些必須被過濾出來。我有大量多餘的智力,隨時需要解除負擔。每隔一段時間我就必須坐下來,用紙筆釋放我的思緒‥‥‥。
幾個小時之上則我醒來,確信自己想好了一句全世界最發人深省的格言。現在我不怎麼肯定了,不過至少這無瑕的金玉良言在我的筆記本裡有了一席之地。我相信它可以換來一頓較為可口的晚餐。如果我把它賣給某個已經有名的人,也許就會讓它進入下一版的《名人語錄》。
我終於決定了我未來的方向。我應該要繼續從事這件我不斷在進行著的事,但是從現在起,我將以此維生。我並不需要當個名人,這點在這一行是很重要的考量,而我還是可以家財萬貫。
當我翻閱著這本舊日記,心中覺得悲傷。上述文字寫就的時候,我才十九歲,日期是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日與十二日。瑪琍亞在幾天前離開,前往斯德哥爾摩,當時她已懷孕三、四個星期。接下來的幾年之間,我們見過幾次面,但是自從我最後一次見到她至今,二十六個年頭已經過去。我不知道她住在哪裡,甚至不曉得她是否仍在人間。
真希望她此刻能夠看見我。我得跳上一架一早起飛的班磯,離開這一切。時至今日,外在壓力已經增加到如內在壓力一般,因此形成了某種平衡狀態。現在我可以想得更清楚。如果我夠小心,或許我會有辦法在網子收線之前,在這裡活上幾個星期。
我很感激自己能安然離開書展。他們跟蹤我到了機場,但我很懷疑他們有能力發現我搭上哪一班飛機。我買了第一個從波隆納(Bologna)起飛班機的空位。「你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嗎?」我搖搖頭。「我只想要離開,」我說,「搭第一班飛機。」現在輪到她搖搖頭,然後她笑了。「沒有很多客人像你這樣,」她說,「但是未來會多得多,相信我。」然後,當我付過機票錢,「好好度個假!我相信這是你應得的……。」
只要她能夠知道。只要她能夠知道我應該得到什麼。
我的飛機起飛二十分鐘之後,有另一架飛機飛往法蘭克福。我不在上面。我確定他們會想像我是夾著尾巴逃回奧斯陸的家。但是如果你是夾著尾巴逃走,挑最近的路就未免太不聰明。
我在海岸邊的一家老旅館投宿。我坐在那裡凝視著海面。岸邊海胛上立著一座古老的摩爾式塔。我望著藍色船上的漁人們。有些還在海灣拉著網,其他人則是帶著他們當日的漁獲,朝防坡堤前進。
地板貼的是磁磚。寒氣經由腳底上懾全身。我穿了三雙襪子,但貼在冷冰冰的磁磚上,卻是毫無用處。情況再不快快改善,我就會把大大的雙人床上的床單捲起來,當成我的腳墊。
我會來到這裡是很偶然的。從波隆納起飛的首班飛機也很可能是前往倫敦或巴黎。但是,正當我一面寫著,我發現自己靠著的這張舊書桌,在很久以前的過去,另一個挪威人——他也等於是個被放逐的人——曾坐在這裡寫字,因此又覺得這真是太湊巧了。我停留的這個城鎮,是歐洲最早開始製紙的地方。眼前的谷底,舊紙廠的廢墟櫛比麟次,彷如串串珍珠。它們當然必須經過我的一一視察。但是依照規則,我必須留在旅館裡。我在這裡已經吃住全包。
此地的任何人大概都不可能聽過蜘蛛先生。這裡的一切都繞著觀光業和檸檬栽植打轉,所幸二者都還未達旺季。我看見有些觀光客在海裡划水,但是游泳季節還沒到來,檸檬也還需要幾個星期才會成熟。
我的房間裡有個電話,但我沒有朋友可以談心,自從瑪琍亞離去之後,就再也沒有了。不太有人會說我是個好朋友,或是個正直的人!但我確定至少有個舊識並不希望我死去。在《晚郵報》上有篇文章,他是這麼說的︰從此之後,一切都變了樣。我決定第二天大清早離開。在南向飛行的班機上,我有足夠的空暇可以回想。我是唯一徹底瞭解自己的行動的人。
我決定和盤托出。我寫作是為了了解自己,而且我應該要盡可能誠實地寫。這並不表示我很可靠。人在寫作關於自己一生的作品時!如果標榜的是可靠!那麼在他踏上這趟機關重重的航程之前,通常就已經翻船了。
我坐在這兒想著時,有個小人兒在房間裡踱著步。他只有一公尺高,但已經是個成人。這個小人兒身著炭灰色西服,腳蹬黑色漆皮鞋!頭上戴著一頂高高的綠氈帽,行走之際,手上揮舞著一支小小的綠色竹手杖。他不時用手杖指著我!這是示意我必須趕緊開始我的故事。
是這個戴著氈帽的小人兒敦促我坦承自己記憶所及的一切。
一旦我寫成我的回憶錄,當然就比較難殺了我。光是謠傳他們受人束縛,即便是最有膽識的人,勇氣也要被吸乾。我得確保這樣的謠言會傳揚開來。
有好幾十捲錄音帶安全的藏在銀行的保險箱裡——好,我說出來了——我不會說出地點,但我已經一切準備妥當。我在這些小錄音帶裡,收集了將近一百個聲音,所以光是這點,就足以昭告天下,有人有謀殺我的動機。有些人還公開威脅,全都存在錄音帶裡,從一號編到三十八號。我還設計了一個很巧妙的索引,可以輕鬆找到任何一個聲音。我很謹憤,有人甚至稱之為狡猾。我確信有關錄音帶的傳聞,已經讓我多活了一、二年。加上這些約略記下的事錄,這些小小的奇蹟就會有更高的價值。
我的意思並不是暗示說,我的自白,或是這些錄音帶就會是什麼安全行為的保證。我想像著我會去到南美或東方的某處。此刻我就覺得太平洋的某一座小島是個吸引人的好主意。不管怎樣,我是孤立的,我向來孤立。對我來說,在一座大城市裡感到孤立,是比隱居太平洋上的小島要悲慘得多。
我變得很有錢。我並不覺得意外。我很可能是有史以來第一個努力不懈於這類特殊行當的人,至少以規模來說是前所未見。市場無限廣大,而我總是有貨品供給。我並不是在進行非法交易,我甚至付了某個額度的稅。我的日子也過得很儉樸,因此現在如果必須補繳欠稅,我也可以補上一大筆。從我的客戶的觀點來看,這也不算是不合口法的買賣,只是不怎麼光采。
我明白從今天起,我會過得比大多數人都窮,因為我正在逃亡。但是如果可以交換,我也不會想要過著當老師的生活。我也不會想當個作家。我覺得很難倚賴一個實實在在的行業維生。
小人兒讓我覺得很緊張。唯一忘掉他的方法,就是繼續我的寫作。我將從我的記憶所及最早的時候寫起。
序幕
我的大腦翻騰著。隨時都有千百種新的點子冒出來。它們就是如此這般源源不絕。
程度上的控制思潮也許還有可能,但是要停止思想就未免強人所難。我的腦袋裡漲滿了點子,我無從解決它們,唯有新的想法將舊的驅逐出境。我無法把它們分開。
我很少能記得自己的思想。在我還沒來得及安於某個靈感前,它通常就已經融化於更新的意念,而後者也同樣具有善變的特色,我總是必須努力將它保存起來,免得受到像火山熔岩般持續流動的思維的吞噬……。
我的腦子裡再度充滿了聲音。我覺得、它們像是一大群騷動不安的精靈陰魂不散,用我的腦細胞在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