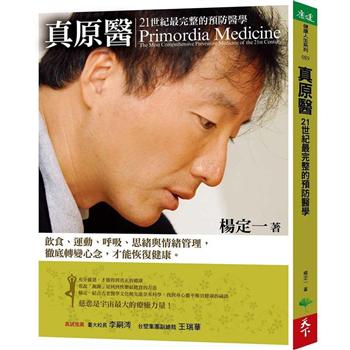永遠難忘人生的那一味──車前草湯
歷經四十年也不曾忘記的野外求生
在民國六十年代,年輕學子開始風行登山,當時許多大專院校紛紛設立登山社,一群又一群的年輕人,自己組隊攀登中央山脈的大山,由於那個時代的登山資訊甚少,也沒什麼好的登山器材,大都是學長當嚮導帶著學弟往深山走。結果民國六十年七月,清華大學登山社五人在奇萊山罹難,民國六十五年八月,陸軍官校畢業生登奇萊山六人罹難。年輕學子的山難事件頻傳,讓政府非常頭痛。
也因此,民國六十六年,當嚕啦啦第九期甄選來到第二階段時,時任中國青年服務社活動組組長的李正元,便將此階訓練定位為「野外求生」,並召集如今已故的知名野外求生專家馬賽教官等人上山,帶領嚕9見習學員進行一場沒有食物、沒有帳篷的野外求生訓練,讓他們去體驗及學習,如果在山中走失,該如何帶領隊員在山野中自我求生。這次的訓練真是刺激萬分,幾乎讓所有嚕9的夥伴終生難忘。
這是一個四天三夜的訓練。第一天,全體見習學員在傍晚集合,將近一百個登山背包一字排開,整齊地擺在中國青年服務社大廳地板上,李正元一聲令下,已經穿上制服的學長姊們便逐一翻搜出見習學員背包內的紙鈔、零錢、餅乾、糖果、泡麵……等,將這些所謂「本次用不到」、「不需要」的物品一一裝袋保管後,嚕9見習們便搭上客運,抱著不知目的為何的忐忑不安,朝黑夜的拉拉山前進。
用冰冷的晚餐填飽肚子後,午夜十二點的巴陵山莊,一群人帶著睡意在戶外廣場夜觀星象,然後草草就寢。有些人以為隔天就是上上課,順便認識大自然;還有些人想,最糟的情況大概就是像今晚這樣……
五個小時後,東方魚肚白,哨聲一響,大家整裝出發,展開第二天的訓練行程,邁步前往那一片黑黝黝的山林。由下巴陵一路到上巴陵,十公里的上坡山路,沿途必須撥開雜草、避開刺藤、還要小心螞蝗,一邊盯著前方夥伴的後腦勺、背包、鞋跟一步步往前走,一邊聽著主導野外求生課程的馬賽教官沿途講解野生植物。
「芭蕉蘭又稱老鷹窩,嫩葉可食;咬人狗有毒,碰到時會發癢,用刀片割其樹皮取其汁液,塗抹傷處即癒;牛皮菜可食;野蒿可食;鹿仔草嫩葉煮湯,喝湯退火……」吳英修細數當年所學的野外植物。
永遠忘不了滋味的車前草湯
此外,張淑芳迄今記得車前草、腎蕨和咬人貓;蘇秉源記得車前草和半夏;有趣的是,其他人也都記得車前草,為什麼呢?因為,當天接下來的訓練,他們就要開始採集晚餐要吃的野菜。面對一片全然不熟悉的山林,每一組都拚命找尋可以吃的、或看起來可以吃的植物,而由於李正元說車前草的味道像茼蒿,因此,沿途的車前草,不管老的、嫩的、長得像的,便都被這些嚕9見習們摘採一空。
「今晚在此紮營!」聽到這個命令時,大家都傻眼了。左邊是一片陡峭的神木林,右邊是小懸崖和溪流,沒有山莊、沒有山洞、沒有帳篷,怎麼紮營?沒有鍋具、沒有米、沒有肉,怎麼煮食?
當大家開始分工紮營與煮食時,更大的考驗來了,天突然下起大雨!
吳英修說,這是「以天為帳,大地為床……屋漏偏逢連夜雨」;萬瑜潔則有深刻的形容:「望著由山坡上傾注奔騰、滾滾急洩的水流,再看看一無所有的我們,我絕望地想著:『今夜我們要命喪於此了!啊!爸爸、媽媽、兄弟姊妹們,永別了!我真不該來參加這個可怕的拉拉山集訓。』
總之,大家手忙腳亂用砍來的竹子撐起登山雨衣,勉強搭起一個個避雨的小帳。只是,大雨將撿來的柴都淋濕了,生火非常困難。自製的「求生武器」派不上用場,無肉可食,每一組只好都煮了同一道菜——將採來的車前草加上薑片、鹽巴和口糧中的牛肉乾丟在鋼杯,煮成「車前草湯」。那味道令大家至今難忘,「很苦!」「哪裡像茼蒿?」
後來晚餐吃什麼呢?「楊志晟不知哪裡摘了一小把紅色野果,一人兩顆……」,大家拿來配上出發前發的營養口糧,「李大哥叮嚀兩包口糧只能吃一包,剩一包回來要檢查!」蘇秉源永遠記得,當晚他只吃了兩片口糧,其他都分給同伴,「反正那時不怕餓!」他說。「如果那時候有熊出來,必死!」蘇明綢指的是「熊必死」,因為,他們那時真是餓到可以吃下一頭熊!
當晚,同小隊就擠在避雨小帳內睡覺,地上是凹凹凸凸的碎石,旁邊是黑漆漆的陡坡,身體躺得直直地,不敢翻動,深怕一翻身就掉到斜坡下!
前所未有的刻苦經驗,磨練出一生的堅韌
第三天一早,迅速收拾,他們往福山前進。半途,李正元指著前方說:「有聽到水聲嗎?那就是我們的目的地!」
「以為那個水聲很近,結果翻了一座山才到!」蘇秉源只吃兩片口糧,腸子打了好幾個結,咬著牙、忍著飢餓,努力走著。受訓隊伍在一條小溪邊停下,大家放下背包以為要休息,心裡暗自開心時,李正元卻要大家開始演練野外急救。男生們只好開始四處尋找竹子和樹枝,砍一砍、綁一綁,先橫跨溪流搭設簡易竹橋,接著大家利用樹枝和衣服做成臨時擔架,將傷患扮演者包紮、做防護,搬上擔架,然後合力抬過溪流。
當晚,每組帶開尋找適合紮營的地點。紮營前,每個人必須製作自己的「捕食工具」或「防身武器」,張淑芳印象深刻地說,他們小隊每個人都身懷絕技:萬瑜潔用細長葉子編了一個漁網;楊志晟將他的童軍小刀綁在樹枝上;鄭偉彰用樹枝和鞋帶做了弓箭;張大春撿了一顆長長圓圓的石頭做了石槌;還有人用細細尖尖的石片做了石刀。眼見童軍和登山社出身的夥伴們一一完成任務,張淑芳正發愁自己什麼都不會的時候,不知誰遞來一把做好的武器讓她湊數。待大家都各有所獲後,全隊便擺出各種姿勢,讓喜愛攝影的夥伴為大家拍下各種紀念合照。
沒想到,當李正元開始檢查大家的「工具」與「武器」時,卻不斷搖頭,最後只有讚賞了楊志晟的童軍小刀,稱它是唯一派得上用場的。但是,想當然爾,就算有這些工具,依當時大家稚嫩的山野經驗,在溪流和叢林裡攪和半天,自然還是什麼都捕捉不到!
但他們依舊必須自行想辦法捕食各種可吃的東西,經過一整天飢餓與疲勞驅使,求生意志已達高點,獵食技巧大增。呂子厚擁有他人沒有的絕技,在溪流邊抓到好多田雞,為他們小隊煮了田雞湯;也有小隊撈到蝦子加菜的,至於配菜依舊是「車前草湯」。晚上夜宿在福山野地中,沒有搭避難小屋,枕著沒有打開的睡袋,靠在稜角分明大小石塊上,選一個剛好不會卡到石頭的角度,半坐半臥,肩捱著肩,仰望星空,一覺到天明。「那時又餓又累,沒力氣思考,也沒心思抱怨,只想著趕快休息!」「想說能活到明天早上醒來就好!」「望著背包裡那包唯一的口糧也不敢吃,說好要帶回去的!」。
前所未有的刻苦經驗,讓這群嚕啦啦第九期服務員們永生難忘,也磨練出他們的堅韌。蘇明綢很有方向感,對於四十年前的路程記憶猶新,也曾在幾年前找尋當時走過的區域,喚回受訓的記憶。張淑芳說,也許是這次的受訓,讓他們之後遇到的各種挫折與困難都成為小事。陳永寧回憶這一切,覺得也許是這次的訓練,讓她日後帶領營隊遇到困難時能夠冷靜且樂觀面對。大家一定都好奇,這四天三夜可比美探索頻道二十一天野外求生節目的真實生活,難道都沒有人半途放棄?蘇明綢揣摩當時大家的心情:「前不著村,後不著店,想半途放棄還要自己走回去!」
相信,在當時讓每個人繼續走下去的,絕不是因為害怕黑漆漆的回頭路,而是在體力快要耗盡、信心快要用完、淚水快要奪眶時,大家互相幫助、打氣,以及一路慢慢熟悉、共同面對挑戰、合力解決問題所建立起的革命情感!
所有受訓結束後,在終點處,李正元為該次九期見習成員,一位一位地掛上通過野外求生訓練的徽章。這枚徽章象徵著嚕啦啦不怕苦、不怕難的服務員精神,許多嚕9夥伴至今都還保留著,當作他們這一生對野外求生訓練的回憶與紀念。
史上參加人數最低的營隊──鱷魚登山隊
在《那一年當我們嚕在一起》企劃成型,大家努力向一至十期的「老嚕」們邀稿時,大部分學長姊都十分害羞,大多謙稱自己文筆不好、不敢提筆,但,嚕4高玉立義不容辭地跳出,調侃說自己是來「自投羅網」的;因為,她正好曾經寫過一篇與同期在山中服務的美好往日,並刊登於中國時報浮世繪;因此,本篇經高玉立授權、直接轉載,原題名為〈鱷魚登山隊〉,全文如下:
民國六十二年的寒假,加入中國青年服務社嚕啦啦的我,被分派到當年救國團最熱門的賞雪景點──合歡山的「陸軍寒訓中心」當駐站服務員,一起駐站的還有兩個憨厚的登山好手──楊佳、顏世長。和兩個不相識的小男生分在一起,一想到要這樣在山上待一個月,就覺得日子很難熬。
駐站的工作是很制式的,每天一早起來,先叫醒前一天到站的學員,整理內務、梳洗用餐後,就一路充內行地邊介紹合歡山的各個景點,邊把他們往昆陽方向送。通常是到了合歡山和昆陽的中間,我們就會在熱情的「珍重再見、後會有期」聲中折返,回到「合歡山莊」和山莊的駐站服務員一起等著吃午餐、計劃晚會的節目。
下午三點左右,再往大禹嶺方向去迎接下一梯次的學員,協助分配床位、寢具、盥洗用具,用過晚餐後,主持個氣氛好又有趣的晚會,一天就這樣過去了!
過了幾天這樣的日子之後,三個人越來越熟,花樣也就越來越多。山上很冷,肚子餓得快,可是在此,除了三餐,是沒有點心宵夜的。當兩個男生聽說我會做蛋糕,就千方百計地和伙頭班長套交情,請班長支援做蛋糕的材料。晚會後,把學員們哄睡,我們就開始分工合作,努力把雞蛋打到發泡,加進麵粉、糖和水,再小心翼翼地把麵糊放入用兩個新臉盆扣起來的克難烤箱中,架在暖爐上,就這樣烤起蛋糕來了!隨著香味四溢,學員一個個來敲門,抱怨睡不著、肚子餓,蛋糕就在一群人的熱切期待下出爐了!沒有發粉,所以發得不夠大,每個人也只吃到一小口,但是那確實是「合歡山」上最有創意、最有滋味的蛋糕了!
吃過蛋糕的學員,下山後多半會寄來各式各樣的零嘴,從此上午送走隊伍後,我們不再直接回「合歡山莊」,而是每天帶著零嘴,攀登附近的小山。有一回爬上「合歡山莊」對面的山頂,發現了那座山的三角點,旁邊放了個玻璃瓶,打開來一看,裡面有好多紙條,上面都是寫著:「某某登山隊於某年某月某日登頂成功」,這才知道我們誤打誤撞,居然登上了合歡山的東峰。看著被皚皚白雪覆蓋的壯闊山景,眺望著傳說中的神祕奇萊山,覺得似乎也該留張字條為證,我們該叫什麼隊呢?想想每天不停地吃,就取「餓」的諧音,叫「鱷魚登山隊」吧!
下山之後,我們三人成了莫逆之交,每逢假日就相約去爬山,從不知名的小山到大霸尖山,直到他二人去當兵,我出國唸書。過了幾年,顏世長移民美國,楊佳做了報社的攝影記者,我當了老師,相聚的機會越來越少。
去年剛放寒假時,合歡山下了大雪,看著電視上熟悉的銀白景色,忍不住帶著孩子奔向久違了的合歡山。只見道路旁和山坡上撲了一層薄薄的白雪,從未見過雪的兩兄弟,興奮地又是打雪仗又是堆雪人,但比起當年積雪盈尺的冬景,實在是不夠看。「合歡山莊」和「松雪樓」都被木板封住了,我悵然地站在門口,依稀聽到當年由門縫中傳出的歡笑聲。「松雪樓」前路旁的大石頭仍在,上面彷彿仍印著我們由「合歡東峰」滑下來時濕漉漉的牛仔褲的水漬,望著陡峭的山壁,我卻沒有再攀登的氣魄,只想著再次見面時,要告訴他們「合歡山莊」和「松雪樓」被封住了!
沒想到再次見面是在台北的第二殯儀館,楊佳和他的家人搭上了那架由峇里島起飛的華航班機,看著靈堂前的相片,我不禁淚如雨下。好伙伴,我還沒告訴你合歡山變了,還沒告訴你我還記得那個合歡山的蛋糕呢!更還沒告訴你年輕的歲月有你們相伴,讓我走得有多麼穩健、踏實又快樂呢!
| FindBook |
有 12 項符合
那些年,當我們嚕在一起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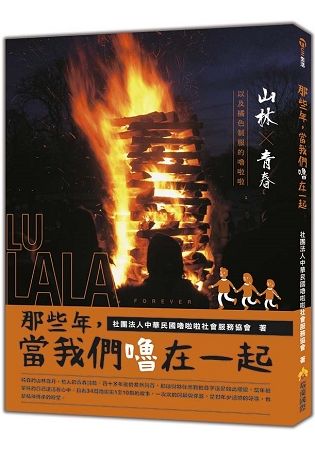 |
那些年,當我們嚕在一起 作者: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嚕啦啦社會服務協會 出版社:瑞蘭國際 出版日期:2019-04-22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那些年,當我們嚕在一起
有煩惱?有愛情?有對未來的憧憬?
在四十年前的台灣山野裡,
有一群服務人群、跟著風奔跑的孩子……
他們的青春,在能迴盪、放大歡笑的谷地裡度過。
他們是──嚕啦啦!
每個人都有專屬於自己的青春可以回顧,那些回憶或許各不相同,但卻都有一些奇妙、甜美的共通點,那就是那段時光有著在人生任何階段都不會有的躁動,那樣的躁動具現在少男少女的閃亮眼睛裡、對世界的好奇裡、對未來的期盼裡。
那樣的躁動驅使了每個人的青春故事,當我們驀然回首時,才發現那樣的故事同時成就了之後的我們。且看有山林之子之稱的嚕啦啦們,在他們的青春裡,寫下了什麼能夠回味一生的動人故事!
■什麼是嚕啦啦?誰是嚕啦啦?
嚕啦啦,或稱LuLaLa,是中國青年救國團轄下的「中國青年服務社假期活動服務員」的簡稱。「嚕啦啦」剛開始只是服務員在山中相遇時所唱的〈國際友誼歌〉的歌詞,幾經傳唱後,便逐漸成為團體的代稱。
嚕啦啦的成員們在學期間皆必須通過服務社嚴謹的訓練,才能穿上專屬的橘色制服。每一年,嚕啦啦都會招募新血,從民國58年創立至今,已經有50屆、超過千位的嚕啦啦。
■他們在做什麼?
假期活動服務員,顧名思義就是為度假的人服務。嚕啦啦團體創立當時,台灣的山林之美剛為人所知,但在缺乏規劃、設備的情況下,登山活動常常發生許多意外。為了讓山林活動更加順利安全,中國青年服務社便開始招募對山林活動、社會服務有興趣的青年,在通過各式專業訓練後,於暑假、寒假在山林中,為報名營隊的人服務。包含以領隊的身分帶領學員走過山路、策畫營火晚會、準備餐食、安排住宿……等。
■屬於嚕啦啦的這本書,可以讀到什麼呢?
本書的內容為民國六○年代初期嚕啦啦的青春冒險故事。他們在今日耳熟能能詳的觀光勝地:合歡山、霧社、溪頭、日月潭、清境農場,還未有大量觀光人潮前,便在那裡進行一連串的訓練。也許當時的他們並不知道,那些嚴苛的訓練培養了他們刻苦耐勞的精神、面對困難不放棄的勇氣,以及不管歷時多久依舊閃耀的友誼。
四十年後的今日,以屆退休之齡的他們,直到聚在一起話當年才發現,那些在山林裡得到的回憶、技能及態度,深深影響了他們的一生。儘管當年留下回憶的場景早已物是人非、山林不再如此神祕、危險,但仍和他們那個因充滿熱血、熱心而純真的自己一起,永遠珍藏在心裡。
那些令人難忘的日子有:
‧酸甜
「她好會唱歌,我們都唱得沒有她好,後來我發現她不會唱蘭花草,我好開心,我就想著,終於有一首妳不會唱的了!」
──〈再見蘭花草〉
人命關天,加上本性使然,周明政二話不說,當下沿著山崖連跑帶滑趕到水邊,一把拉起落水的同梯學員,這一拉,也拉出與嚕啦啦的一世情緣。
──〈小心星探就在你身邊〉
‧驚險
直到晚上洗澡時,當水流滑過身軀,竟是陣陣刺痛,這才發現,雙手雙臂,處處都是芒草割過的傷痕,其中甚至還有一隻不知名蠕蟲在手肉裡鑽著……
──〈你帶過最特殊的團是?〉
由於這三件緊急狀況幾乎在同一個時間發生,一時之間,忙碌、緊張、驚險……籠罩整個合歡山區……
──〈一日三胡──從一場流程完整的嚕家聚會說起〉
最糟的是,雙腳上的登山鞋像千斤頂般拖著我往下沈,我想腳踏溪底,卻驚覺溪水已淹至頭頂,口鼻也已無法呼吸。
──〈我們心中都有一條「巨流河」〉
‧展望
這些形式上的過程她其實已經想不起來,細節也記不得了,重點是,她在二十歲那年和嚕啦啦一起過生日,在有著滿山滿谷螢火蟲的溪頭森林裡和同期談理想,並自此種下快樂的種子,那淡淡的、雋永的回憶,她一生難忘!
──〈生日快樂〉
於是,在三千公尺的高山上,一位年方二十歲的年輕女孩,頓時有了七十歲的心思,雖是初出茅廬,卻有種歷盡滄桑的領悟……
──〈我們都曾經是珍妮〉
‧遺憾
「松雪樓」前路旁的大石頭仍在,上面彷彿仍印著我們由「合歡東峰」滑下來時濕漉漉的牛仔褲的水漬,望著陡峭的山壁,我卻沒有再攀登的氣魄,只想著再次見面時,要告訴他們「合歡山莊」和「松雪樓」被封住了!
──〈史上參加人數最低的營隊──鱷魚登山隊〉
「就在這些看似短暫的山林活動裡,我學習到了『知己納人』的崇高人生觀,愛鄉更也愛上台灣深山裡的森林與土地,既曾徜徉於大自然裡並也享受與人互動的美感……」
──〈媽媽跪求:你別再上山了!〉
‧淚水
是晚,大夥兒閒聊,大家突然同時有一陣奇異感,感覺邱惠森就在他們身邊,彷彿告訴著他們,這件事已經事過境遷,希望大家放下!
──〈學弟妹們的守護者〉
每個人的青春都有一些故事,每次回味,都會為那些故事增添新的風味。歷經四十年還留存在腦中的回憶故事,反覆醞釀後,會是什麼樣的味道呢?年輕的我們,讀完又能嘗到什麼樣的滋味呢?不管你是不是嚕啦啦,都邀請你來品嘗、啜飲,這杯在山林裡釀成的陳年好酒!
作者簡介: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嚕啦啦社會服務協會
嚕啦啦,或稱LuLaLa,是中國青年救國團轄下的「中國青年服務社假期活動服務員」的簡稱。踏出校園的嚕啦啦們,為了凝聚終身服務社會的共識,於民國78年成立了「嚕啦啦聯誼會」,為這群熱心人投入終身志工的淵源。
民國86年11月15日,嚕啦啦聯誼會轉型為正式法人團體。民國104年11月4日取得社團法人資格,正式更名為「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嚕啦啦社會服務協會」(簡稱「嚕協會」)。
嚕啦啦所代表的已不只是一個團體、一種人群的集合,嚕啦啦更代表了一種精神、一種態度、一種文化與一種生活的方式,回顧從前、立足現在、放眼未來,山林之子依舊執情,從現在直到永遠。
嚕協會除聯誼活動除了持續培養革命情感外,更積極運用嚕家人在各行各業的人脈資源,結合志同道合的朋友,扮演社會企業的角色,徜徉在這片「快樂傻瓜」的天空,不論在原住民部落、921災區、安老院、教養院、育幼院,都有著嚕家人的足跡。
延續嚕啦啦「熱心人」取之社會,回饋社會的精神,自民國103年於圓山花博廣場舉辦,「愛在偏鄉、夢想起飛」公益活動,持續發揮嚕啦啦精神。
章節試閱
永遠難忘人生的那一味──車前草湯
歷經四十年也不曾忘記的野外求生
在民國六十年代,年輕學子開始風行登山,當時許多大專院校紛紛設立登山社,一群又一群的年輕人,自己組隊攀登中央山脈的大山,由於那個時代的登山資訊甚少,也沒什麼好的登山器材,大都是學長當嚮導帶著學弟往深山走。結果民國六十年七月,清華大學登山社五人在奇萊山罹難,民國六十五年八月,陸軍官校畢業生登奇萊山六人罹難。年輕學子的山難事件頻傳,讓政府非常頭痛。
也因此,民國六十六年,當嚕啦啦第九期甄選來到第二階段時,時任中國青年服務社活動組組長的李...
歷經四十年也不曾忘記的野外求生
在民國六十年代,年輕學子開始風行登山,當時許多大專院校紛紛設立登山社,一群又一群的年輕人,自己組隊攀登中央山脈的大山,由於那個時代的登山資訊甚少,也沒什麼好的登山器材,大都是學長當嚮導帶著學弟往深山走。結果民國六十年七月,清華大學登山社五人在奇萊山罹難,民國六十五年八月,陸軍官校畢業生登奇萊山六人罹難。年輕學子的山難事件頻傳,讓政府非常頭痛。
也因此,民國六十六年,當嚕啦啦第九期甄選來到第二階段時,時任中國青年服務社活動組組長的李...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點滴,回憶;累積,記憶;鑄下,標記
書本記錄著點滴的回憶,積累著絲絲的記憶,回顧每一份曾經的美好,訴諸每一段動人的故事,並為過往鑄下永恆的標記。
嚕啦啦(Lulala),是中國青年救國團轄下的中國青年服務社假期活動服務員的簡稱,是一群具備充分熱血、高度熱忱、十足熱情的永續世代,也是群自許快樂傻瓜的服務團隊。嚕啦啦以積極工作的態度、真誠如一的信念、發乎至誠的行動,在活動中學習,在歡笑中反省,在助人中研究,透過溫暖笑意、親切問候,展現對社會盡責的精神,期許能夠做到「凡經我手,必使之更真、更善、更美」。
嚕...
書本記錄著點滴的回憶,積累著絲絲的記憶,回顧每一份曾經的美好,訴諸每一段動人的故事,並為過往鑄下永恆的標記。
嚕啦啦(Lulala),是中國青年救國團轄下的中國青年服務社假期活動服務員的簡稱,是一群具備充分熱血、高度熱忱、十足熱情的永續世代,也是群自許快樂傻瓜的服務團隊。嚕啦啦以積極工作的態度、真誠如一的信念、發乎至誠的行動,在活動中學習,在歡笑中反省,在助人中研究,透過溫暖笑意、親切問候,展現對社會盡責的精神,期許能夠做到「凡經我手,必使之更真、更善、更美」。
嚕...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理事長序:點滴,回憶;累積,記憶;鑄下,標記
緣起:我們只有青春不會老
不滅:嚕啦啦榮譽責任的橘色制服
看風兒起
你帶過最特殊的團是?
再見蘭花草
史上參加人數最低的營隊──鱷魚登山隊
媽媽跪求:你別再上山了!
背掛不求人的師奶殺手
看雲兒湧
小心星探就在你身邊
一日三胡──從一場流程完整的嚕家聚會說起
從水平線到海拔二千公尺
你也是啦啦隊嗎?
生日快樂
看風起雲湧嚕啦啦
我們是怎麼嚕過來的?
我們心中都有一條「巨流河」
我們都曾經是珍妮
我的徽章我的夢:源自英國的熊章
被撕毀的學員地址
...
緣起:我們只有青春不會老
不滅:嚕啦啦榮譽責任的橘色制服
看風兒起
你帶過最特殊的團是?
再見蘭花草
史上參加人數最低的營隊──鱷魚登山隊
媽媽跪求:你別再上山了!
背掛不求人的師奶殺手
看雲兒湧
小心星探就在你身邊
一日三胡──從一場流程完整的嚕家聚會說起
從水平線到海拔二千公尺
你也是啦啦隊嗎?
生日快樂
看風起雲湧嚕啦啦
我們是怎麼嚕過來的?
我們心中都有一條「巨流河」
我們都曾經是珍妮
我的徽章我的夢:源自英國的熊章
被撕毀的學員地址
...
顯示全部內容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