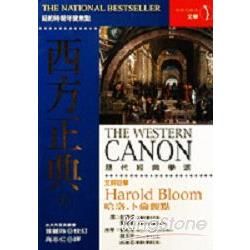期待多元的世界文學經典論集
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 彭鏡禧
吾人生也有涯,而學也無涯。想要博覽古今浩瀚的典籍,總得有所挑選檢擇吧?《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1994)一書是美國著名文學教授兼批評家哈洛.卜倫(HarOld BlOOm)針對這個問題而提出的答案。
卜倫曾任哈佛大學講座教授,現任耶魯大學及紐約大學講座教授、獲得麥克阿瑟獎,又是美國學術院院士,學術聲望崇隆,影饗力極大。一九五0年代「新批評」理論鼎盛時期,卜倫在該學派的大本營耶魯大學接受洗禮。但是這位曾經以「影響的焦慮」(the anxiety Of iMhe)解釋文壇遞嬗原理的大師,本人似乎也難免同樣的焦慮,經常跟他的師長唱反調:在英國浪漫文學方面,他高舉雪萊便是一例。卜倫的文學理論及批評鮮少跟著潮流走:他對文學的評價一貫以知性與美學為標準。這本《西方正典》也不例外。
正典者,歷代「公認」的經典著作是也。這原本似乎天經地義的觀念,近年受到學術界嚴格的質疑和批判。因為經典的形成,有太多政治、種族、性別、權力等因素介入。反對者認為,所謂西方的經典只能代表歷史上白種歐洲男人的偏見:所謂美學,不過是特定階層人士的喜好。然而,對傳統的挑戰,其實正說明了傳統的根深蒂固,以及它在文化演進發展中的關鍵地位。想要真正了解一種文化,認識其重要思想或人文特色,閱讀他們的經典著作、分辨其背景脈絡,仍舊是不二法門。
卜倫這本將近六百頁(原文)的大作力排眾議,堅持經典的價值。他甚至點名批判多元文化論者和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拉岡學派、新歷史主義、解構主義、符號學派等六種學說,統稱之為「憎恨學派」,認為它們會置文學於絕境。本書首篇題為《正典輓歌》,末篇題為《最後的輓歌》,足見上倫深知自己的不符時尚、違反潮流,卻也同時顯示出他知其不可而為的勇氣,展現了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學術良知。
正典的選擇是一大難題。西洋文學從古代希臘算起,已有兩千多年歷史。其間希臘文、拉丁文曾經是歐洲學術的共同的語言:文藝復興之後國別文學興起,作家開始大量使用本國語文創作,各國各代都有輝煌的成就,重要作家與作品不知凡幾。卜倫從其中選擇了二十六家。撇開難以避免的個人偏見不提,這本《西方正典》作家作品的挑選,顯然深受語言的影響。其中英語作家佔了十二席;非以英文寫作的作家,必須先有好的英文翻譯,才有可能對英語世界產生影響。令人費解的是希臘羅馬西方文化文學的源頭居然沒有代表;弗洛依德搖身一變而為文學大師也頗出人意表。
這本書旗幟鮮明,出版以來貶褒不一。褒揚者讚嘆卜倫的勇氣與博識之餘,也有人指出,它的出現更加凸顯提倡西方以外文學經典的必要,西方人固然應該了解他自己的文學傳統,也許更應該祛除自大與無知,進而了解世界上其他的重要傳統。而這也正是本書翻譯成中文的重大意義,《西方正典》是一塊很好的敲門磚,可以讓我們透過經典作品的討論,一窺西方文學堂奧。雖然跟多半的書籍一樣,這本書也是「一人之見﹂,但卜倫的意見絕對值得重視,值得用心思考。
閱讀這本書,也使我們反思,大量的中國文學經典,是否該有人來整理出類似的導讀或評論?其他的文學傳統,近如日本、韓國,稍遠如印度、伊斯蘭,我們有沒有能力,有沒有心思,認真研究、介紹?還是說,我們以翻譯西方為滿足?(而就連西方,我們翻譯的質與量也還遠遠不及理想!)僅僅列出五十大或一百大書目是不夠的:我們要有詳盡的評論。選材的公平反而不必太在意,因為絕無可能盡如人意。
希望《西方正典》的中譯本,不但可以引起中文讀者對西洋文學傳統的興趣,也可以加速我們學術界對自己,以及對其他文學傳統的研究與反省。然則志仁學弟翻譯這本學術巨著的艱辛:就有了最大的報償了。
民國八十七年七月五日於台灣大學外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