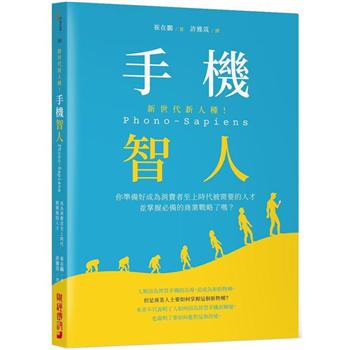《希臘羅馬名人傳》原名「對比的傳記」(Parallel Lives),作者Plutarch普魯塔克為羅馬時代的希臘著名傳記作家、哲學家,其作品在文藝復興時期至為重要。全書共五十個篇章,除四篇單人傳記,另四十六篇均各包含一個希臘人物和一個羅馬人物的傳記,記後一比較文,文中將二人顯著之特點加以對比。作者著重於人物道德質地,其次才是他對於當代或後世的影響力,此為本書一大特色。這部作品不僅是西洋文學的寶貴資料,更由於其所包含的豐富學問、優美文學性質和嚴正的人生哲學,因此二千多年來,一直被視為必讀之文學典籍。
本書特色
1.《希臘羅馬名人傳》作者Plutarch普魯塔克為羅馬時代的希臘著名傳記作家、哲學家,其作品在文藝復興時期至為重要。
2.這部作品不僅是西洋文學的寶貴資料,更由於其所包含的豐富學問、優美文學性質和嚴正的人生哲學,因此二千多年來,一直被視為必讀之文學典籍。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希臘羅馬名人傳(上)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70 |
人物群像 |
$ 270 |
世界人物傳記 |
$ 270 |
中文書 |
$ 270 |
歷史 |
$ 270 |
社會人文 |
$ 270 |
歷史人物 |
$ 270 |
Books |
$ 270 |
Others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希臘羅馬名人傳(上)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Plutarch(普魯塔克)
本書作者Plutarch普魯塔克(西元46-120年),羅馬時代的希臘著名傳記作家、哲學家,其作品在文藝復興時期大受歡迎,法國哲學家蒙田對他推崇備至,莎士比亞也不少劇作取材於他的相關記載。普魯塔克以《希臘羅馬名人傳》一書留名後世。
譯者簡介
吳奚真(1917~1996)
瀋陽市人。北平中國大學畢業後赴英國倫敦大學做研究。曾任雜誌主編、國立編譯館編審、大學教授、瀋陽市立圖書館館長。來台後任臺灣師範大學教授,為翻譯學界推崇為翻譯教父。 1992年榮獲國家文藝基金會翻譯獎的傑出譯作獎,譯著有:《孤軍流亡記》、《人類的故事》、《教育心理學》、《斑衣吹笛人》、《希臘羅馬名人傳》等,並主編《牛津高級英漢雙解字典》。
Plutarch(普魯塔克)
本書作者Plutarch普魯塔克(西元46-120年),羅馬時代的希臘著名傳記作家、哲學家,其作品在文藝復興時期大受歡迎,法國哲學家蒙田對他推崇備至,莎士比亞也不少劇作取材於他的相關記載。普魯塔克以《希臘羅馬名人傳》一書留名後世。
譯者簡介
吳奚真(1917~1996)
瀋陽市人。北平中國大學畢業後赴英國倫敦大學做研究。曾任雜誌主編、國立編譯館編審、大學教授、瀋陽市立圖書館館長。來台後任臺灣師範大學教授,為翻譯學界推崇為翻譯教父。 1992年榮獲國家文藝基金會翻譯獎的傑出譯作獎,譯著有:《孤軍流亡記》、《人類的故事》、《教育心理學》、《斑衣吹笛人》、《希臘羅馬名人傳》等,並主編《牛津高級英漢雙解字典》。
序
譯序
蓋拉德(Albert Guerardya)說:「一部古典作品(Classic)之所以爲古典作品,並非因爲它是在很久以前寫成的,而是因爲時至今日,它仍然新鮮如昔。」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就是這樣的一部歷百世而常新的作品。
關於普魯塔克的生平,我們所知不詳。連他的生卒時期,我們也只知道一個約計的年代(45?─120?A.D.)。他世居希臘比奧細亞(Boeotia)的一個小城,名字叫做凱洛尼亞(Chaeronea)。在一篇討論作家居住大城市之利益的文章裏面,他曾經說過這樣的話:「至於我自己,我是住在一個小城裏面,而且我願意住在那裏,因爲我一搬走,那個城市豈不將變得更小了。」他在雅典受教於一個名叫亞蒙尼亞斯(Ammonius)的哲學家。他去過埃及。在公元九十年之前,他爲了執行公務而在意大利停留相當的時期,並在那裏講學,很受注意。他曾擔任本城的執政官,和阿波羅神殿的祭司。他至少有五個子女,其中有兩個兒子長大成人;那兩個兒子之中的一個,名叫藍普里亞斯(Lamprias。後來也成爲一個哲學家,曾爲他的作品(包括現存的和已經散失的)編製一個目錄。
作爲一個哲學家,普魯塔克可以說是一個折衷派。他的思想線索,來自許多不同的淵源。他從柏拉圖的學院派習得了謙遜,從亞理斯多德的消遙學派(Peripatetics)習得了自然科學和邏輯,從斯多亞學派(Stoics)習得了堅忍,從伊匹鳩魯(Epicurus)學派習得了一種合理的享樂,從畢達格拉斯(Pythogoras)學派習得了對於一切生物都持著親善態度。換句話說,他似乎是一個獨立的思想家,並不依附某一門派。
普魯塔克的名聲,主要是建立在「希臘羅馬名人傳」之上。除了這部傳記之外,他的其餘作品的總名爲Opera Moralia,其中包括六十篇論文。我現在舉出其中幾篇論文的題目爲例,就可以窺知作者興趣的範圍是如何的廣泛:「論子女的教育」,「論機會」,「論迷信」,「論命運」,「論女人的美德」,「如何區別奉承者和朋友」,「論蘇格拉底的天才」,「論傾聽的正當方式」,「論月輪之面」(On the Face of the Moon's Disk),「陸上動物與海上動物何者更爲聰明」,「水與火何者更爲有用」,「論羅馬人的命運」,「雅典人所賴以馳名者,是戰爭?還是智慧?」
從歷史的觀點看來,普魯塔克所寫的傳記在某些方面是不夠確實的,因爲他對於數字有些馬忽,他所根據的資料未必盡屬可信,他的敘述有時也不免有些錯誤或前後矛盾之處。但是他對於傳記的寫作,卻懷有另外一種目的。他對於那些偉大人物的主要興趣,是去發現他們的道德性質。關於這一點,克拉夫(Arthur Hugh Clough)的下面這段話做了一個很好的說明:「在閱讀普魯塔克的時候,我們必須記住下列各點。他是一個道德家,而不是一個歷史家。他的興趣比較少在於政治和帝國的更迭,而更多在於人的品性、個人事蹟、和行爲的動機;被完成並且受到酬報的職責;受到懲戒的倨傲,獲得矯正的輕率的憤怒;在現實世界(the visible world)獲得成功、或者在靈冥世界(the invisible world)尋求憑藉的仁愛、公正、和慷慨。在寫作傳記的時候,他一直都在念念不忘亞理斯多德的道德學和柏拉圖的學說,那些東西構成了他那個時代的有教養的人們的宗教。 」
在亞歷山大傳的第一段裏,普魯塔克曾就他爲亞歷山大和凱撒的傳記選取材料的原則加以說明:「大家不要忘記,我現在所撰著的並非歷史,而是傳記。從那些最輝煌的事蹟之中,我們並不一定能夠極其淸晰地看出人們的美德或惡德;有時候,一件不太重要的事情,一句笑話,或者片言短語,會比最著名的圍城,最偉大的軍備,和最慘烈的戰爭更能使我們瞭解人們的性格和意向。因此,肖像畫家在作畫的時候。特別用心描繪最能表現性格的面部輪廓和眼神,而對於身體的其他部分則不必多加注意,同樣地,請讀者們也容許我對於人們的靈魂的跡象和徵兆多加註意,藉著這些來描寫他們的生平,而把他們的偉大事功和戰蹟留待其他作家們去敘述。」這是寫作傳記的一個正確的原則,也是必須具有大匠的技巧才能實行的原則。因爲「描繪人們的靈魂的跡象和徵兆」,寶在比逐一敘述一個人生平的事蹟,更爲困難得多。普魯塔克所提示的這種原則,一直被後世的傳記作家奉爲圭臬。
「希臘羅馬名人傳」原名「對比的傳記」(希臘文爲Bioi Paralleloi;英文爲Parallel Lives),分爲若干「卷」(Books),每卷包含一個希臘人物和一個羅馬人物的傳記,後面附有一篇「比較」,把兩個人的顯著特點加以對比。普魯塔克所採取的步驟,顯然是先來評斷人物們的道德本質,再來衡量他們所發生的影響,最後把他們的長處和短處,成功和失敗,分別加以比較。可惜的是,這些傳記後來佚失了若干部分;而作者原來的計劃也有若干遺略,顯然是由於他並沒有全部完成這部傳記的寫作工作。現在所留下來的共有五十篇傳記,其中有四十六篇是排比成對的,四篇是單人的。在排比成對的四十六篇之中,有八篇是沒有「比較」的。不過,就這部作品的現有的形貌來說,它迄今仍被認爲是一部只能做爲模倣對象,而不能侈望加以改善的完美傳記作品。這部作品不僅是西洋文學的寶貴資料之一,而且由於其中所包含的豐富的學問、優美的文學性質、和嚴正的人生哲學,也一直被列爲愛好文學者的必讀之書。
「希臘羅馬名人傳」的英文譯本很多,其中比較重要的幾種如下:
(一)Sir Thomas North譯本,刊於一五七五年。
(二)John Dryden譯本,刊於一六八三年。
(三)John and William Langhorne譯本,刊於一七七○年。
(四)Bernadotte Perrin譯本,爲希臘文與英文對照本,刊於一九一六年。
在這幾種譯本之中,最著名的當推諾斯(North)和朱艾敦(Dryden)的兩種譯本。諾斯的譯本,也就是莎士比亞所使用的譯本,並非自希臘文直接譯出,而是從亞繆(Jacques Amyot)的法文譯本(一五五九年)譯出的。不過,如桑普孫(George Sampson)所說的,「這個譯本﹝指諾斯的譯本﹞已經不是普魯塔克,而是利用普魯塔克的題材寫成的一部新的傑作。諾斯的普魯塔克距離亞繆法文譯本之遙遠,正像亞繆的法文譯本遠非普魯塔克希臘文原著的本來面目一樣。」但是,諾斯的伊利莎白式的散文,瑰麗奇特,本身成爲上好的文章。
譯者所採用的,是朱艾敦的譯本。採用這個譯本的原因,不僅因爲它是譯者在臺北所能找到的一種最佳的譯本(對於本書的譯述工作,有關方面規定的期限不長,所以來不及向國外選購書籍),也因爲這個譯本的文字和句法比較現代化,而又保持著原著的濃厚的學術的和文學的氣息。這個譯本雖然名爲朱艾敦譯本,實際上卻是出自好幾個人的手筆,所以文筆並不十分一致。譯者所根據的,是克拉夫的一八六四年的修訂本。Everyman's Library和Modern Library裏面,都用這個版本。朱艾敦是十七世紀的英國詩人、批評家、和戲劇家,英文裏面的biography(傳記)一字,就是由他在「希臘羅馬名人傳」的「緒言」裏面首先創用的。英譯本原文的句法有時很冗長而繁複,譯者盡力保存其文體上的風格。在翻譯的時候,譯者並且參考一部殘缺的Perrin譯本,和Langhorne譯本的一個選本,這是我目前所能得到的僅有的兩種其他譯本。有少數費解的地方,我採用了Perrin的說法,因爲Perrin譯本是希臘文和英文對照的,應該比較切合原文:這類情形中的比較重要之處,譯者都在註解中說明。
朱艾敦英譯本原書共載傳記五十篇(如全部譯成中文,約有一百四十萬字),本書只選譯了五篇(約二十萬字),每篇都是完整的翻譯。原書有克拉夫的長序一篇(近二萬字),在一個比較大規模的譯本裏面,那篇序當然是必不可缺的,但是在目前這個小型的譯本裏面,譯者只把那篇長序做爲這篇「譯序」的主要參考資料之一。
因爲參考書的缺乏,和時間的限制,譯文的註解做得不夠周詳,這是譯者引爲歉憾的事情。其他方面的疏誤,當亦不免,希望讀者不吝指正,我想將來在適當的時機,再做一些增補工作。
本書是由譯者受國立編譯館的委託而譯出的。王館長鳳喈很重視這部書,在這五篇譯稿完成付梓之後,王館長又設法克服一些物質條件上的困離,計劃繼續出版一冊。現在譯者已經接受王館長的囑託,即行著手將這部「希臘羅馬名人傳」再選譯二十萬字左右,作爲本書的下冊出版。
本書譯稿承梁寶秋先生在他本身的著述工作非常繁忙之中,惠予校訂,譯者深爲感謝。
蓋拉德(Albert Guerardya)說:「一部古典作品(Classic)之所以爲古典作品,並非因爲它是在很久以前寫成的,而是因爲時至今日,它仍然新鮮如昔。」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就是這樣的一部歷百世而常新的作品。
關於普魯塔克的生平,我們所知不詳。連他的生卒時期,我們也只知道一個約計的年代(45?─120?A.D.)。他世居希臘比奧細亞(Boeotia)的一個小城,名字叫做凱洛尼亞(Chaeronea)。在一篇討論作家居住大城市之利益的文章裏面,他曾經說過這樣的話:「至於我自己,我是住在一個小城裏面,而且我願意住在那裏,因爲我一搬走,那個城市豈不將變得更小了。」他在雅典受教於一個名叫亞蒙尼亞斯(Ammonius)的哲學家。他去過埃及。在公元九十年之前,他爲了執行公務而在意大利停留相當的時期,並在那裏講學,很受注意。他曾擔任本城的執政官,和阿波羅神殿的祭司。他至少有五個子女,其中有兩個兒子長大成人;那兩個兒子之中的一個,名叫藍普里亞斯(Lamprias。後來也成爲一個哲學家,曾爲他的作品(包括現存的和已經散失的)編製一個目錄。
作爲一個哲學家,普魯塔克可以說是一個折衷派。他的思想線索,來自許多不同的淵源。他從柏拉圖的學院派習得了謙遜,從亞理斯多德的消遙學派(Peripatetics)習得了自然科學和邏輯,從斯多亞學派(Stoics)習得了堅忍,從伊匹鳩魯(Epicurus)學派習得了一種合理的享樂,從畢達格拉斯(Pythogoras)學派習得了對於一切生物都持著親善態度。換句話說,他似乎是一個獨立的思想家,並不依附某一門派。
普魯塔克的名聲,主要是建立在「希臘羅馬名人傳」之上。除了這部傳記之外,他的其餘作品的總名爲Opera Moralia,其中包括六十篇論文。我現在舉出其中幾篇論文的題目爲例,就可以窺知作者興趣的範圍是如何的廣泛:「論子女的教育」,「論機會」,「論迷信」,「論命運」,「論女人的美德」,「如何區別奉承者和朋友」,「論蘇格拉底的天才」,「論傾聽的正當方式」,「論月輪之面」(On the Face of the Moon's Disk),「陸上動物與海上動物何者更爲聰明」,「水與火何者更爲有用」,「論羅馬人的命運」,「雅典人所賴以馳名者,是戰爭?還是智慧?」
從歷史的觀點看來,普魯塔克所寫的傳記在某些方面是不夠確實的,因爲他對於數字有些馬忽,他所根據的資料未必盡屬可信,他的敘述有時也不免有些錯誤或前後矛盾之處。但是他對於傳記的寫作,卻懷有另外一種目的。他對於那些偉大人物的主要興趣,是去發現他們的道德性質。關於這一點,克拉夫(Arthur Hugh Clough)的下面這段話做了一個很好的說明:「在閱讀普魯塔克的時候,我們必須記住下列各點。他是一個道德家,而不是一個歷史家。他的興趣比較少在於政治和帝國的更迭,而更多在於人的品性、個人事蹟、和行爲的動機;被完成並且受到酬報的職責;受到懲戒的倨傲,獲得矯正的輕率的憤怒;在現實世界(the visible world)獲得成功、或者在靈冥世界(the invisible world)尋求憑藉的仁愛、公正、和慷慨。在寫作傳記的時候,他一直都在念念不忘亞理斯多德的道德學和柏拉圖的學說,那些東西構成了他那個時代的有教養的人們的宗教。 」
在亞歷山大傳的第一段裏,普魯塔克曾就他爲亞歷山大和凱撒的傳記選取材料的原則加以說明:「大家不要忘記,我現在所撰著的並非歷史,而是傳記。從那些最輝煌的事蹟之中,我們並不一定能夠極其淸晰地看出人們的美德或惡德;有時候,一件不太重要的事情,一句笑話,或者片言短語,會比最著名的圍城,最偉大的軍備,和最慘烈的戰爭更能使我們瞭解人們的性格和意向。因此,肖像畫家在作畫的時候。特別用心描繪最能表現性格的面部輪廓和眼神,而對於身體的其他部分則不必多加注意,同樣地,請讀者們也容許我對於人們的靈魂的跡象和徵兆多加註意,藉著這些來描寫他們的生平,而把他們的偉大事功和戰蹟留待其他作家們去敘述。」這是寫作傳記的一個正確的原則,也是必須具有大匠的技巧才能實行的原則。因爲「描繪人們的靈魂的跡象和徵兆」,寶在比逐一敘述一個人生平的事蹟,更爲困難得多。普魯塔克所提示的這種原則,一直被後世的傳記作家奉爲圭臬。
「希臘羅馬名人傳」原名「對比的傳記」(希臘文爲Bioi Paralleloi;英文爲Parallel Lives),分爲若干「卷」(Books),每卷包含一個希臘人物和一個羅馬人物的傳記,後面附有一篇「比較」,把兩個人的顯著特點加以對比。普魯塔克所採取的步驟,顯然是先來評斷人物們的道德本質,再來衡量他們所發生的影響,最後把他們的長處和短處,成功和失敗,分別加以比較。可惜的是,這些傳記後來佚失了若干部分;而作者原來的計劃也有若干遺略,顯然是由於他並沒有全部完成這部傳記的寫作工作。現在所留下來的共有五十篇傳記,其中有四十六篇是排比成對的,四篇是單人的。在排比成對的四十六篇之中,有八篇是沒有「比較」的。不過,就這部作品的現有的形貌來說,它迄今仍被認爲是一部只能做爲模倣對象,而不能侈望加以改善的完美傳記作品。這部作品不僅是西洋文學的寶貴資料之一,而且由於其中所包含的豐富的學問、優美的文學性質、和嚴正的人生哲學,也一直被列爲愛好文學者的必讀之書。
「希臘羅馬名人傳」的英文譯本很多,其中比較重要的幾種如下:
(一)Sir Thomas North譯本,刊於一五七五年。
(二)John Dryden譯本,刊於一六八三年。
(三)John and William Langhorne譯本,刊於一七七○年。
(四)Bernadotte Perrin譯本,爲希臘文與英文對照本,刊於一九一六年。
在這幾種譯本之中,最著名的當推諾斯(North)和朱艾敦(Dryden)的兩種譯本。諾斯的譯本,也就是莎士比亞所使用的譯本,並非自希臘文直接譯出,而是從亞繆(Jacques Amyot)的法文譯本(一五五九年)譯出的。不過,如桑普孫(George Sampson)所說的,「這個譯本﹝指諾斯的譯本﹞已經不是普魯塔克,而是利用普魯塔克的題材寫成的一部新的傑作。諾斯的普魯塔克距離亞繆法文譯本之遙遠,正像亞繆的法文譯本遠非普魯塔克希臘文原著的本來面目一樣。」但是,諾斯的伊利莎白式的散文,瑰麗奇特,本身成爲上好的文章。
譯者所採用的,是朱艾敦的譯本。採用這個譯本的原因,不僅因爲它是譯者在臺北所能找到的一種最佳的譯本(對於本書的譯述工作,有關方面規定的期限不長,所以來不及向國外選購書籍),也因爲這個譯本的文字和句法比較現代化,而又保持著原著的濃厚的學術的和文學的氣息。這個譯本雖然名爲朱艾敦譯本,實際上卻是出自好幾個人的手筆,所以文筆並不十分一致。譯者所根據的,是克拉夫的一八六四年的修訂本。Everyman's Library和Modern Library裏面,都用這個版本。朱艾敦是十七世紀的英國詩人、批評家、和戲劇家,英文裏面的biography(傳記)一字,就是由他在「希臘羅馬名人傳」的「緒言」裏面首先創用的。英譯本原文的句法有時很冗長而繁複,譯者盡力保存其文體上的風格。在翻譯的時候,譯者並且參考一部殘缺的Perrin譯本,和Langhorne譯本的一個選本,這是我目前所能得到的僅有的兩種其他譯本。有少數費解的地方,我採用了Perrin的說法,因爲Perrin譯本是希臘文和英文對照的,應該比較切合原文:這類情形中的比較重要之處,譯者都在註解中說明。
朱艾敦英譯本原書共載傳記五十篇(如全部譯成中文,約有一百四十萬字),本書只選譯了五篇(約二十萬字),每篇都是完整的翻譯。原書有克拉夫的長序一篇(近二萬字),在一個比較大規模的譯本裏面,那篇序當然是必不可缺的,但是在目前這個小型的譯本裏面,譯者只把那篇長序做爲這篇「譯序」的主要參考資料之一。
因爲參考書的缺乏,和時間的限制,譯文的註解做得不夠周詳,這是譯者引爲歉憾的事情。其他方面的疏誤,當亦不免,希望讀者不吝指正,我想將來在適當的時機,再做一些增補工作。
本書是由譯者受國立編譯館的委託而譯出的。王館長鳳喈很重視這部書,在這五篇譯稿完成付梓之後,王館長又設法克服一些物質條件上的困離,計劃繼續出版一冊。現在譯者已經接受王館長的囑託,即行著手將這部「希臘羅馬名人傳」再選譯二十萬字左右,作爲本書的下冊出版。
本書譯稿承梁寶秋先生在他本身的著述工作非常繁忙之中,惠予校訂,譯者深爲感謝。
五十二年十月吳奚眞序於臺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