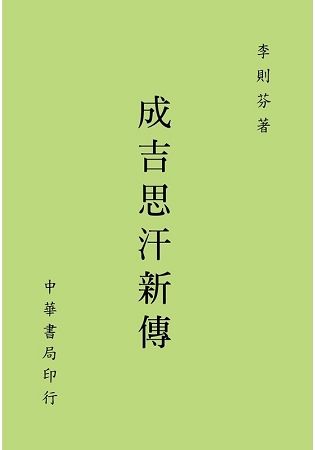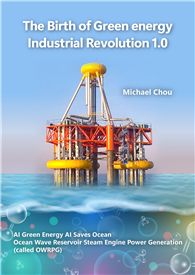元史是中外漢史學家最感興趣的一部斷代史,也是最難以考據整理的一代史,本書根據前人研究,援引中外元朝史料,重加考證正誤統整而成。雖名為《成吉思汗新傳》,實為「蒙古(元)史」,文末又收錄數十張地圖、圖表、年表,資料珍希,是為研究元史者必備之史籍。
本書特色
1.本書根據前人研究,援引中外元朝史料,重加考證正誤統整而成。
2.《成吉思汗新傳》,實為「蒙古(元)史」,文末又收錄數十張地圖、圖表、年表,資料珍希,是為研究元史者必備之史籍。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成吉思汗新傳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514 |
宋元史 |
$ 585 |
歷代君主/帝王 |
$ 585 |
宋元史 |
$ 585 |
歷史人物 |
$ 585 |
社會人文 |
$ 585 |
歷史人物 |
$ 585 |
Social Sciences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成吉思汗新傳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李則芬(1907年─)
黃埔軍校第五期畢業,前半生獻身軍旅,來臺後退役,三十餘年來專心治史。
李氏重要著作有《元史新講》、《中外戰爭全史》、《中日關係史》﹑《成吉思汗新傳》、《戰爭史話》、《泛論司馬光資治通鑒》、《文史雜考》、《先秦及兩漢歷史論文集》、《三國歷史論文集》﹑《兩晉南北朝歷史論文集》、《虞夫詩集》、《哀樂平生詞集》﹑《八十自選詩詞》等書。
李則芬(1907年─)
黃埔軍校第五期畢業,前半生獻身軍旅,來臺後退役,三十餘年來專心治史。
李氏重要著作有《元史新講》、《中外戰爭全史》、《中日關係史》﹑《成吉思汗新傳》、《戰爭史話》、《泛論司馬光資治通鑒》、《文史雜考》、《先秦及兩漢歷史論文集》、《三國歷史論文集》﹑《兩晉南北朝歷史論文集》、《虞夫詩集》、《哀樂平生詞集》﹑《八十自選詩詞》等書。
目錄
第一章 蒙古起源的傳說
第二章 蒙古諸氏族
第三章 阿蘭豁阿與孛端察兒
第四章 前代數可汗
附錄 陰山室韋與汪古部
第五章 鐵木真誕生及其年齡之謎
第六章 蒙古人的生活習慣
第七章 國際情勢概述
第八章 寡婦孤兒艱苦奮鬪
第九章 從愛妻被奪到安答的分離
第十章 成吉思汗興起
第十一章 蒙古里島權爭奪戰
第十二章 滅王汗,併克烈
第十三章 擊滅乃蠻,統一漠北
附錄 出師日期考
第十四章 蒙古帝國初建
第十五章 四宮佳麗
第十六章 皇親國戚
第十七章 十太功臣
第十八章 內除心腹之患
第十九章 畏吾兒自動來歸
第二十章 金國在衰弱中
第二十一章 初次伐金
第二十二章 癸酉攻勢
附錄 哲別取東京的繫年
第二十三章 初期降將
第二十四章 連下三京
第二十五章 耶律楚材與成吉思汗
第二十六章 耶律留哥起兵與遼東的平定
第二十七章 高麗臣服,東夏消滅
附錄 元史之東夏國考
第二十八章 國王木華黎伐金
第二十九章 哲別輕取西遼
第三十章 西征之役的歷史地理背景及戰爭原因
第三十一章 西征花刺子模
附錄 過甚其詞的屠殺紀錄
第三十二章 長春真人及其西遊記
第三十三章 速不台、哲別萬里長征
第三十四章 滅西夏及伐金最後一役
第三十五章 成吉思汗遺產
第三十六章 後嗣繼志,完成大元帝國
第三十七章 成吉思汗論
圖一 唐代蒙兀室韋位置判斷圖
圖二 蒙古四鄰各部落
圖三 聯軍進攻篾兒乞
圖四 蒙古本部領導權之戰的戰場
圖五 蒙古克烈聯軍進攻乃蠻
圖六 汗山之戰判斷圖
圖七 征服乃蠻經過判斷圖
圖八 蒙古初次伐金
圖九 癸酉攻勢
圖十 木華黎經略遼西
圖十一 癸酉遼東情勢
圖十二 金與高麗的國境
圖十三 契丹竄擾高麗
圖十四 木華黎末年的蒙金形勢
圖十五 西遼帝國本部
圖十六 河中交通概況
圖十七 阿拉伯帝國的東方省區
圖十八 西征之進軍路線
圖十九 河中之戰
圖二十 速不台、哲別萬里長征
圖二十一 十三世紀初期的東歐形勢
圖二十二 西夏最盛時代的疆域
圖二十三 滅西夏,遂伐金
圖二十四 元初帝國統治地區
成吉思汗年表
主要參考書籍
表一 元朝秘史所載之蒙古世系(一)
表二 元朝秘史所載之蒙古世系(二)
表三 成吉思汗子孫
表四 术赤子孫及欽察諸汗
表五 察合台子孫
表六 窩闊台子孫
表七 拖雷子孫
表八 忽必烈子孫及元朝帝統
表九 旭烈兀子孫及伊兒汗國王統
第二章 蒙古諸氏族
第三章 阿蘭豁阿與孛端察兒
第四章 前代數可汗
附錄 陰山室韋與汪古部
第五章 鐵木真誕生及其年齡之謎
第六章 蒙古人的生活習慣
第七章 國際情勢概述
第八章 寡婦孤兒艱苦奮鬪
第九章 從愛妻被奪到安答的分離
第十章 成吉思汗興起
第十一章 蒙古里島權爭奪戰
第十二章 滅王汗,併克烈
第十三章 擊滅乃蠻,統一漠北
附錄 出師日期考
第十四章 蒙古帝國初建
第十五章 四宮佳麗
第十六章 皇親國戚
第十七章 十太功臣
第十八章 內除心腹之患
第十九章 畏吾兒自動來歸
第二十章 金國在衰弱中
第二十一章 初次伐金
第二十二章 癸酉攻勢
附錄 哲別取東京的繫年
第二十三章 初期降將
第二十四章 連下三京
第二十五章 耶律楚材與成吉思汗
第二十六章 耶律留哥起兵與遼東的平定
第二十七章 高麗臣服,東夏消滅
附錄 元史之東夏國考
第二十八章 國王木華黎伐金
第二十九章 哲別輕取西遼
第三十章 西征之役的歷史地理背景及戰爭原因
第三十一章 西征花刺子模
附錄 過甚其詞的屠殺紀錄
第三十二章 長春真人及其西遊記
第三十三章 速不台、哲別萬里長征
第三十四章 滅西夏及伐金最後一役
第三十五章 成吉思汗遺產
第三十六章 後嗣繼志,完成大元帝國
第三十七章 成吉思汗論
圖一 唐代蒙兀室韋位置判斷圖
圖二 蒙古四鄰各部落
圖三 聯軍進攻篾兒乞
圖四 蒙古本部領導權之戰的戰場
圖五 蒙古克烈聯軍進攻乃蠻
圖六 汗山之戰判斷圖
圖七 征服乃蠻經過判斷圖
圖八 蒙古初次伐金
圖九 癸酉攻勢
圖十 木華黎經略遼西
圖十一 癸酉遼東情勢
圖十二 金與高麗的國境
圖十三 契丹竄擾高麗
圖十四 木華黎末年的蒙金形勢
圖十五 西遼帝國本部
圖十六 河中交通概況
圖十七 阿拉伯帝國的東方省區
圖十八 西征之進軍路線
圖十九 河中之戰
圖二十 速不台、哲別萬里長征
圖二十一 十三世紀初期的東歐形勢
圖二十二 西夏最盛時代的疆域
圖二十三 滅西夏,遂伐金
圖二十四 元初帝國統治地區
成吉思汗年表
主要參考書籍
表一 元朝秘史所載之蒙古世系(一)
表二 元朝秘史所載之蒙古世系(二)
表三 成吉思汗子孫
表四 术赤子孫及欽察諸汗
表五 察合台子孫
表六 窩闊台子孫
表七 拖雷子孫
表八 忽必烈子孫及元朝帝統
表九 旭烈兀子孫及伊兒汗國王統
序
序
日本那珂通世博士作「支那通史」,至元代而擱筆,先下一番工夫,研究蒙古歷史,完成一本「成吉思汗實錄」。作者的情形也很相似,因爲著作中外戰爭史,寫完了宋遼金之後(已出四冊,約二百萬言)要過元代一個大關,也只好暫時放下戰爭史,先將元史考據整理一番。年來在幾個月刋上,分別發表過元史論文約十萬言,因受讀者及朋友的鼓勵,便索性完成這一本成吉思汗傳記。
元代史是中外漢史家最感興趣的一部斷代史,也是最亂的一代史,其考據整理,是一種無止境的接力賽。所有研究元史的人,不分中外,不論其研究全史或一部分,都是參與接力賽的一員。各人的雖有大小,皆不過跑完其中某一段里程而已。迄今爲止,完成理想元史的目標,還是遙遠得很。本書對於前人的考據,指出許多錯誤或可疑之處,無非是在我自己這一段賽程中,履行接棒人應盡的一份責任而已,決沒有輕視前人功績之意。事實上,沒有前人研究成果的累積,就不會有本書的產生。
本書所用的人地名,與一般專門研究元史的作家不盡相同。大體上說,蒙古的人地名,本書仍以「元朝秘史」爲主,惟當今史地教科書所常用者,則捨秘史而取通用之名。例如元初四代皇帝的本名,歷史教科書皆依「元史」,稱鐵木眞、窩闊台、貴由、蒙哥;一般人在中學時代,就很熟悉這四位皇帝的大名,故不用秘史的鐵木眞、斡歌歹、古余克、蒙格。西方的人地名也是一樣,大都採用世界史地所通用的譯名。例如Sultan譯爲蘇丹,不用算灘,算端,沙勒壇,蘇而灘,蘇爾灘等舊譯名; Mohammed譯穆罕默德,不用舊譯名摩訶末;Baghdad譯巴格達,不用報達,八吉打,巴黑塔等舊譯名;Caucasus譯高加索,不稱太和嶺或高喀斯山;Georgia譯喬治亞,不稱谷兒只,曲兒只或谷魯斤。(按札奇斯欽教授及田中萃一郎已創此先例。)
雖然如此,爲使一部分有志研究元史的人,便於對照參考書籍,本書仍盡量註明舊名。遇有異名過多的,爲省文起見,只說亦作什麼名,不一一註明其出處。卽註明出處者,亦以「秘史」、「親征錄」、「元史」、「譯文證補」及馮承鈞譯「多桑蒙古史」數書爲主。「新元史」的人地名,一般皆依「元史」與「譯文證補」;「蒙兀兒史記」則以「元朝秘史」爲主,二者的人地名皆非自創,故除特殊情形外。不在註明之列。
元史與其他斷代史不同之處,是必須參考許多國外著作。不幸西人所用的中國及亞洲人地譯名,也像中文譯名一樣亂,甚或尤有過之。例如成吉思一名,作者在西書中所看過的,已有如下十幾種寫法:Genghis,Ghenghis,Jenghis,Jenghiz,Chankez,Chengiz,Chinghis,Chi nghiz。 Zings,Cinggis Cingis,Cingiz,Tchinggis,Tchinguis。本書附註的西文人地名,一般採用英文著作中比較通用者。然英文著作或法德文原著的英譯本,也往往引用法德文的人地名,要想純用英文名統一起來,是不可能的事。
作者引以爲憾的,是不能直接閱讀法、德、俄文原著,除依靠中、英、日文的一部分譯本外,對於那三種文字的豐富資料,多不能引爲參考。好在本書性質不重在細節的一一考據,而以全般的綜合研究爲主旨。換言之,只替成吉思汗描繪一個輪廓,並說明他的時代背景,以供一般人閱讀爲主,專家參考次之。就此範圍而論,說一句解嘲的話,或者差可勝任了。
中日及西方各國人士,已經寫過不少成吉思汗傳,一般皆嫌簡略,且有混淆不清之弊,錯誤亦不少。 (缺乏參考價值的,未列入參考書目之內。)本書自然要比前人諸作稍爲進步,至少作者個人自信如此。這不是我比前人強,而是作者接棒於前人之後,以前人的終點爲起點。明言之,因爲本書後出,前人對的我已吸收,錯的我已糾正不少。至於本書命名新傳,無非是別於前人著作而已。然如前所述,有關元史的考據發展,實基於前人研究成果的累積,與史地知識的時代進步。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今日爲新,來日爲舊。因此,雖名新傳,作者內心還是有所不安的。但願此後的接力者,很快又有更新的著作出現,以解除作者的責任。
近十餘年來,作者專心治史,難關重重,幸虧還有許多長官師友支持鼓勵,始能堅苦從事。待拙著中外戰爭史全部完成(約四百萬言),當在是書寫一篇後序,一一道謝。然在此悠長歲月中,助我最多的幾位師友,如四十多年的老朋友王逸芬,李漢儀二兄,曾共患難多年的柳劍霞老師與郭外川先生,三十多年的老同學呂省吾兄,及遠在南洋的家叔柏林等,特須在此先行致謝。至於本書之作,有好些參考書,多賴王寓農同學及陳伯尹、高亞偉二教授代借。還有羅香林、汪大鑄二教授贈書甚多,可爲拙著戰爭史參考者很不少,而羅教授的大著「唐元二代之景教」,則爲本書參考所需。姚夢谷先則常代作者考查或鑑定屬於考古或美術等問題,皆應在此一併道謝。自然,尤其要謝的,還是我的夫人張虞珠女士。在今日唯利是圖與享受第一的社會中,如果沒有一位安貧樂道的賢內助,決不能專心治學。以作者的情形來說,恐怕早就改行謀生,或改寫武俠小說了。
李則芬五十八年十月於臺北景美嚮序
日本那珂通世博士作「支那通史」,至元代而擱筆,先下一番工夫,研究蒙古歷史,完成一本「成吉思汗實錄」。作者的情形也很相似,因爲著作中外戰爭史,寫完了宋遼金之後(已出四冊,約二百萬言)要過元代一個大關,也只好暫時放下戰爭史,先將元史考據整理一番。年來在幾個月刋上,分別發表過元史論文約十萬言,因受讀者及朋友的鼓勵,便索性完成這一本成吉思汗傳記。
元代史是中外漢史家最感興趣的一部斷代史,也是最亂的一代史,其考據整理,是一種無止境的接力賽。所有研究元史的人,不分中外,不論其研究全史或一部分,都是參與接力賽的一員。各人的雖有大小,皆不過跑完其中某一段里程而已。迄今爲止,完成理想元史的目標,還是遙遠得很。本書對於前人的考據,指出許多錯誤或可疑之處,無非是在我自己這一段賽程中,履行接棒人應盡的一份責任而已,決沒有輕視前人功績之意。事實上,沒有前人研究成果的累積,就不會有本書的產生。
本書所用的人地名,與一般專門研究元史的作家不盡相同。大體上說,蒙古的人地名,本書仍以「元朝秘史」爲主,惟當今史地教科書所常用者,則捨秘史而取通用之名。例如元初四代皇帝的本名,歷史教科書皆依「元史」,稱鐵木眞、窩闊台、貴由、蒙哥;一般人在中學時代,就很熟悉這四位皇帝的大名,故不用秘史的鐵木眞、斡歌歹、古余克、蒙格。西方的人地名也是一樣,大都採用世界史地所通用的譯名。例如Sultan譯爲蘇丹,不用算灘,算端,沙勒壇,蘇而灘,蘇爾灘等舊譯名; Mohammed譯穆罕默德,不用舊譯名摩訶末;Baghdad譯巴格達,不用報達,八吉打,巴黑塔等舊譯名;Caucasus譯高加索,不稱太和嶺或高喀斯山;Georgia譯喬治亞,不稱谷兒只,曲兒只或谷魯斤。(按札奇斯欽教授及田中萃一郎已創此先例。)
雖然如此,爲使一部分有志研究元史的人,便於對照參考書籍,本書仍盡量註明舊名。遇有異名過多的,爲省文起見,只說亦作什麼名,不一一註明其出處。卽註明出處者,亦以「秘史」、「親征錄」、「元史」、「譯文證補」及馮承鈞譯「多桑蒙古史」數書爲主。「新元史」的人地名,一般皆依「元史」與「譯文證補」;「蒙兀兒史記」則以「元朝秘史」爲主,二者的人地名皆非自創,故除特殊情形外。不在註明之列。
元史與其他斷代史不同之處,是必須參考許多國外著作。不幸西人所用的中國及亞洲人地譯名,也像中文譯名一樣亂,甚或尤有過之。例如成吉思一名,作者在西書中所看過的,已有如下十幾種寫法:Genghis,Ghenghis,Jenghis,Jenghiz,Chankez,Chengiz,Chinghis,Chi nghiz。 Zings,Cinggis Cingis,Cingiz,Tchinggis,Tchinguis。本書附註的西文人地名,一般採用英文著作中比較通用者。然英文著作或法德文原著的英譯本,也往往引用法德文的人地名,要想純用英文名統一起來,是不可能的事。
作者引以爲憾的,是不能直接閱讀法、德、俄文原著,除依靠中、英、日文的一部分譯本外,對於那三種文字的豐富資料,多不能引爲參考。好在本書性質不重在細節的一一考據,而以全般的綜合研究爲主旨。換言之,只替成吉思汗描繪一個輪廓,並說明他的時代背景,以供一般人閱讀爲主,專家參考次之。就此範圍而論,說一句解嘲的話,或者差可勝任了。
中日及西方各國人士,已經寫過不少成吉思汗傳,一般皆嫌簡略,且有混淆不清之弊,錯誤亦不少。 (缺乏參考價值的,未列入參考書目之內。)本書自然要比前人諸作稍爲進步,至少作者個人自信如此。這不是我比前人強,而是作者接棒於前人之後,以前人的終點爲起點。明言之,因爲本書後出,前人對的我已吸收,錯的我已糾正不少。至於本書命名新傳,無非是別於前人著作而已。然如前所述,有關元史的考據發展,實基於前人研究成果的累積,與史地知識的時代進步。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今日爲新,來日爲舊。因此,雖名新傳,作者內心還是有所不安的。但願此後的接力者,很快又有更新的著作出現,以解除作者的責任。
近十餘年來,作者專心治史,難關重重,幸虧還有許多長官師友支持鼓勵,始能堅苦從事。待拙著中外戰爭史全部完成(約四百萬言),當在是書寫一篇後序,一一道謝。然在此悠長歲月中,助我最多的幾位師友,如四十多年的老朋友王逸芬,李漢儀二兄,曾共患難多年的柳劍霞老師與郭外川先生,三十多年的老同學呂省吾兄,及遠在南洋的家叔柏林等,特須在此先行致謝。至於本書之作,有好些參考書,多賴王寓農同學及陳伯尹、高亞偉二教授代借。還有羅香林、汪大鑄二教授贈書甚多,可爲拙著戰爭史參考者很不少,而羅教授的大著「唐元二代之景教」,則爲本書參考所需。姚夢谷先則常代作者考查或鑑定屬於考古或美術等問題,皆應在此一併道謝。自然,尤其要謝的,還是我的夫人張虞珠女士。在今日唯利是圖與享受第一的社會中,如果沒有一位安貧樂道的賢內助,決不能專心治學。以作者的情形來說,恐怕早就改行謀生,或改寫武俠小說了。
李則芬五十八年十月於臺北景美嚮序
|